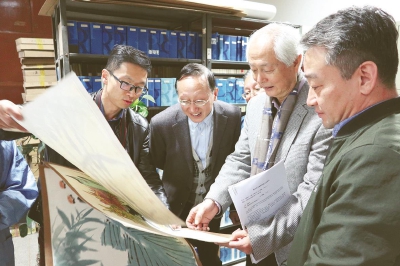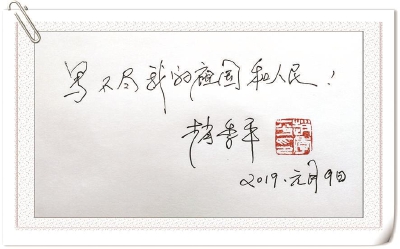特约撰稿 施雪钧
前不久,在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的“赵季平音乐创作国际学术论坛”上,中唱上海分公司向全球首发了一套五张“赵季平音乐作品经典系列”黑胶唱片。这是中国最老牌唱片公司花巨资,从德国全套引进黑胶生产流水线后,出版的首套名家唱片。
真是笔走龙蛇。中国的电影大片、热播电视剧的配乐,近乎一半出自赵季平之手;影视作品的音乐中,走红的主题歌,赵季平三分天下有其一;保守估计,有三代人、超过8亿中国听众,听过他的音乐。那年中国女排在欧洲打比赛,到了紧要关头,忽然观众席上呼啦啦地唱起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赵季平,在上世纪80年代电影《黄土地》以来的几十年间,开创了中国影视音乐的一个“黄金时代”,导演张纪中说:“他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无法抗拒的音乐力量……”
这仅仅是电影音乐。在音乐创作诸多领域,赵季平涉猎甚广,包括交响乐、协奏曲、室内乐、歌剧、民族管弦乐、舞剧、艺术歌曲等,他的作品,题材之广、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叹服。
【人物档案】
赵季平,男,汉族,1945年8月生于甘肃平凉,1970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1978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八届名誉主席。他是我国目前电影音乐界获奖最多、奖次最高的音乐家。经他配乐的电影《红高粱》、《孔繁森》分别获得第八届、第十六届“金鸡”奖最佳作曲奖,《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获法国“南特”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奖,电视剧《水浒传》获第十六届“飞天”奖最佳音乐奖,其中《好汉歌》获最佳歌曲奖,《嫂娘》获第十八届“金鹰”奖最佳音乐奖。
泥土芬芳承载大气象
一个作曲家的黄金储备,就是他对生活的思考和观察的储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内容丰富的外部经历和内心经历。
赵季平难忘第一次“触电”的经历。1984年,他与陈凯歌、张艺谋、何群等年轻导演到陕北采风。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听了农民歌手贺玉堂唱了整整一晚的陕北民歌。是夜,赵季平满脑子都是贫瘠村落的一个个画面。
在米脂县,他们住进脚夫歇脚的大车店。“这晚,睡在炕上,我们盖的被子与土地一样黑,上面都是‘小爬虫’,那条件,你想象不出有多艰难。可电影《黄土地》中的穷苦农民,却一个个变得栩栩如生起来,有筋骨、有血性、有情感。”赵季平说。
云层急剧的碰撞与刺激,便产生出奇妙的电闪雷鸣。作曲家灵感忽现,音乐从灵魂中汨汨流淌出来。很快,赵季平写出了主题曲《女儿歌》。这晚,在窑洞里,几位导演将灯熄灭,黑暗中,传来了如泣如诉、摄人心魄的歌声。灯亮后,每个人眼中,都噙着泪花……
这是一次难忘的艺术“炼狱”!正是这次成功,锻造了赵季平的未来。
此后几十年中,无论在与陈凯歌合作《霸王别姬》《风月》《梅兰芳》,还是与张艺谋合作《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与张纪中合作《水浒传》《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等影视片,赵季平都如同旅行家,用“脚”在写音乐。写《水浒传》音乐,他行走在齐鲁大地;写《乔家大院》,他数次深入山西忻州、河曲一带采风;写《狼毒花》,他多次前往陕晋蒙边区;写《大秦岭》,他走进秦岭山区腹地,如此等等……
赵季平的音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他将音乐与电影情节的结合,发挥到极致,如同中国建筑艺术的榫卯结构,丝丝入扣,严密无间。音乐,塑造出了一个个电影的灵魂,直击人们的心灵。
所有的成功,赵季平都归结为“站在泥土地上写作,与民族音乐血脉相通”。他吸收融汇各种戏曲和民间音乐的风格、节奏、音阶等语汇,当作音乐母语使用。
这种“泥土气”,成就了赵季平音乐的气象万千。譬如,《红高粱》中震天撼地的48支唢呐群,《菊豆》中远古幽灵般的埙,《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中娓娓诉说的南音尺八,《心香》中清新飘逸的箫和古琴,《霸王别姬》中倾诉心声的京胡,《秋菊打官司》中的弹月琴,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令人叫绝的晋胡和二股弦这两件地方特色乐器的运用,电视剧《大宅门》主题曲中糅进的京韵大鼓、京剧、平剧、豫剧、梆子、民歌、通俗七种音乐元素……
民间音乐的绝妙元素信手拈来,成为赵季平音乐作品的标记。这基因传承,来自他的父亲——“为大众而艺术”的中国画一代宗师赵望云。
赵季平说:“我的艺术,继承了先父的基因。父亲的作品,追求的是人民性。他的艺术追求,从小就植入我心。所以我特别关注民间的东西,我的音乐中,大量是老百姓的声音,可能和我父亲画笔下的穷苦百姓和劳动民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山水灵境,万种风情,给了赵季平“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的灵感。他的大脑,成了中国民间音乐和戏曲的巨大储藏室。他的音乐作品,跳动着生活脉搏,有民间音乐的根。
然而,光环、鲜花、荣誉、名利,与世无争的赵季平都看作过眼烟云。他说:“我的音符,长于泥土中。”
中西合璧成就大格调
追求“中国风格、中国气质、中国精神”,是赵季平创作意境的大格调。
“我经常做的功课是,一边采风,一边悉心研究国内外大师的总谱,研究他们的语汇和技巧,一手伸向传统,学习民间艺术;一手伸向世界,借鉴国际音乐优秀成果。这就是我今天的创作状态。我要用中国音乐的母语,与世界对话。”赵季平告诉笔者。
日本作曲家武满彻很欣赏赵季平的艺术独创性。2000年,由他推荐,柏林爱乐在“夏季森林音乐会”上演了赵季平的交响音画《太阳鸟》、交响叙事曲《霸王别姬》,时间长达20分钟。这是中国音乐作品在国际“艺术珠峰”上“零的突破”。
可容纳2.2万人的柏林“瓦尔德尼森林剧场”,有着世界性声誉,是音乐名家们的梦想驿站。因为在欧美特别是德国,乐团的等级森严,分甲级乙级,或者A级B级,乐团要上演一部中国作品,是件极困难的事,有时往往需要全体演奏员投票后,才能做出演奏决定。
而此次,是国际乐坛对中国作品、中国作曲家的认可,也是中国音乐的荣光时刻。因为,在西方人眼中,赵季平是“最具东方色彩、中国风格的作曲家”,其作品渗透着中华传统的精髓、中华美学精神。他的音乐,既具有一种特殊的门德尔松式的优美和雅致,以及洗练明晰的结构,又极具张力,有品位、有风格、有个性。他被公认为是一位集音乐纯洁、甜美、匀称、优雅的旋律大师。他的音乐,符合东西方听众的听觉审美,其音乐中丰富细致的情感表达,能触动听众感官纤维中最敏感的神经。
在创作中,赵季平没有照搬模仿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思维和技法,而是将其运用到中国传统音乐的思维中,并将它中国化。这使得他的中国视野扩展为国际视野,成了“中国音乐走出去”的先行者。
“越是民族的东西,越要与时代同步,越要走向世界、感染世界。民族音乐如果锁在家里,那如何向外寻觅知音,产生共鸣,成为世界的精神财富?在多元化的世界里,音乐界也要解放思想,对外开放,让世界认知中国音乐,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肃然起敬。”赵季平说。
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便是如此。这部国家大剧院的委约之作,创作历时一年,但作品却酝酿了近十年。他心无旁骛,定下创作宗旨,要写出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作品。这部表现人间大爱、人性回归的作品,在2017年10月10日国家大剧院的首演中,便获得极大成功。赵季平很欣慰。他说:“令我感动的是,首演后观众反响非常强烈,懂音乐的、不懂音乐的都很喜欢。之后,国家大剧院还带着这部作品到北美巡演,外国听众也很喜欢。”
而他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同样也被国际乐坛一线演奏家带进西方国家的音乐厅。这部作品,无论在文化内涵还是技术层面,都堪称上乘之作。以至于大提琴演奏者马友友在首演前,作了大量的特别研究和艺术阐释。首演成功后,《庄周梦》成了他在各国演出的保留曲目。
《庄周梦》在国际乐坛处处遇知音。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一位教授特别钟爱这部“美妙得难以形容”的作品,在比利时和中国,都上演了此作。
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王次昭说:“赵季平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缩影。他的创作,恰恰是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反思最好的回答,许多让我们困惑的问题、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赵季平的作品中解决了。他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杰出代表。”
面向大众呈现大情怀
赵季平深爱大西北。指着脚下土地,他多次对笔者说:“对西安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情结——‘不浮躁,人心静’。艺术创作,最需要的就是不浮躁。我的磁场就在这!”
儿子赵麟,解释了他父亲的“磁场”一说。“我父亲一直不离开西安,很大原因在于家族的基因和传承。我爷爷上世纪40年代来到陕西,安家西安后,画遍了大西北的人民和土地。到了父亲这一辈,他用音乐,继续描绘大西北……”
赵季平出身于名门世家。父亲赵望云,与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画友多有往来。自小,赵季平和兄弟们就在文人荟萃的浓厚文化氛围中受熏陶。赵家七兄弟中,出了三个音乐家、两个画家。
在家中,哥哥、弟弟自小就有画画天赋,而赵季平却显不出有何能耐。溺爱他的母亲,称他为“傻四”。可“傻四”对戏文与音乐,特别有感觉。或许,拉一手好京胡、能唱全本京剧《玉堂春》的超级京剧迷父亲,将文艺基因,重点传给了他。
赵季平说:“对音乐,我简直是入迷。我们家住在西安碑林,碑林里每天放广播,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不爱听广播,就自己哼哼,瞎编调。在小学三年级的一次晚会上,每个小朋友站都起来报志愿。我站起身,脱口就说将来要当作曲家。到了小学六年级,我在院子里组织起‘球拍扫帚乐队’,球拍当小提琴,扫帚当大提琴,我拿着诗,瞎编了一曲,指挥一群孩子,教他们唱。父亲看到后,常在一旁笑。”
然而赵季平却非常喜欢看父亲画画。一有空,他就钻进父亲的画室,时不时地在一旁“指点江山”。看到精彩之笔,如京剧票友一般大声喝彩。久而久之,使得他对色彩及画面极为敏感,无意间练就了画家观察事物的独特眼光。他觉得,父亲的画中有诗、有音乐。
1970年,赵季平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省戏剧研究院。当时,父亲被下放到农村,赵季平坐长途班车去乡下看他。“在棉花地里,我沮丧地告诉了父亲,不料他听后非常高兴。‘到那好啊,你在学院学的东西,是书本上,是基础。你要把民间音乐这一课补上,那可是个戏窝子,你要坚持住!’父亲这番话启发了我,犹如播下的种子。在那,我一个猛子扎了21年。磨炼,是最好的课。”他接着说,“从小,父亲从来不打我们,也不给我们什么压力,但有时他几句话,就让你受用一辈子。”
的确,赵望云在长期旅行写生中练成的坚毅性格,人道主义精神,远大、独到的眼光,形成了超乎常人的精神信仰和人格力量。这个被冯玉祥称为“顶爱国”的画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
早在20世纪30年代,赵望云的农村写生,开辟了中国创作的生活之路。他发表在《大公报》上反映中国农村破产和劳苦大众生活的画,冯玉祥配上了打油诗,让赵望云监工、老舍作序,刻成48块石刻,耸立在泰山脚下;上世纪30年代之后,他的塞上写生、西北写生,用中国的画笔和技法,记录了一个时代。赵望云把生活转到画面上,而赵季平,又将父亲的画面转到音乐中。
很多年后,人们发现,赵季平的文化遗传,子承父脉。赵望云曾说:“美术是凝固的音乐”,现在,赵季平让“音乐成了流动的美术”;赵望云一生“为大众而艺术”,儿子赵季平一生是“艺术为大众”。与西北有着特殊情缘的父亲,将天生怀有对劳动者尊重的个人情怀等“基因”,都遗传给了“傻四”。
这种“扎根生活”的家训,使赵季平没有偏离父亲的艺术思想。他的音乐,始终面向大众,人人都能在一种音乐体裁中认识到它的美。
可贵的是,赵季平的家风,正代代相传。赵季平常用父亲的艺术人格和思想,教育儿子。他告诉赵麟:“当年,你爷爷坐着大车,骑着骆驼,三上敦煌,五进河西走廊,在艰苦的条件下,长年坚持在大西北旅行写生。现在,交通条件便利了,你可以坐飞机到兰州,沿着你爷爷走过的路,到祁连山去深入生活。”赵麟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深入祁连山采风三个月,回来后很快写出了大提琴与笙协奏曲《度》,由马友友、吴彤与纽约爱乐乐团首演并引起轰动。“我对他说,你看,深入和不深入,就是不一样。扎根生活,是你爷爷留下的家风!”赵季平说。
在纪念父亲的文章《心语》中,赵季平写道:“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至今,我始终不忘父亲的教诲,坚持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中国民族音乐这片沃土……”
是的,沿着父亲走过的路,赵季平创作出了管子与乐队《丝绸之路幻想曲》《黄河遥遥》舞剧《大漠孤烟直》室内乐作品《关山月——丝绸之路印象》《大秦岭》等众多脍炙人口的音乐。
赵季平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有一个使命,为中国创作黄钟大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