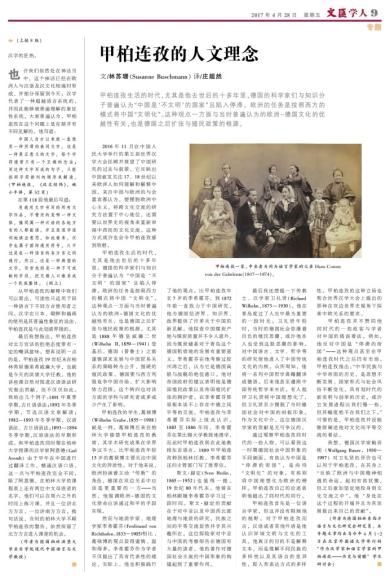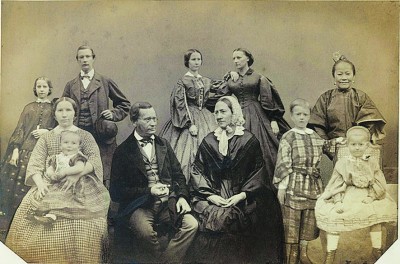文/林苏珊(Susanne Buschmann) 译/庄超然
甲柏连孜生活的时代,尤其是他去世后的十多年里,德国的科学家们与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是‘不文明’的国家”且陷入停滞。欧洲的任务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将中国“文明化”。这种观点一方面与当时普遍认为的欧洲-德国文化的优越性有关,也是德国之后扩张与殖民政策的根源。
2016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汉学大会回顾并展望了中国研究的过去与前景,它反映出中国愈发关注17、18世纪以来欧洲人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来自中国与欧洲的与会嘉宾都认为,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将跨文化交流的研究方法置于中心地位,还需要以世界史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西间的文化交流。这种方式或许也会令甲柏连孜感到欣慰。
甲柏连孜生活的时代,尤其是他去世后的十多年里,德国的科学家们与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是‘不文明’的国家”且陷入停滞。欧洲的任务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将中国“文明化”。这种观点一方面与当时普遍认为的欧洲-德国文化的优越性有关,也是德国之后扩张与殖民政策的根源。尤其是1888年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登基后,德国(普鲁士)之前谨慎谋求发展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策略转为公开、强硬的殖民政策。德国要与西方列强竞争中国市场,扩大影响势力范围。这个转向也对该方面的学科与研究者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
甲柏连孜的学生,葛禄博(Wilhelm Grube,1855—1908)就是一例。葛禄博后来在柏林大学接替甲柏连孜的教席,其学术研究成果在学界争议不大。比甲柏连孜年轻15岁的葛禄博主要关注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对于他来说,欧洲扮演着主动“传教”的角色,德国在双边关系中应该是更重要的一方——当然,他强调欧洲-德国的文化使命应该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
然而与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相比,葛禄博的观点显得谨慎、温和得多。李希霍芬作为学者不仅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实际上,他也积极践行了他的观点。比甲柏连孜年长7岁的李希霍芬,到1872年前一直致力于中国研究。他为德国经济界、知识界、政界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新见解。他探查中国煤炭产地与煤炭质量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煤炭储备对于青岛这个德国租借地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李希霍芬在他考察过胶州湾之后,认为它是德国商船与战舰的绝佳港口。他对帝国政府的建议表明他是德国殖民政策以及帝国殖民扩张的拥护者。在李希霍芬那里根本谈不上存在中德之间平等的交流。甲柏连孜与李希霍芬实际上彼此认识。1883至1886年间,李希霍芬在莱比锡大学教授地理学,而此时甲柏连孜则在此地教授东亚语言。1889年甲柏连孜转到柏林任教,李希霍芬还向主管部门写了推荐信。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也值得一提。19世纪80年代末,他曾在柏林跟随李希霍芬学习过一段时间。斯文·赫定的贡献在于对中亚以及中国西北部地理与地质的研究,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显然并非其兴趣所在。这位探险家对中亚与中国的考察报告在德国有大量的读者,他的著作对德国社会主流的中国形象的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他在青岛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光。卫礼贤年轻时,当时的德国社会弥漫着自负的殖民思潮,或许他本人也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对中国语言、文学、哲学等的研究使他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众所周知,他将一系列中国哲学典籍翻译成德语。后来他甚至遵照中国传统哲学来生活。有人批评卫礼贤将中国理想化了,但卫礼贤至少摆脱了当时德国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作为文化中介,这位德国汉学家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
通过观察甲柏连孜同时代的一些人物,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德国社会中国形象的不同侧面。有些认为中国是“停滞的帝国”,是尚待“文明化”的对象。有些则将中国理想化为欧洲的榜样。甲柏连孜自己的论述表明他超出了同时代的同行。
甲柏连孜首先是一位语言学家,但这并没有限制他的视野。对于甲柏连孜而言,汉语或者其他外语是他认识异域文明与文化的工具。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解释文本,而是理解不同民族的多样性以及其语言的差异性,即人类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甲柏连孜的这种立场也契合世界汉学大会上提出的那种在双边世界史视角下探索中欧关系的要求。
甲柏连孜并不赞同他同时代的一些政客与学者对中国的错误看法。例如,他反对中国是“停滞的帝国”——这种观点甚至在甲柏连孜时代之后仍有市场。甲柏连孜指出:“中华民族与中华帝国的历史,是思想不断发展、国家形式与社会风俗不断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新发明与创举的历史。或许它发展进程比我们慢一些,但其幅度绝不在我们之下。”可惜的是,甲柏连孜并没能继续阐述他对文化间平等交流的看法。
我想,德国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7)对卫礼贤的评价也可以用于甲柏连孜,在其身上“反映了欧洲与中国精神相遇的命运,起初有些犹豫,但之后愈加坚定地投身到文化交流之中”。他“身处在这个过程的开端并且为其发展做出来自己的贡献”。
(作者为德国柏林东西方语言与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本专题文章均出自今年4月1-2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作为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甲柏连孜——历史与前瞻”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