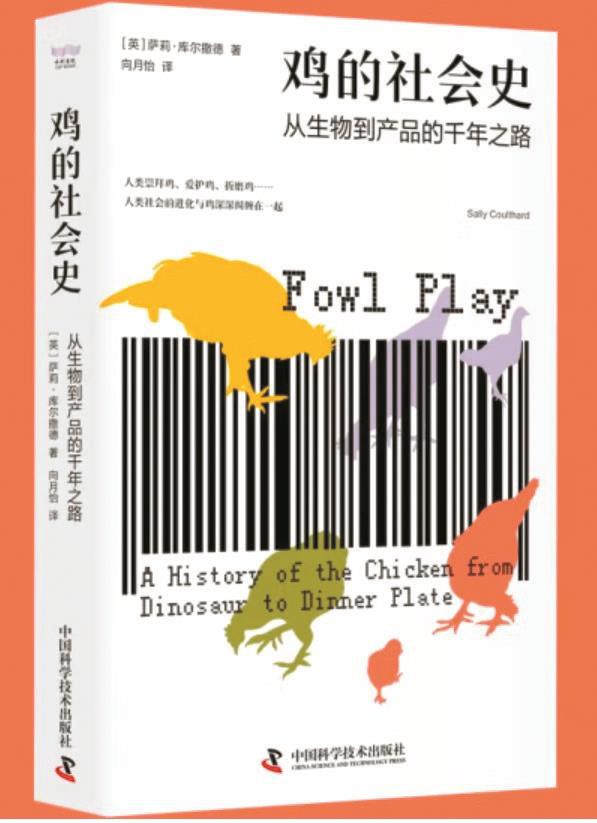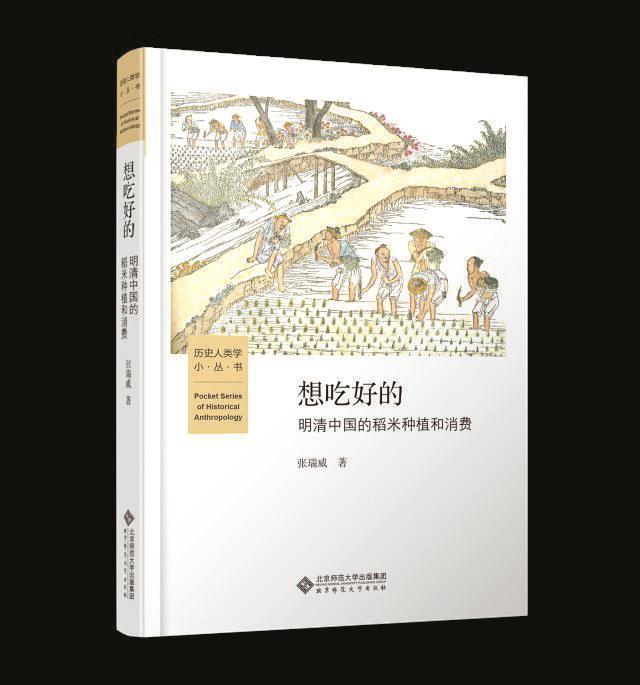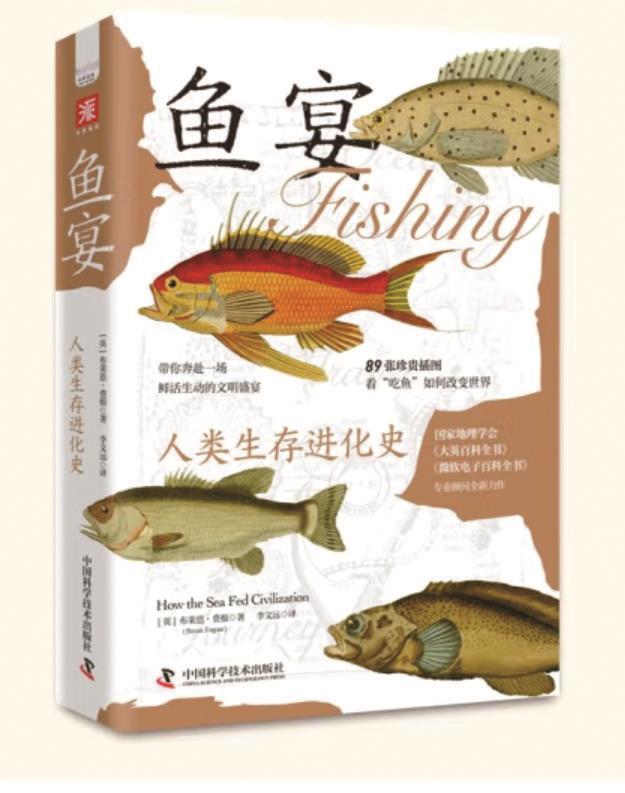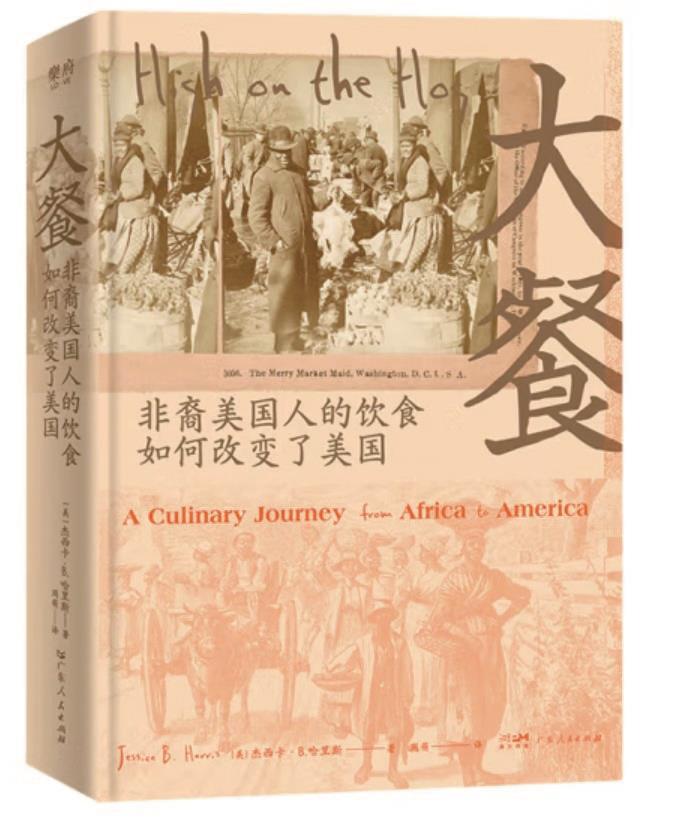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10-20 第28119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历史,应该从舌尖讲起
《鸡的社会史:从生物到产品的千年之路》 [英]萨莉·库尔撒德 著 向月怡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出版
■唐山吃非小事,可在历史书写层面,常被忽略。
古人写史,多有激浊扬清、垂范后世之意,吃很难与道德判断搭上关系,故被误为“小道”。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有饮食禁忌,表达出对“口腹之欲”的鄙夷。
可吃毕竟是重要的。人体消化器官原本只适植食,冰川时代下,不得不食肉,这需要强大的消化系统,可就算这样的系统被进化出来,其重量也已超过承受能力的极限,大腹便便的原始人将从此消亡。幸亏人类利用了火,熟食大大减少了消化负担,人得以拥有大脑这样的“奢侈器官”——仅占体重的2%,耗能却达25%。
第一个吃熟肉的智人可能只是被美味诱惑,好在他身后的智人们同样贪吃、同样“没出息”,这才有了今天的我们。从猿到人,舌尖居功至伟。
也许,正史本就该从舌尖讲起,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正确把握它的意义。
从宠物混成了食物
2023年,我国出栏肉鸡130.22亿只,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在今天,“养鸡就是用来吃的”是常识,但在《鸡的社会史:从生物到产品的千年之路》的作者萨莉·库尔萨德看来,并没这么简单。
早期出土的家鸡骨骼完整(未经烹饪、啃咬)、寿命长(长者达4年,现代肉鸡一般不超60天)、公母比例为3∶1(现代养鸡场一般是1∶10,早期人类似乎只偏爱公鸡)……说明鸡当时只是宠物。
原因一是直到19世纪初,鸡体重很少超1公斤,不堪一食。二是鸡威武雄壮,受敬重。
从DNA看,鸡是霸王龙的近亲,科学家给鸡尾绑上棍子,模仿霸王龙尾,鸡果然走出“霸王龙步”;鸡保留了长尾基因,鸡胚有16节椎骨,比孵化后多9节;科学家已培育出长牙的鸡,或有一天,鸡会暴露出它是潜伏的霸王龙的另一面。
在古希腊,年轻人观摩斗鸡是必修课,以“培养士兵对勇敢的追求”。古罗马时,将军们常用公鸡占卜,老普林尼称:“世上各国的伟大指挥官都得听凭公鸡的差遣。”然而,尚武的古罗马人最早坏了规矩,他们吃鸡蛋且吃鸡,且嘲笑:“我们不像古希腊人那样,竭尽所能找来最凶猛的鸟类只为比赛和打斗。”
百年战争时,英人仇视法人,拉丁语中公鸡音近高卢,足球与虐待公鸡成了英国忏悔节的全民运动,路易十四则将公鸡列为法国皇室标志。
1849年,英国禁斗鸡,鸡再被宠物化,维多利亚女皇尤喜中国的“九斤黄”,却误称为交趾鸡,由此培育出的“梵天鸡”引发金融风暴,堪比“郁金香泡沫”。
中世纪时,肥美的阉鸡受追捧,但成功率低(死亡率1/7),富家菜谱中鸡肉占比不超10%。一战时,鸡肉不在管制名单上,始入寻常百姓家;二战时,美国军方大量采购鸡肉,推进了“现代化养鸡”——在现代化鸡场中,每平米挤入15只鸡,远小于烤箱面积——鸡的“居住条件”至死都不得改善。
生而拥挤,鸡场主用断喙、给小鸡戴特殊眼镜等,防止互啄。鸡看上去呆头呆脑,但学者发现,它远比人类想象得阴险:老鹰来时,公鸡往往不发警报,以免牺牲自己;如附近另有公鸡,它会毫不犹豫报警,利用老鹰除掉潜在对手。
历史证明,出肉率高、繁殖能力强、心眼多的宠物,难免沦为食物,但人类意犹未尽,坚持培养毛更少、体重更大的鸡。鸡因战力强被赞赏、被神话、被饲养,又因战争需要被吃。福兮祸所依,这本书告诉我们,每个全家桶里都蕴含了这一复杂道理。
“想吃好的”也是进步动力
“南人食米,北人食面”,似是习俗;《天工开物》称“种性随水土而分”,认为是自然安排……但这些观点,忽略了人的选择性和市场的巨大作用。张瑞威先生的这本《想吃好的:明清中国的稻米种植和消费》从历史人类学视角,爬罗剔抉,钩沉出变迁的隐秘逻辑。
受气候等因素影响,古代北方确少稻作,但主粮粟(小米)也非寒代植物。据《齐民要术》,粟分早晚两种,早粟产量高,每亩只需三升种子,晚粟产量低,每亩需五升种子,贾思勰却力挺后者:“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晚粟得到普及,源于好吃,而非“效率提高”。在“效率”与“想吃好的”之间,市场发挥了平衡作用。
宋代时,占城稻被引入,一年两熟,引发“农业革命”。占城稻需插秧、水车和牛耕,可在肥沃的江南之地,农民不用耕牛,靠人力牵引铁搭。牛耕10亩,人力仅5亩,宋应星却赞美:不养耕牛,则无需饲草,闲地可种豆、麦、蔬菜,经济上更划算。
人们常误以为,农业是封闭经济,但据英国经济学家陶尼在1932年的研究,中国农民53%的农产品卖到市场,包括1/3的水稻,1/2的小麦、豆类和豌豆,2/3的大麦,3/4的芝麻和蔬菜等。明清农民是为市场而生产。
如果只追求效率,红薯最应被普及,它产量是稻米的10倍,可直到上世纪中期,广东农民依然“有轻视番薯的思想……如说某人没有用处,就说他是‘大番薯’”。
一方面,水稻易换成金钱。1820年前,孟加拉已成欧美进口稻米的主要产区。红薯却不行。
另一方面,大米好吃。在广东等稻米产区,富人将本地最优产品截留消费,普通城市居民买湖南、广西等地产大米,它们外观与本地大米相近,这既赋予他们身份感,也让他们成为米价上扬时的受害者。可一旦情况好转,他们依然选择稻米。
长期以来,一提起农业,似乎就是“落后的”,忽视了农业与市场的紧密联系,这可能是近代化的关键。清政府鄙夷米商,却较少干预市场,长途贩运成为可能,但种种不确定因素,仍使质量与数量的平衡、价格选择、供需关系、品牌培育等无法优化,被封印在“静止的”“僵死的”的状态中。只从舶来的近代化视角,很难理解其中逻辑。本书在常人熟知的“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增多—商业进步—近代化元素产生”的观念之外,呈现出历史本身的丰富和多元。
吃鱼改变了世界
“吃不吃鱼?”这是餐桌上常见问题。有人忌鱼,也有人视鱼为“硬菜”。这种“认知分裂”并不奇怪,在《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中,英国学者布莱恩·费根给出解释:
其一,不喜吃鱼是正常的。捕鱼民族未发展出大型文明,对比偶尔吃鱼者,他们是极少数。
其二,喜吃鱼也是正常的。在人类最古老的三种获取食物的方式(捕猎、采集、捕鱼)中,只有捕鱼传承至今。如果不吃鱼,原始人可能早已灭绝;没有鱼干,金字塔将无法建成;在中世纪,不吃鱼的欧洲人会死于营养不良;鲱鱼产量猛降,让荷兰迟迟无法迈入近代化……人类史上的重大事件,多与盘中鱼相关。
距今约1.8万年,地球经历最后一次冰盛期,带来丰富的海产品。在沿海地区,先民留下许多山一般的贝冢。贝类热量低,但易得,四季可采,只是海产品生产无法支撑人口增长。
海岸线常变化,沿海难农耕,无法实现社会转型。捕鱼多靠单打独斗,人人重平等,很难组织,在渔场分配等问题上,捕鱼民族的家庭内部常有冲突。只有极少的捕鱼民族孕育出复杂社会,人们靠每年在“夸富宴”上竞奢斗侈,博取尊重。
捕鱼民族不断迁徙、分裂,走遍全球,包括最早通过白令陆地桥,进入美洲。
捕鱼民族未成帝国,但他们的技术被其他帝国所用——古埃及人会钓鱼、围网捕鱼,还会加工鱼干,那是建金字塔工人的必备食物之一。古埃及人还掌握了人工养鱼,发展出最早的鱼市。古罗马人发扬光大,鱼池成了贵族别墅的标配。
公元一世纪起,基督教要求信徒在宗教节日斋戒,16世纪时,欧洲人一年约40%的日子禁食,靠吃鱼维持。此前捕鱼都是抓大鱼,鲱鱼个头小却产量惊人。16世纪初,鲱鱼捕捞占荷兰GDP的8.9%。可每隔百年,鲱鱼会改变渔场,19世纪时,鲱鱼只占荷兰GDP的0.3%。
再如,为获取鳕鱼,英国人一度占据格陵兰岛,并冲向北美大陆,在英国的挤压下,法国为保护渔场,决定支持美国独立……渔业资源将列强卷入敌对,可它们都是失败者,“工业化捕捞”让鳕鱼资源几近枯竭,如今产量不足当年的1%。
只靠捕鱼,难成正果;依靠捕鱼,赢得发展。吃鱼与不吃鱼都理直气壮,如今更值得担心的倒是:明天的鱼在哪里?无鱼可吃的那一天,人类如何进步?
是谁创造了美国美食
什么是美国的乡土美食?炸鸡、胡椒羹、焖猪排、烤肉、秋葵汤、可口可乐、烤红薯……可《大餐:非裔美国人的饮食如何改变了美国》的作者杰西卡·B.哈里斯说:它们都是非裔美食。
早期非裔作为奴隶,被卖到美国南方,他们带去高粱、光稃稻(非洲人驯化的稻种)、秋葵等,以及热带人喜爱的酸辣口味。奴隶们初期在烟草地中劳动,17世纪,种植园开始让奴隶当厨师。这是份苦差事,终日工作在炉旁。旅行者来访,铃声便响起,奴隶厨师须立刻准备食物。奴隶厨师渐成种植园的“门面”——饭菜好,客户常光临,生意机会多。
1776年,美国发布《独立宣言》,89年后,才废除奴隶制。为掩盖其中落差,美国南方农场主将黑人描述为“快乐的厨师”——只会做饭,被好心的奴隶主收留,他们很愉快。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主厨詹姆斯·海明斯就是非裔,为摆脱奴隶身份,他选择了逃走。
其实,奴隶制被终结后很长一段时间,非裔们的生活仍艰难,找不到工作,只能继续当厨师,他们创出诸多名品:可口可乐的原材料可拉果便来自非洲;红薯虽是美洲作物,但美国早期种植、收割者都是非裔,非裔还发明了红薯派等,非裔科学家乔治·卡弗开发出100多种用途,红薯得以普及。
上世纪60年代,在民权运动推动下,人们渴望与非裔结成“灵魂伙伴”,因此有了“灵魂帽子”“灵魂服装”等,“灵魂美食”成了非裔菜的通称,甚至将中餐、东南亚菜等也纳入其中。
非裔美食在塑造美国传统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但“技术精湛、才华横溢的黑人厨师已从历史中被抹去,这使人们被种族主义言论误导——非裔除了劳动力,没给美国带来什么,没对美国产生积极影响”。
更有甚者,人们以为非裔菜即炸鸡、玉米粉蒸肉、一锅炖等,是不健康的菜肴。其实,非裔菜多用豌豆、绿叶菜等,只是在城市化裹挟下,它也被单调化、快餐化,给了不想承认非裔贡献者以借口。
本书是相关研究领域的经典,不仅全面呈现了非裔菜发展历程,更为“美国人是前所未有的种族:非洲、欧洲和美洲的混合体”这一论断,提供了坚实的论据。对于想“吃懂美国”者,本书不可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