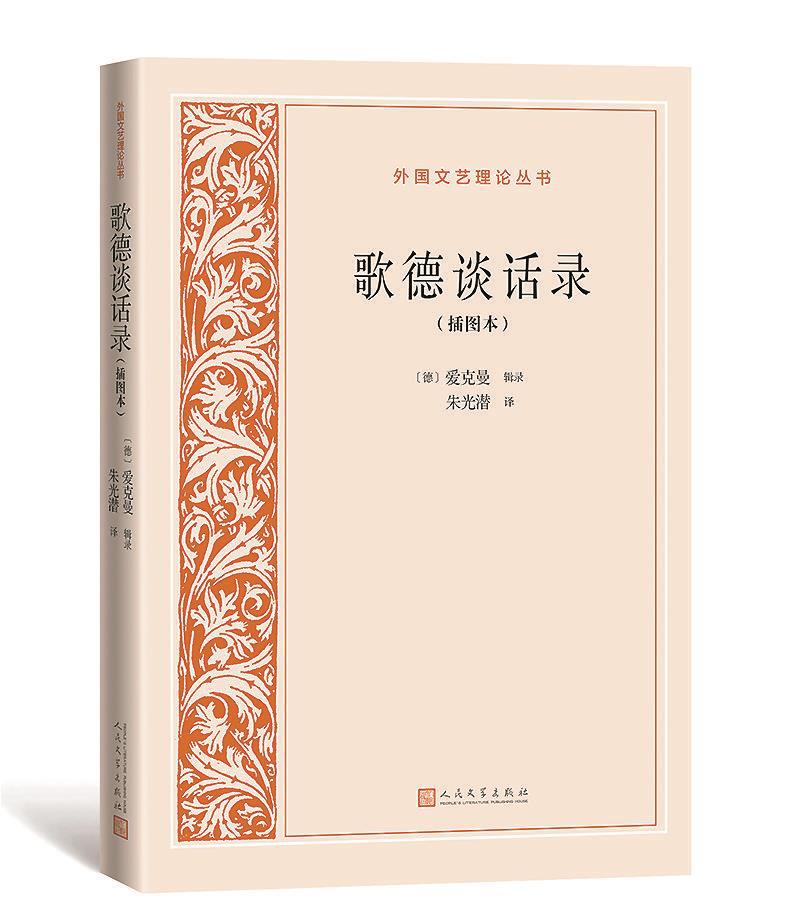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10-13 第28112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重读《歌德谈话录》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郜元宝但凡重要的新书甫一出版,报刊杂志便会很快刊登应景适配的读后感或评介性文字。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书评随笔就出于此等“捷才”之手。
我年轻时拿到一本新书,也能洋洋洒洒写出一篇并不太坏的文章。如今眼花腰痛,反应迟钝,再也不敢见猎心喜了。
唯其如此,就愈发叹服伟大的歌德观察体验之精细。他说“天才”(也应包括善写书评的“捷才”)都需要身体基础,健壮而不知疲倦,像拿破仑指挥战役,几天几夜不睡觉还精神饱满。他回忆自己年轻时经常被灵感驱使而奋笔疾书,沉静之后发现一幕精彩的戏剧、一些闪光的诗行、一段动人的小说情节业已宣告诞生,晚年虽依旧健康,但精力不济,只能少写、慢写了。
歌德还相信物质刺激能焕发本有的天才。他告诉秘书兼助手爱克曼,席勒书桌抽屉里总是放满腐烂的苹果,那种气味令他头晕目眩,却让席勒神清气爽,文思泉涌。歌德还建议爱克曼,倘能自控,不妨少量饮酒,帮助写作。爱克曼裒集的《歌德谈话录》确实留下了他们师徒小酌怡情的许多动人场景。
朱光潜所译《歌德谈话录》1978年初版,我书架上这本是人文社1985年第4次印刷。扉页上有当年稚嫩的签名,并写着购书时间:1986年4月8日。
不记得这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了。总之,是临近本科毕业并已决定读研究生的那段时间,听了先师蒋孔阳先生的建议,特地去复旦校门口新华书店购置的。
几十年来我不停地翻看这本书,许多内容已烂熟于胸。若说我私下谈论它的频率超过某些国学发烧友引用《论语》,恐怕与事实也相去不远吧。
歌德谈话录范围极广,包括古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以来众多历史事件、政治学说、哲学和文艺思潮,涉及难以数计的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举其荦荦大者,就有英国的莎士比亚、司各特、拜伦、穆尔、边沁、卡莱尔,法国的高乃依、博马歇、莫里哀、狄德罗、伏尔泰、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意大利的但丁,西班牙的卡尔德隆,德国的康德、谢林、黑格尔、席勒、许莱格尔兄弟,还有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家,达尔文、牛顿等科学家,文艺复兴以来众多画家雕塑家,包括中国明朝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当然,还有歌德本人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与颜色学、光学、植物学研究。
我岂能仅仅因为这是摩挲已久的珍藏,就自信能写出与之相称的书评呢?我只能再次捧出这本发黄的小册子,记下不同时间阅读它的点滴感受。
有段时间我总是跟蒋孔阳先生大谈生活上的苦恼,以及自以为是的“思想”。他就劝我去看《歌德谈话录》“两个时代说”。这是歌德与爱克曼1826年谈话的头条,朱译加了小标题,“衰亡时代的艺术重主观,健康的艺术必然是客观的”。
我明白蒋先生的用意。他给毕业生留言,最爱抄录《浮士德》名言:“人要立定脚跟,向四周观看;这世界对有为者并不默然。”世界很大,人应该冲出小我,不可画地为牢。但我总觉得“两个时代说”未必完全正确。反之也可以说,衰亡(走下坡路)时代的艺术往往追逐客观世界的表象,健康的时代精神则鼓励文艺家真正关切并尊重内心世界。歌德顶多只对了一半。
《歌德谈话录》如散金碎玉,却并不缺乏类似“两个时代说”的纲领性思想。不必说歌德与席勒共同感兴趣的“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异同了,以另一个巨人拿破仑为话题,歌德也发表过不少惊世骇俗的议论。他经常因为拿破仑征战埃及时行囊里带着《少年维特之烦恼》而毫不掩饰地沾沾自喜,但他对拿破仑的好感绝不仅仅因为拿破仑重视他个人的作品,而是赞赏拿破仑所代表的法国革命时期弥漫欧洲的积极进取的文化。
德法两国当时有激烈的利益冲突,但歌德说:“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他关心文明与野蛮之辩,超过国族利益之争。
歌德还发现:“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但是也有一种文化水平,其中民族仇恨会消失。”他庆幸自己60岁之前就“坚定地站在这种文化水平上面了”。
由此出发,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歌德谈话录首次提出、至今仍被东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世界文学”的概念。
歌德时代一些有考据癖的学者动辄指斥莎士比亚或其他作家笔下某个人物来自古希腊罗马的虚构,并因此抹煞莎士比亚等人的创作。歌德鄙视这种“历史批判”。他不认为那些考据得来的“可怜的真相”有何益处,“罗马人既然足够伟大,有能力虚构出这样的传说,我们就没有一点伟大品质去相信这种传说吗?”
有关古希腊罗马的记载是否属实是一回事,归在古希腊罗马大师名下的作品本身价值如何,则是不容回避的另一个问题。如果您说它们是虚构,那就请您也虚构一下试试?
关于莎士比亚和拜伦,歌德有说不完的话。他说这两位总嫌生存空间太逼仄,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说都是监牢。他认为莎士比亚过于丰富雄壮,德国作家最好每年只读一部莎剧,否则会被“压垮”。他最怕听人奢谈“独创性”,“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他讨厌批评家们一旦发现作家作品之间有相似性,就惊呼“抄袭”。歌德既有害怕被“压垮”的“影响的焦虑”,也渴望并感谢其他作家的影响。他经常如数家珍地告诉爱克曼,自己受过哪些本国和外国作家的滋养。
不可不读朱光潜的注释。朱先生翻译并注释此书,中心任务是要证明恩格斯经典论述的正确性,即歌德既是天才,又是庸俗的魏玛枢密顾问。
但歌德的自相矛盾并不总发生在天才和庸人之间。他期待“世界文学”早日到来,却仍推崇古希腊为不可超越的典范。他相信灵魂不灭,却怀疑三位一体。他告诫爱克曼别在乎批评,却不停地抱怨国内外读者对他本人的指责。他大谈天才,相信父母年轻健康或年迈体弱时养育的子女将来身体和智能会有难以跨越的差距,却又鼓励爱克曼努力学习,勤于观察,不可坐等灵感自动降临。他似乎总能保持平和睿智的风度,但偶尔也会发出梅菲斯特菲勒斯的恶毒讥诮:“我没有感到有必要去看关起来的疯人,在世间自由行走的疯人我已经看够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歌德甚至并不顾念读了《维特》而轻生的青年,居然说什么“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十来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去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
这些矛盾让歌德看上去不够完美,却很真实。
初见爱克曼,歌德就谆谆教诲他不可制定庞大计划。要从小事做起,比如写些小散文,记录旅游时对各地风物的观察。但歌德又规劝爱克曼须力戒小气,敢于抓住宏大命题。他经常深情回忆自己和席勒在“狂飙突进”时代如何不断写出佳作力作。
爱克曼没有记录他每逢这时会作何感想,我则油然想起《傅雷家书》。歌德和傅雷教导晚辈,都难免一厢情愿,越俎代庖。这或许让有些年轻人吃不消,但现在的我倒宁愿把他的絮叨视为老年人爱才惜才之情真挚的流露。
爱克曼原著三大本,朱光潜只是摘译。不解渴的书虫或研究者们不妨去追读全本,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兴许这样的篇幅也正合适吧。
2024年9月17日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