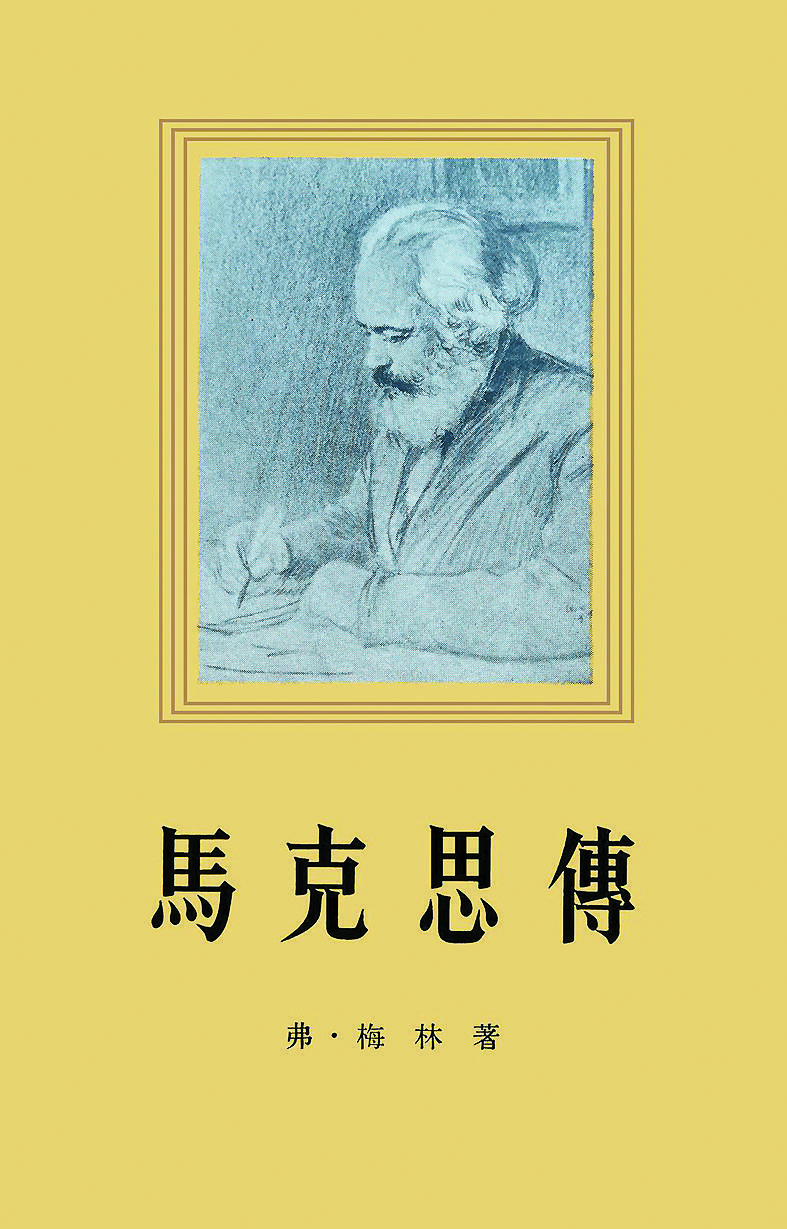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9-16 第28085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情感·探索·寻找
《人类的明天会怎样?——汤因比回思录》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冰晶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广智记得美国思想家、梭罗的导师爱默生说过:“阅读乃属于个人的孤独行为。”是的,读他的学生梭罗的世界性名著《瓦尔登湖》,然也。其实,阅读者于频繁的联绵牵引中,或可营造出一个蕴藏于他心中的大千世界,凝聚成历史的印迹。这于文学然,于史学亦然,因为两者同在一个星空下,告诉世人真实的历史,是他们共同的意愿。
近年来,笔者自谓“徜徉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学步,半与艰辛相连,半与安心相翩,如此而已。阅读是我近年来的“个人的孤独行为”,在此试将阅读书事之所得,披露于众,以望能与读者朋友有会心默契的时刻。
让情感驻留在历史中
很多年了,一直喜爱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你可以悠然地打开书页,朝飞暮卷,雨丝风片,就会读到先生于1921年写的诗《生命之窗的内外》:“是诗意、是梦境、是凄凉、是回想?缕缕的情丝,织就生命的憧憬。大地在窗外睡眠!窗内的人心,遥领着世界深秘的回音。”诗人的情感浸润于文字中,给读者以无尽的联想。
近读作家陈丹燕寄来的新作《告别》,她30年壮行,以灼热的情感流露在完美的“地理阅读”中,读完了爱尔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塞尔维亚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那可是欧洲20世纪小说金字塔尖上的两部小说,从中领略到可触及的世界与可感知的世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融合,浑然一体,对丹燕而言,这实在是最难忘的阅读经历,不管是在拉扎尔大公的修道院里还是在都柏林的街头。丹燕于《告别》一书的情感因素,感染了万千读者,也影响了书评者,于是我就以“缕缕的情丝,织就生命的憧憬”为题,为她的《告别》书评,落墨为文。
是啊,情感具有通世的感召力,情感史也逐年奋进。回望20世纪西方史学史,现代西方新史学一路凯歌行进,70年代以降,西方新史学涌动着新的史学潮流,呐喊着“转向”,微观史学因反省当时史学弊端而生,新文化史因打 着“文化转向”(语言学 转向)而长,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着历史学的堤岸,在“还有什么不是文化史”的年代里,一切皆被文化史掩盖着。有趣的是,催生情感史的茁壮成长,不正是有新文化史的雨露滋润吗?1985年,美国历史学家彼得·斯特恩斯和卡罗尔·斯特恩斯夫妇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提出了“情感学”(Emotionology),可谓是当代情感史研究的拓荒者,这自然是情感 史的“启蒙时代”,它作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还是要到了新世纪之后。行至2010年,25年过去了,由美国情感史先驱者芭芭拉·罗森宛恩作出了“情感史的问题与方法将属于整个历史学”的预言,五年后,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得到了验证,情感史被列为大会四大主题之一,至此,情感史登入大雅之堂,终于成为当今西方新史学的一个流派,为国际史学界所认可,该年或许是情感史研究作为一门学术体系奠基的一年。如今情感史研究在我国也悄然兴起,正方兴未艾。
情感史前程未可限量。在学界译事中,有贤者认为译书的过程不是硬梆梆的文字转换,也是译者与原著的一次思维与心灵的对话,倘如是,那学界史事即历史研究,更非昔日的“消灭自我”或“无色彩”。在情感史家看来,遵循新史学之跨学科路径,反叛上述陈言,在感性与理性的贯联中耕耘,让情感驻留在历史进程中,洒于天地之间,成为永恒的、有温度的记忆,永不消逝——这就是情感史的宗旨。
在不断地探索中求新
壬寅岁首,我惊喜地读到了汤因比(1889—1975)的《人类的明天会怎样?——汤因比回思录》(以下简称《汤因比自传》),他又再次浮上了我的心头。翻看汤氏传内与传外之作,他86岁的生涯给人们留下了多少回忆:生于雍容华贵的维多利亚王朝时代,有一个蒲公英吹拂过的童年。肯辛顿公园、皇后大道、马车与动物园、《曼彻斯特导报》记者、东方列车上的遐思、“一战”与“二战”时英国外交部智囊、12卷本思辨性的《历史研究》巨作、和平战士、史诗性的《人类与大地母亲》等等。1959年我在复旦历史系读大一时,就阅读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上册(索麦维尔节本),就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历了汤因比从被批判的“反动史家”,到被誉为西方史学大师、近世以来最伟大历史学家的过程。
我个人从业西方史学研究久矣,起步于个案研究,最初是希罗多德,尔后就是汤因比,古今各一,钩贯隐通,互补益彰,对后者的关注尤甚,在我学术生涯的各个时段,皆有研究汤因比史学的篇什。学术研究的创新,需要新材料的发掘,又要视角的转换,比如汤因比史学研究的深化,近时由于译界的发力,被我新见的史料不少,而“视角的转换”,即是“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是我们对待西方史学的“视角”,对汤因比亦如是。为此,我借为《汤因比自传》写序的良机发问:汤因比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简言之,汤因比留下的学术文化遗产,犹如大海,以我个人微薄之力,只能是“以蠡测海”:汤因比在探索世界文明的版图时,进行个案剖析,创造了出众的“世界文明三种模式说”;又跳出西方,疏离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发现了一个别样的“新东方”,为探索中国文明而锲而不舍。他博观而圆照,从思辨走向叙事,从《历史研究》到《人类与大地母亲》,对世界文明和人类未来发出过“警世良言”,其前景即便是微光,他也把“希望的微光”放在心间,从不舍离。正如他的孙女波莉·汤因比之言:“我的祖父为我们树立了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希望而非绝望的榜样。”
诚哉斯言。我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读汤因比的书,迄今已逾一个甲子。把汤氏之书读透、读通,读出汤氏文明研究的寻根究底,读出世界文明发展的恢宏气势,读出人类文明进程的交流互鉴。于我、也于学界同仁而言,求索无止境,永远在路上。
寻找不该遗忘的角落
为《汤因比自传》一书作序,翻箱倒柜,书架中看到了醒目的汤因比的《中国纪行》,不经意间发现了德国弗兰茨·梅林(1846—1919)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原作是篇长文,中译者李康,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初版,我收存的是复印本,纸已泛黄,有年头了。该书出版说明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弗兰茨·梅林的名字对于我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名著《马克思传》早已译成中文了……此是一篇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60多年来,历史唯物主义在所向无敌的国际工人运动中获得了辉煌的证明。因此我们认为梅林的这篇文章现在仍有现实的意义,值得向读者推荐。”自1958年至今,66年过去了,梅林的这篇佳作,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也使我想要放开眼界说开去,回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似光风霁月,横空出世,随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亦同步诞生,留下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为后世所继承和发扬,这可称之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简称“经马”)。其后经历180年,它的“谱系”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四个分支:
1、欧洲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简称“欧马”)。
2、自1917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简称“苏马”)。
3、自20世纪20年代萌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简称“西马”)。
4、与上大体同时诞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简称“中马”)。
观今现状,“经马”的研究十分看重,且有重大成就;“苏马”的研究,前几年也有突出的成绩;“西马”的研究,正以蓬勃之朝气,势头正旺;“中马”是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整体的还是个案研究,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令人遗憾的是,“欧马”的研究恰是个被学界所遗忘的角落(领域)。19世纪下半期,欧洲产生了以德国弗兰茨·梅林为代表的第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学家,其中还有德国的卡尔·考茨基、法国的保尔·拉法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和俄国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他们中有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有的是他们的学生,有的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在那里,有太多的业绩需要传颂,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梳理,有太多的疑案需要辨析。历史表明,这一批欧洲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曙光初照的年代,高举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实践和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华章,其地位至关重要,我们怎能把他们遗忘,或任由史实被雾霾所遮掩呢?
由此悟到,为了推进学术事业的发展,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当要不畏艰辛,奋发为之,发现、再发现这些被遗忘的角落,在史学的莽原上,不断地开辟新的园地。
进而遐想,情感——探索——寻找,在无意中可以串成一条项链,彼此牵系,相互接续。一个文史写作者倘能以诚挚的情感去探索世界,并进而寻找到事物的真相与真理之所在,诚至所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