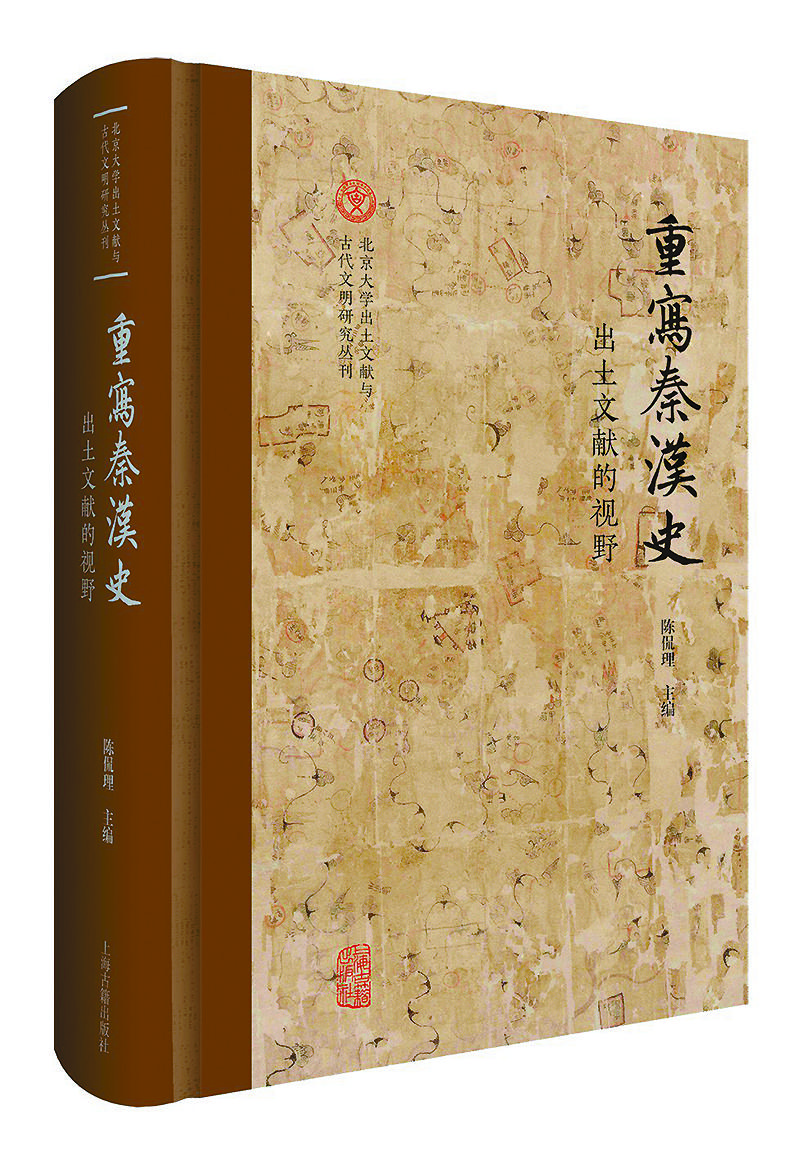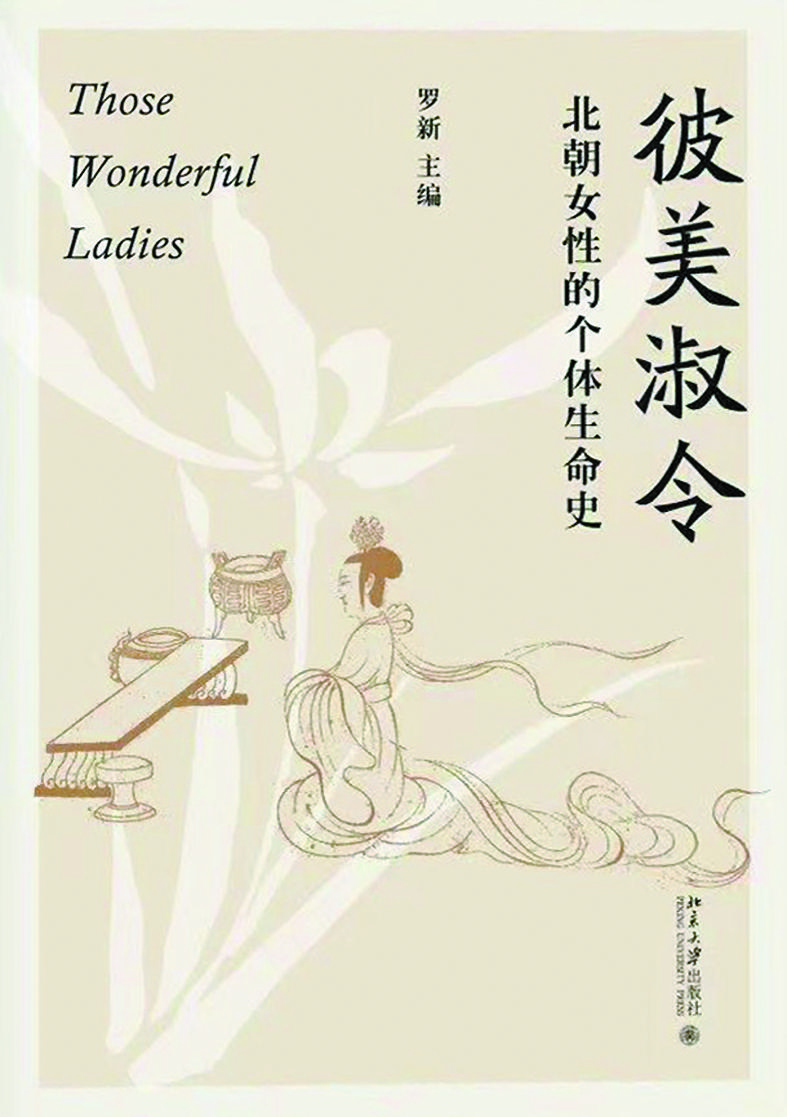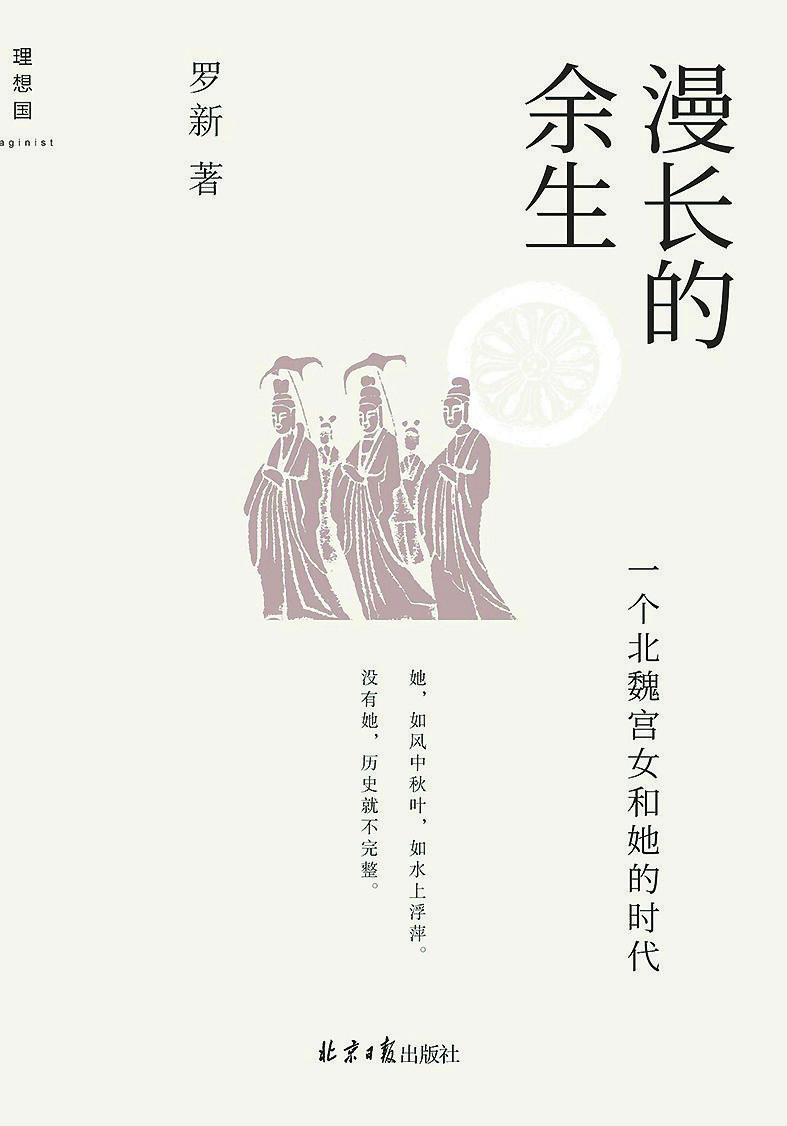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9-12 第28081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出土文献研究,打开历史叙事的另一种可能
《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 陈侃理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池骋历史书写如何创新,是史学界的重要议题。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基人之一,傅斯年有“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说法,将扩充史料视作促成史学进步的重要手段。而最近100多年,随着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史料确实大为扩充,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北京大学历史系陈侃理副教授主编的《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和罗新教授主编的《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就是两部尝试超越老套路,围绕出土文献,对历史进行“再书写”的新著。它们既体现了当代学者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新思路和新进展,也为突破传统的历史叙事打开了另一种可能。
价值:从“平等对话”到“图景重建”
提到“文物”,一般人最容易想到的是青铜器、玉石、瓷器、雕塑、书画等。这同我们的日常经验有关。我们逛博物馆、艺术馆时,它们都是常见展品;翻阅相关书籍,也多有浓墨重彩的介绍。与这些直观且便于陈列展示的事物相比,出土文献就很难进入公众视野了。可以设想,倘若一座博物馆里尽是简牍、帛书、墓志、碑铭,那么普通观众大概率会看得一头雾水,“劝退”效果十足。但是对专业人士来说,就如同老鼠掉进米缸,幸福感拉满。因为他们深知,出土文献之于历史研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我国古代即有以青铜器铭文和石刻碑碣等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它由北宋欧阳修开创,历经数百年,在清代乾嘉学派手上蔚为大观,涌现出钱大昕、毕沅、翁方纲等一众大师。不过,金石学的宗旨是“证经补史”,即证明儒家学说,为正史查漏补缺。这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卫道士,学者再努力,也不可能突破这块天花板。因此,无论本体还是方法,金石学都跳脱不出传统套路,构不成一门独立学科。现在普遍把金石学视作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既为“前身”,和真正的考古学之间就还隔着一道墙。
第一次试图推倒这堵墙的,是大学者王国维。时值清末民初,郑州、安阳一带发现大量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王国维就是最早投身破解甲骨文并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期间,王国维开设《古史新证》课,倡导“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指“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两者互相印证,互相阐发,有助于解决上古史中的诸多谜团,如夏朝是否存在、殷商都城的位置及商王世系等。
二重证据法赋予出土文献独立价值——它不仅仅是现有传世文献的补充,更是获得了与传世文献“平等对话”的资格,从而推动历史研究。凭借解释力强等优势,二重证据法成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本范式。
晚清以来,越来越多在地底沉睡的文献重见天日,居延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在二重证据法“加持”下,出土文献摆脱了金石学的附庸地位,自立门户。对此,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张固也《先秦诸子与简帛研究》等新著均有阐发。
出土文献还有优越于传世文献的地方。像典籍、正史之类的传世文献,具有浓厚的“人为建构”色彩,渗透编撰者的心机。而出土文献常常未经斧凿,保留原生态。这是否表示出土文献更接近历史原貌?不可简单论断,但至少提供了主流以外的叙事,让我们知道经典文本不止一个系统,正史不等于历史真相。举例而言,马王堆帛书《老子》、郭店楚简《老子》均和通行本差异甚大,对考察老子学说的源流意义重大。考古学家从海昏侯墓中发掘出失传1800年之久的《齐论语》简牍,学术价值亦不言而喻。
可见,辨别传世文献的真伪只是出土文献的功用之一,它更像一台“时光机”,帮助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按照葛兆光教授的设想,出土文献加典籍记载,再配合历史学家的体验和想象,使我们能够对古代图景进行最贴近和最稳妥的重建。而从前辈学者的“平等对话”到当代学者的“图景重建”,路径的演进正体现了出土文献无可替代的作用和二重证据法的持久生命力。
格局:在腾涌的烈焰旁“重写历史”
数十年来,在用出土文献进行图景重建方面,中外学者取得了诸多进展,有的步子迈得还很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李峰在《西周的政体》一书中抛开真伪难明的“上古典籍”,利用铜器铭文研究周代政治和官僚制度。李峰的另一部著作《西周的灭亡》综合运用考古发现、铜器铭文和传世文献,考察西周的解体过程。两部著作均令人耳目一新。
作为出土文献的“爆发区域”,秦汉史的研究成果更为丰赡。
在传统史学中,秦汉史本就占据独特地位。“前四史”里的《史记》《汉书》《后汉书》,都属于秦汉史范畴,它们塑造了两千多年来国人对秦汉时代的基本认知。现代历史学家固然可以在视角和方法上创新,但原材料依然脱不出这三部大书,钱穆、吕思勉、翦伯赞等人的《秦汉史》莫不如此。这决定了他们的书写或有新意,却难有飞跃。
好在不断涌现的出土文献改变了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况。当代学者掌握的材料已经远远超出旧史,换言之,我们能看到被司马迁、班固、范晔等舍弃、或连他们也未曾看过的材料。这为“重写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侃理主编的《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对此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在序言里,陈侃理概括了出土文献研究结出的硕果。当前,秦汉出土文献的总字数以百万计,涵盖屯戍、行政、经济、礼仪等各个方面,“时代自战国末以迄东汉晚期形成完整序列,地域分布从西北边境扩散到大江南北,制作、抄写和使用者下到戍卒、小吏,上至王侯显贵”,其丰富程度远超外界想象。尤为重要的是,经过几代学者的整理、考订、阐释,“出土文献已经进入了秦汉史的主流论述,新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用上了简牍资料”。
不过陈侃理坦言,研究方法尚有改进空间。时至今日,一些学者仍未跳出“证经补史”的窠臼,似乎出土文献只为印证传世文献和主流论述而存在,若两者发生龃龉,则削足适履,使之强行合拍。
幸运的是,得益于前辈的开拓、资料的喷涌,加上更系统的教育,年轻一代学者的视野和格局已大为拓展。陈侃理本人就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青年学者,此次主编《重写秦汉史》,更是汇聚众多80后学人,来了一次“集体巡礼”,展现出中国史学界后浪推前浪的勃发景象。
全书共九章,每一章的撰写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一线学人。他们分别从文字发展、文书行政和律令法系、徭役和军事制度、政区地理、信仰世界及时间秩序等维度,勾勒出过往秦汉史研究忽略的面向。其中尤其值得深思的,是陈侃理在序言里揭示的,随着复杂的细节从出土文献中喷涌而出,很多既存事实不再不言自明,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张力也越发彰显。这对于今人在大一统迷思之外,开辟重新审视秦汉史的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这样浩大的工程绝非一本著作所能完成,毋宁说,书名“重写秦汉史”是一种展望,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诚如陈侃理所言:“本书仅代表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研究蓬勃发展之时,一部分目击者的视角和思索——如同站在喷发中的火山旁边,观察烈焰腾涌、岩浆奔流,想象未来将会升起怎样的地平线。”仅仅是描摹这幅壮阔绚烂的前景,已足以令人向往。
意义:为“被消音”的个体找回公道
有必要指出,学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照,搜寻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差距,并不是为了推翻千百年来的定论。出土文献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打破一元化的历史叙事,延展出更多样的视角和认知,从而走出“唯一真理观”(陈嘉映语)。如果学者只是孜孜以求翻案,则相当于从这个“唯一真理观”滑向另一个“唯一真理观”,表面新颖,实则并未突破老套路。
实际上,出土文献能在多个维度为今人提供新知。以《重写秦汉史》为例,北京大学副教授田天撰写的第七章《信仰世界》,依据出土文献探讨古人的疾病观、身体观及其信仰内核,将触角伸向秦汉社会的心灵家园。这对于我们理解古人的信仰结构和精神状态是颇有助益的。
当然从整体而言,《重写秦汉史》的诸位作者更关注行政文书、军事制度、政区地理等宏观和中观层面,于微观史、个人史尚未重点着墨。其实这同样是出土文献有机会大放异彩的领域,而且往往更能引发普通人共鸣。
2022年,罗新教授推出《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上世纪20年代,洛阳出土了一方墓志,墓主人是北魏一位法号叫慈庆的比丘尼,于86岁的高龄在洛阳昭仪寺去世。传世文献里没有任何有关慈庆的记载,她的一生又实在平凡,因此墓志并未得到重视,继续湮没无闻。罗新独具慧眼,将墓志与史书、宫廷档案等结合,从历史的缝隙里钩沉线索,拼凑出慈庆的人生遭际和她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漫长的余生》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出土文献的整理与阐发,呈现出被现有材料有意无意过滤掉的小人物的命运,而这在传统史学叙事中原是常态。它让我们透过宏大叙事的包裹,看到一个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鲜活个体。
显然是意犹未尽,近日,罗新又主编了《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罗新指出,一般而言,社会上男女人口各自的数量是比较接近的,然而出现于史书里的男女比例相差悬殊。这表明,在古代社会,“女性是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历史编纂之外的”。庆幸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北朝墓志中女性墓主占比颇高,这为今天的学者将曾经遮蔽北朝女性的面纱揭开,把她们拉回历史视域提供了契机。
本书所收11篇文章,利用新出墓志,佐以石刻、史书等材料,描绘了11位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书名中的“彼美淑令”源于一位柔然公主的墓志。这位16岁嫁到东魏,担负和亲之责的公主,墓志说她“彼美淑令,时惟妙年”,活脱脱一个美丽贤淑的妙龄少女。可惜“生之不吊,忽若吹烟”,因难产或生产染病,19岁就死了,犹如一缕轻烟随风飘散。
像柔然公主这样的人,历史上不知凡几,即便贵为王孙,也终究是政治拨弄的工具。如果沦为“罪臣之女”,那就更为不幸了。在《寻找仇妃》一文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冲从一方不起眼的墓志中钩沉出北魏仇氏的灰色往事。仇氏幼年时因生父伏诛,入宫当罪奴,后来朝廷将她赐给南安王元桢为妃。从罪奴到王妃,看似逆袭,其实细究起来,仇氏一生只是被动服从,未曾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恐怕才是岁月长河中大多数人的普遍境遇。
出土文献之于微观史的意义亦蕴藏其间。如罗新所言,它们以不同于主流话语的形态,为“那些被隐藏被遮蔽被消音”的个体生命,找回了一点点公道——那是来自当代读者的观照与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