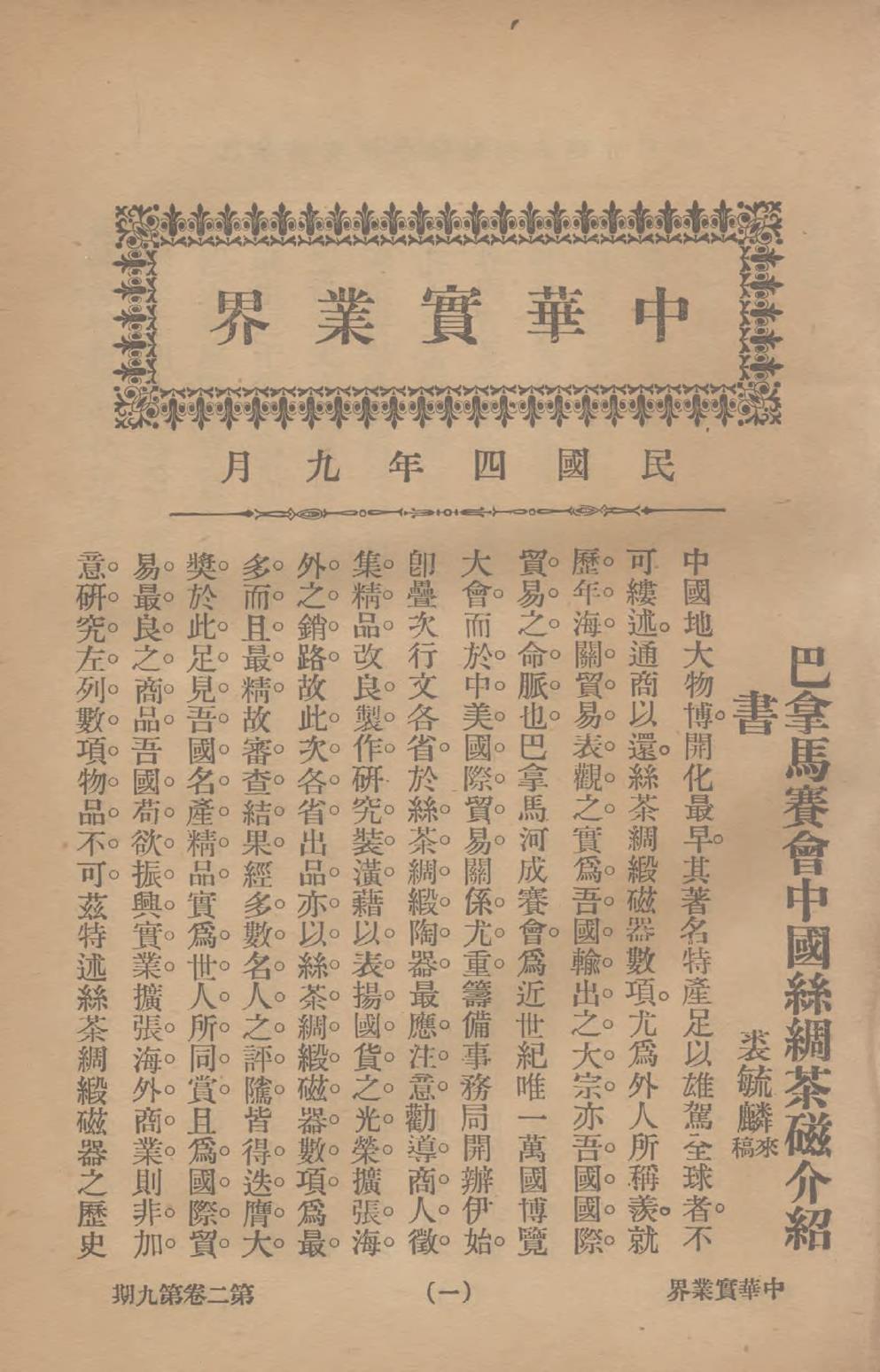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8-25 第28063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一个留美学生的思想回澜
——裘毓麐的《游美闻见录》及其他
裘毓麐像
■ 裘陈江裘毓麐(也作毓麟),字匡庐,浙江宁波慈溪人,约出生于1890年。清末入译学馆,为乙级学生,宣统元年(1909)夏毕业,后升入京师分科大学,于1913年毕业,专业为法科政治门。他所在的这一级毕业生,是中国政治学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批政治学本科毕业生,在中国近代政治学教育史上有独特地位。毕业不久,裘氏的清代史料笔记《清代轶闻》(中华书局,1915)出版。该书有友人序言六则,集合众序可知,至少到此书撰成出版前后,裘氏为人称道的是长于英文,对于西方新制度、新学说,皆能窥其奥窔,而《清代轶闻》一出,友人纷纷惊骇于其学问之博,对于国史之熟悉。不过可惜的是,其中对于裘毓麐的生平极少介绍,只是各序中提及他当时正好有留学美洲之行,可见其人于中西文化均有一定的造诣,绝非一般闭塞守旧之徒。
“学究之眼光”与“洋迷之眼光”
1914年12月,裘氏正式赴美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习政治经济学,1916年学成回国。期间的1915年2月22日—12月4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以纪念巴拿马运河开凿成功。裘毓麐正是当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其正式职务为中国驻美赛会监督处出品股股员兼农业馆主管。他在美期间留下的文字记录《游美闻见录》,及回国后不久翻译发表的诸多介绍世界各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状态的译文,均是留美的成果。不过在此之后,裘氏几乎很少再有著述发表,要迟至三十年代,偶有几篇笔记文章见诸报刊,且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向。因此,裘氏当时的连载和译文,可以作为研究近代博览会、留美学生群体和民初中外经济、科技交流等领域的重要史料。而其后期的思想转向,也可作为考察清末民初新派人物思想转折的有趣个案。
裘氏的这些著述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专门介绍。首先,是他作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亲历者的见闻,有介绍之功。1914年12月6日,裘氏正式随中国赴美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人员一起出洋。其在《游美闻见录》中称:
余赴美后,在巴拿玛会场历十五月之久,巴拿玛大博览会,实为二十世纪初唯一之大博览,规模之宏大,历次赛会咸弗及。……赴会者共三十馀国,所以萃五洲之精英,罗万国之工巧,广搜慎择,聚于一堂,凡莅会场观览者,得于最短时间遍览世界新奇之物品,藉以觇各国文化工业之消长,以收比较观摩之效。由于他完全身处当地,且未来持续在此求学,故《闻见录》从到达旧金山伊始介绍起,记录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华侨的历史与现状,巴拿马博览会的参观见闻,均可谓是第一手的现场实录。除此之外,他又利用了当时各国所编专书杂志,故除了在1915—1916年的《大中华》《中华实业界》等杂志直接介绍博览会外,归国后的1919—1921年,他于《江苏实业月志》上发表50余篇介绍各国经济、科技的译文,应也是当年介绍博览会盛况的延续,其翻译报道的密度和广度可谓少见。
在这些译文中,经济方面除了综论有关进出口贸易的《输入或输出超过之真诠》等之外,连续介绍了英国、美国、日本、瑞士、荷兰、墨西哥、坎拿大(加拿大)、澳洲、俄国等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及各自问题。在科技方面,主要介绍了工业革命时期的众多发明家和巨商的生平与成功之道,人物主要集中于英美两国。他的这些译著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而其关怀更在于希望中国能在世界经济大潮中早日摆脱积贫积弱的处境。如《游美闻见录》借巴拿马运河开凿的话头,展望二十世纪的商业的发展方向:
自去岁巴拿玛运河落成,为近世商业开一新纪元,其关于太平洋、大西洋两岸诸国影响甚巨。……列强对于吾国之国际关系,当必愈形紧逼。
鉴于当时美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突飞猛进,回顾国内却“金融紧迫,实业凋零,哀鸿遍野,萑苻时虞,国民生计,有儳然不可终日之势”,裘氏大为忧虑:
彼(列强)挟其商业政策,国民富力,操刀待割,乘时进取者,固大有人在。循自以往,恐户内蛮触之争未已,而他人已入室矣。
他愤而警告:
立国于二十世纪竞争剧烈之场,苟国民于新企业、新工艺之智识,茫无所知,而犹沿中古式诡谲侵陵之政策以为治,则国未有能倖免者也。
因此,在其著述中还有如《吾国实业不振之原因》等分析种种缘由,同时又屡有鼓吹如何提振本国经济的种种办法,可谓苦口婆心。
其次,展现了民国初年留美学生的心态和生活。裘氏在《游美闻见录》开门见山直陈,国人游历欧美各国,作评论时,“必先去其二弊”。何谓二弊?“一为学究之眼光,一为洋迷之眼光是也”:
学究之眼光,则以吾国旧礼教、旧风俗无不善,亦无一不当保存,甚至西国政治学术之可采者,亦必以吾国旧说附会之。……洋迷之弊,则适与之相反。洋迷一履西土,无殊登仙,景仰西人,无殊天人。无论西国之秕政陋俗,咸诩为美谈;无论西国鄙夫俗子,咸视为神圣。而语及我国政教风俗,似有深恨宿仇,必丑诋之而后快,一若吾国自皇帝尧舜至今,野蛮已五千年,无丝毫文化之可言者。
他作《闻见录》,虽说“不敢偏于学究,亦不敢偏于洋迷”,但其鉴于“近年以来,国人中洋迷之毒者愈甚”,批评的主要还是“洋迷”问题。
比如裘氏在文章中提醒不可偏听偏信所谓留洋经验。他指出“苟欲求世界智识,如通外国文者,不如多读西书西报,如不通西文者,亦可择译书译报之佳者读之”。他以自己初到美国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首先指出不可迷信“出洋老前辈”,其言可能反而多不切于实情。其次,如一般盲目推崇外人,称其必定诚实可信、必定慎重人命等定论也不可全信。此外,在批评“中洋毒”的留学生时,更是辛辣讽刺。他以曾遇到的一位粤籍留学生为例,称其不通中国普通方言,只能操英语相谈。而二人交谈后,更得知其粗通之国文,竟是习自游历中国有年、年老来美的英国人傅兰雅。而他在亲自拜见傅兰雅后更是大受刺激,因为傅氏也感慨:
中国近日之派遣留学生,何漫不选择至此?余亲见多数留学生,中学毫无根底,于中国内情隔膜殊甚,与一未至中国之外国人无异。即使学成,将使为中国人耶?为美国人耶?抑中国政府将为美国代造就国民耶?余不解此辈回国后果有丝毫之裨益于祖国否耶?
而有鉴于当时日本所派留学生的良好效果,裘氏痛惜中国留学界多怪诞离奇之现象,而仍无一定方法宗旨。同时批评中国留学生“在外时,既无选择去取之辨别,回国后则务以大言吓人,小试不售,即悍然归咎国民程度之不到”。故裘氏主张:“评论欧美之政教风俗,是非优劣,宜各求其实,不可随声附和,一味赞美,致未出国门者阅之,疑鬼疑神,无所适从也。盖制度法令,无绝对之利,亦无绝对之弊,而一国之大,万民之众,俶诡奇离之风俗,烦颐复杂之政教,决不人人贤良,事事优美也。”正是其“不敢偏于学究,亦不敢偏于洋迷”的立场,使得其立论虽也偶有偏激之处,但仍不失务实恳切。
第三,裘氏的著述多集中于归国后不久,此后发表的作品明显减少。又由于裘氏个人资料的奇缺,只能知道在1921年6月,他已参与了上海华商证券棉花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后成为常务理事之一;同年11月,又参与了大东物券日夜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后也成为常务理事之一,显然忙于从事经济活动。在此之后或许正是忙于经商,几乎看不到裘氏任何著述,最后一个发表高峰要到三十年代了,而其思想已明显发生了很大的转向。
钱基博和唐文治所撰书评序言中的裘毓麐
时至1933年,裘氏在《青鹤》杂志上发表了《匡庐笔记》三篇,其中自道:“近年余喜阅宋明诸儒性理等书。”同时批评“乃一二妄人,对于吾国旧有之学术,不惜出全力以抨击之。一若是类书籍,深有害于人群,碍于文化,非绝迹于国内,则决难图改革者”。这当然与其留美期间批评“洋迷”问题有着一贯性,仍主张“吾国苟欲免敌人之侵凌者,当先去学术上之奴性”,但其为学的根基,明显已非西学,而归于佛典、宋学等。
裘氏后期的学术,本可以通过其所撰《思辨广录》一书加以了解,但可惜至今难觅原书,或许该书本就未曾刊行。不过幸好可由1935年钱基博和唐文治所撰的书评和序言大致了解,尤其是钱基博的书评,名为《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实则便是向学界推荐裘氏的《思辨广录》。文章开头对于裘氏的生平经历作了一些介绍:
先生,名毓麟,匡庐其字,慈溪人。旧译学馆毕业,升入京师分科大学,以民国二年赴美,留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习政治经济。五年回国,曾为文著论欧美社会之崇势利而薄仁义,终无以善其后,而不如孔孟之道为可大可久,刊登《时报》。方以新思潮澎湃莫之省也,于是闭门读书二十年于兹,精究程朱,旁参释老,积久有得,而著为书。
钱文对于裘氏的治学经历与该书主旨作了大量的摘录与介绍,其摘录裘氏自叙治学之经历,则为“三十以前,年少气锐,事事喜新恶旧”,且“三十岁以前,固为一纯粹学校之学生,彼时所喜研究者,厥惟西儒之科学。吾国圣经贤传,尚不厝意。”而在回国后数年间,“偶得佛经读之,恍然如久处黑暗之中,骤睹光明,奇趣妙理,日出无穷,读之愈久,好之愈笃。……往年余思研国学,欲略知宋儒学之梗概,取《近思录》读之,不能得其精意。”但凭借着“读之愈久,好之愈笃”的求学精神,因而得以撰成《思辨广录》,对于近代以来中西古今学问之争,对于青年修习国学的方法,对于清代学术,对于儒释道三教会通等等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到钱基博超乎寻常的赞赏:“观其所称,见解超卓,议论中正,以聪明人,说老实话。其论不必为近十年发,而近十年之国学商兑,惟先生殚见洽闻,洞见症结,人人所欲言,人人不能言。”(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光华大学半月刊》1935年第3卷第9、10期合刊)而唐文治在序言中也称赞裘氏此书“举凡辨章国学,匡救时弊,致广大,尽精微,而会归于有用”,故在文末“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教中国、救世界之责,属望于裘君”。(唐文治:《广思辨录序》,《国专月刊》1935年第1卷第4期)
裘毓麐一生治学从西而中,由新而旧,渐渐对于中国旧籍和传统学问有着更多同情和理解。裘氏由译学馆出身,后留学美国,对西方文字、西方制度、西方文化的了解绝非停留于纸面,归国后,随着经历学识见长,却能转入宋学甚至佛典之中,可以看出其思想转变的轨迹,或可说是一位学人成熟深思的回归。裘氏能有如此思想转向,在1940年还一度引起晚年吴虞的注意,吴氏在日记中称“裘毓麐为美留生,竺信朱子”,而裘氏的思想转向与吴氏晚年自觉“考订训诂,烦琐无补身心”颇相契合。这种自民初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思想回澜,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近代反传统运动的不同面相。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