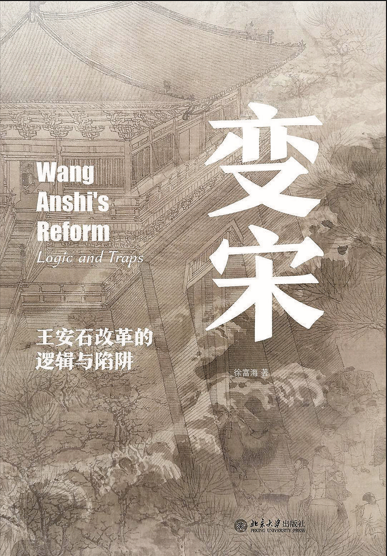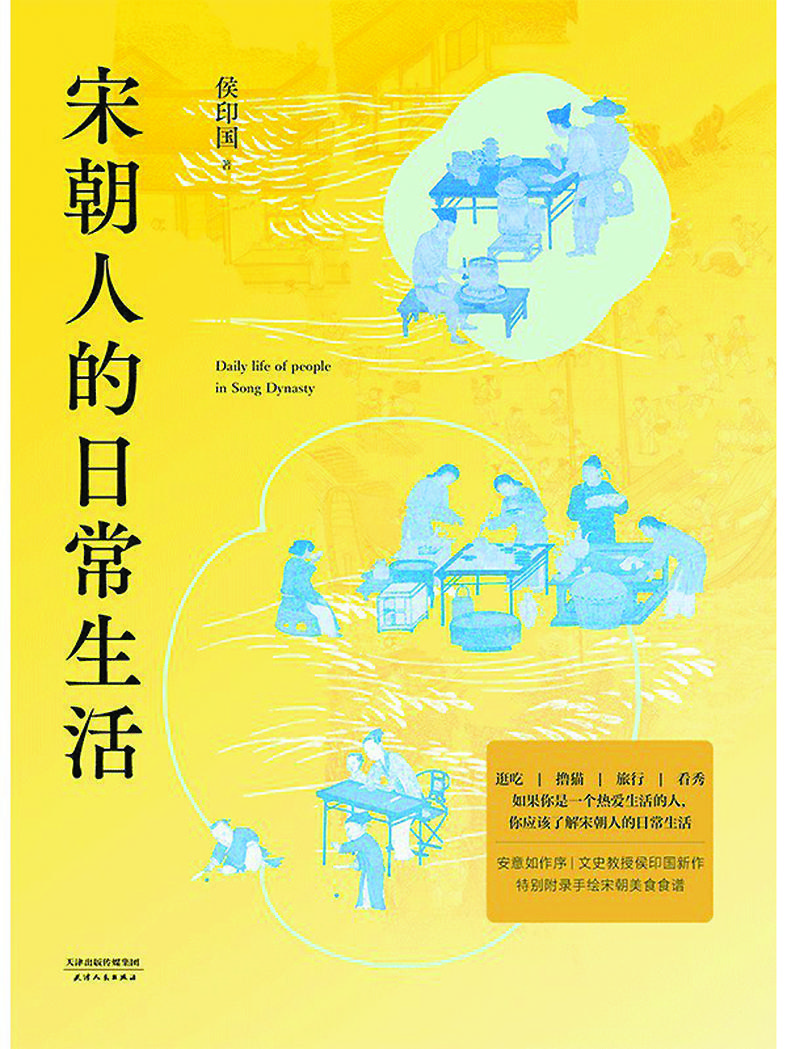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8-25 第28063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风华北宋的芸芸众生
《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 徐富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易扬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有过一句脍炙人口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千年以来,历朝历代、海内外的史学家们几乎都把北宋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根据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北宋人口已经发展到将近一亿,是盛唐时期的1.6倍,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再次追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农桑等各项事业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难怪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直言:“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朝堂上的帝王
我们谈论历代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时,《诗经》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句子,很难不闪现于脑海;但当宋太祖开国之时,喊出一句“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之后,宋朝皇帝的“地位”似乎就一落千丈,无论是开辟盛世的仁宗、革故鼎新的神宗,还是昏聩亡国的徽宗,虽然远见、秉性、能力等各不相同,但面对纷纷扰扰的朝堂争吵,全都憋着一肚子说不出的苦水,概而论之就是五个字:“万事不自由”。
这些“万事不自由”的事例,被各类历史书籍津津乐道,也将长久以来被过度神化的帝王们拉回成了“芸芸众生”。在吴钩的《宋仁宗:共治时代》里,就记录了一则宋仁宗“委屈指数”拉满的片段。有次宋仁宗被台谏官的章疏搞得很不高兴,溜须拍马的宫人便问仁宗:“(台谏)所言必行乎?”这一问就立马刺激到了仁宗的痛点,后者满腹牢骚地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俨然就是一副行事处处受限的孩童形象,可宋仁宗一点儿都不糊涂,几天之后,阿谀奉承的宫人就被随便安了个由头赶出宫去,仁宗的解释让人肃然起敬:“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可谓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
宋仁宗赋予台谏官们的“风闻奏事”权利,不仅令其自身深受“困扰”,就连他的皇子皇孙们也都“苦不堪言”。学者徐富海在其所著的《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中,同样写到了一段宋神宗的“憋屈往事”。神宗皇帝被台谏官们各种无根无据的“互喷”搞得焦头烂额,但又碍于制度设定无法对其问责,于是便要耗费大量精力,去安抚那些受到中伤却又爱耍性子的官员们,在御史中丞王陶对韩琦、曾公亮的弹劾案中,宋神宗疲于奔走在双方之间,“折腾了两个月”,才让他们逐渐消停下来。虽说“风闻奏事”不可避免地滋长了言官们的口舌之战、相互中伤,但倘若用辩证的观念去审视,正如元人脱脱在《宋史》里所说的“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身处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约束和广开言路?
宋徽宗在后代史书中饱受嘲讽,《元史续编》的作者胡粹中甚至挖苦“徽宗多能,独不能为君耳”。照理说,无知者无畏,作为朝堂上的“甩手掌柜”,宋徽宗理应过得万般自由,可在美国学者伊沛霞的《宋徽宗:天下一人》中,他和列祖列宗一样,也奈何不了那帮整天吵吵闹闹的言官,满肚子都是倒不尽的委屈。为了竭尽全力维护宠臣蔡京,宋徽宗不得不顶住满朝文武的压力,力挽狂澜。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无奈地三次贬谪蔡京,并且“每次替代蔡京的都是批评他的人”,可见即便昏庸如徽宗,在与宰臣共治的政治制度下,也还是处处受到掣肘,有着不少摆不平的朝堂事。
乡野里的臣子
北大教授罗新在其著作《漫长的余生》的扉页,手书过这样一句话:“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时代的主流。”令人颇为感怀。学者赵冬梅的《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在论述司马光的成长经历、人生阅历、政治履历之前,先不惜笔墨地介绍了他那些“以五代衰乱不仕”、一直隐于山林的近世祖先,以及北宋建国后,在司马家族内部逐渐清晰起来的宗族分工——和当时很多出身乡野的宗族一样,他们都试图举全家之力,将那些会念书能考试的孩子,送上光宗耀祖的仕途。以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为例,兄弟三人中,老大司马浩、老三司马池负责读书应举,老二司马沂则扛起耕地畜牧的重担,负责管家养家;然而生活的重担,让司马沂年仅32岁就撒手人寰,于是老大司马浩就放弃读书、接过担子,殚精竭虑培养司马池一人科举入仕、光耀门楣。司马家族的分工故事,在北宋历史上并非孤例,蔡襄、梅询等出身乡野的平民官员,也都是如此走上科举之路。根据相关史料,平民子弟在北宋官员中的占比达到45%,这又何尝不是缔造北宋清明政治的重要基石?
“乡野”是不少北宋官员迈入朝堂的人生起锚地,同样也是他们政治受挫时的情绪缓冲地。苏轼40年宦途大起大伏,他曾讲过一句“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其豪迈旷达的人生写照。事实也确是如此,当后人为苏轼波澜壮阔的一生著书立传时,总是不免谈及他那些游走于乡野之间的平民之交,这其中有酒监、药师、道士、和尚、琴师、大夫、农夫等等,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在学者李一冰著述的《苏东坡新传》中,多次提到苏轼的一位出生贫贱的同乡至交巢谷,在苏轼被贬黄州时,巢谷奔赴而来,一边充当苏轼孩子们的塾师,一边还亲自为苏家充当家厨;当苏轼再贬儋州、苏辙被贬龙川时,年过古稀的巢谷复又徒步寻访苏家兄弟,并最终死在了寻访途中。值得一提的,“二苏重入政坛,官高爵显,巢谷从不问讯”,如此堪称“至情至性在乡野”。
《苏东坡新传》里还记录了不少苏轼贬谪时交往当地乡野的有趣故事。比如在黄州,苏轼特别垂涎刘唐年家名为“为甚酥”的自制煎饼,带着家人外出郊游,都想着写诗讨要几块:“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又比如在儋州,有次行歌田间,一位老妇人对苏轼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苏轼不仅毫不生气,而且往后每次见面都调侃老妪为“春梦婆”。这也正应了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里所作的概括:“(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街市中的平民
在《宋仁宗:共治时代》里,作家吴钩还记录了一段源自起居注的对话。面对民间酒楼的宴乐之声,内廷宫人十分羡慕地对宋仁宗说:“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宋仁宗没有顺着接下话来,而是答道:“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的明君形象跃然纸上,与北宋皇宫一墙之隔的喧嚣街市,也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出来。
澶渊之盟的“红利”,为北宋谋得了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难得机遇,时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都生动记录了北宋市井的鼎盛繁华。以《东京梦华录》中与吃食相关的记录为例:瓠羹店(肉汤店)“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不可谓不壮观;饼店“唯张家、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不可谓不兴盛;鱼行“每日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不可谓不忙碌。这些场景即便放置于今日,与那些令人趋之若鹜的“网红店”相比,都可迅速“出圈”。
曾经为《东京梦华录》做过译注的文化学者侯印国,还出版过一部《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全书的起始之章就名为“吃货”,记叙的也正是宋朝令人眼花缭乱的吃食,其中又以夜市小吃为甚。包括侯印国在内的不少学者都认为,是进入北宋后日趋瓦解的坊市制度,间接热闹起了夜幕下的街市。循着《东京梦华录》里描绘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盛况,以及书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吃食,侯印国挑选其中几种作了详细介绍,比如他提到的旋炙猪皮肉、煎衬肝肠,观其食材和制作方法,几乎就是“北宋牌”的烧烤和炸物,堪称千年前的“热量炸弹”;又比如当时颇为流行的砂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荔枝膏等等,俨然就是如今各种茶饮、果饮的“鼻祖”,由此可见,被我们奉为“快乐水”的消暑冰饮,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惠及我们的祖先了。
无独有偶,写作《宋仁宗:共治时代》的吴钩,也出版过一本名为《好一个宋朝》的通识读物。在书中,吴钩不仅考证出深受老饕欢迎的火腿、刺身、汤圆、爆米花等美食和小吃,“都是发明或流行于宋朝”,而且还谈及了“吃喝”之外的“玩乐”,铺陈了北宋街市上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娱节目。特别是在元宵节当天,说唱、歌舞、魔术、杂剧、傀儡戏等表演轮番登场,镜灯、水灯、日月灯、马骑灯等多种灯品各出新奇,就连我们常规认知中“躲在深闺无人识”的女子们,也都精心打扮、穿金戴银,出入于华灯之中,享受着这一年一度的“民间狂欢节”。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张生彩鸾灯传》《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宋话本小说,都把佳人相约的故事情境,设置在了元宵之夜的街市上。
北宋大儒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里形容元宵之夜“花市灯如昼”。繁华的街市和熙攘的人群,生动展示着北宋一朝富足昌盛、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落灯后、年事毕,“士人攻书,工人返肆”,元宵的街市又恢复到了往日,但作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北宋的辉煌却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