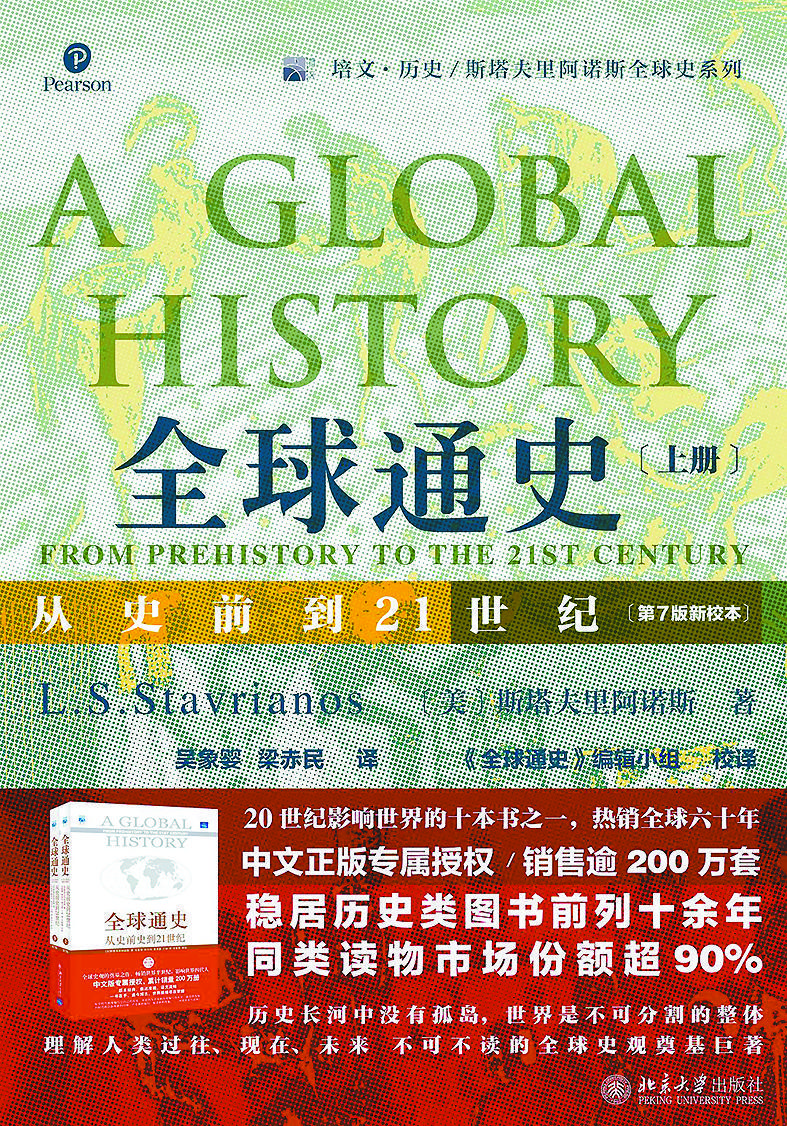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8-07 第28045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葛兆光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骋华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主编、汇集20多位中青年学者参与撰稿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于日前出版,并引起广泛讨论。全书分三卷,摒弃一切“中心主义”,探讨人类与文明的起源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讲述全球史中的帝国、战争与移民、商品贸易与物质交换、宗教与信仰,疾病、气候与环境。这套书既弥补了中国历史学家在全球史著作中“缺席”的遗憾,也体现了一代中国学人的视野和抱负。
作为“启蒙读物”的《全球通史》
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读的第一部全球史著作是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本书初版于1971年,1999年推出中文版,恰逢千禧年临近,给当时的中文世界带来了一种类似“敲开新世纪大门”的全新体验。我至今记得2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阅读这本书时激发出的奇思妙想。原来,汉朝与匈奴之间超过百年的征战,曾经导致草原部落大迁徙,随着一波又一波“蛮族”从蒙古高原一路向西涌入欧洲,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耳熟能详的历史,竟产生过这般神奇的“蝴蝶效应”,实在是震撼。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写法也与众不同。他摒弃了中国人习惯的、源自前苏联史学的“上古—中古—近现代”三分法,而是以1500年为界,将人类历史分为两大阶段,即1500年前各大文明圈相对孤立的世界和1500年后开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如此大刀阔斧又清晰明确的划分,令人耳目一新。
从学识、眼界到叙事方式,《全球通史》都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门,成为了很多人的“全球史启蒙读物”,难怪它风靡一时。此后,这本书多次出修订版,而图书市场上与全球史相关的书籍也越来越多。宏观层面,有海洋的全球史、贸易的全球史、疾病的全球史;物质层面,有糖的全球史、棉花的全球史、茶叶的全球史……不过,像《全球通史》这样全局性的通史著作还是偏少,而随着斯塔夫里阿诺斯于2004年去世,这本书已经不可能更新了。算起来,最新一版的《全球通史》距今也有20多年了,期间,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研究日新月异,映照之下,这部书有些落伍了。
通史偏少是有客观原因的。首先,通史写作本就体量庞大,涉及面又十分广泛,更何况还是全球史,这对作者的脑力和体力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在学科划分细密、专业壁垒森严的当下,单个历史学家想掌握如此庞杂的知识,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位历史学家如果立志写全球史,势必借助各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此,他理应具备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观”,能把千差万别的专业知识融会贯通,纳入整体性叙事,以免“拼盘”之感。
这绝非易事,因为它不仅考验作者的知识面、知识量,更考验作者的历史观、价值观。《全球通史》就蕴含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历史观——他之所以将1500年作为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帷幕徐徐拉开,世界各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格局逐渐形成。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是斯诺夫里阿诺斯看重的。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国内一般把全球史称作世界史。追根溯源,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始于晚清,由林则徐《四洲志》、徐继畲《瀛寰志略》、魏源《海国图志》发其端,至20世纪中叶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问世乃成型。20世纪90年代,吴于廑又与齐世荣主编六卷本《世界通史》,作为高校教材之用。如今,不少高校设有世界史专业,属于一级学科。
传统的世界史研究偏重于政治、文化、经济等宏观层面,而且往往以国家、民族为叙述主体,成为葛兆光教授所说的“国别史的拼合”,如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日本史等。国别史自有其意义,不过,民族国家毕竟是晚近的产物,用今天的滤镜映照过往的人事,难免变形失真。
传统的世界史研究还有“以己度人”的毛病。举例而言,中国人信奉“大一统”,认为统一代表治世,分裂意味着乱世。放在中国的语境里固然没问题,但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两河流域兴起过赫梯、亚述、巴比伦等古王国,它们都未曾完全征服该地区,难道能说两河流域一直处于乱世吗?其实,古代很多帝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与“大一统”差异甚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晏绍祥就指出,在波斯帝国,地方总督拥有很大自治权,这同实施郡县制、皇帝能牢牢控制地方的秦汉帝国很不一样。
当然,以己度人实为通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就批评过所谓“欧洲中心论”。巴勒克拉夫指出,西方史学界总是习惯于把欧洲(主要是西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轴和动力,有意无意地贬低欧洲以外地区的文明成就,认为它们都是需要欧洲人拯救的“野蛮”地区。
为打破欧洲中心论,巴勒克拉夫倡导“全球史观”。他主张历史学家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把世界上的每个民族、每个文明放在平等位置上,进行公正的叙述。巴勒克拉夫开全球史之先河,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是对其主张的实践。近年来引进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企鹅全球史》,亦可作如是观。
放置于这条脉络中,《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一方面,这套书由葛兆光、梁文道策划,20多位中国学人共同撰稿,“全华班”阵容打造,自然能够免疫于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撰稿人也在尽量避免滑向“中国中心论”。诚如葛兆光所言,全球史瓦解“中心”,强调“联系”,不管以哪个区域为中心,都违背了这一理念。
不搞“中国中心论”,但要“从中国出发”。区别在于,前者把自己当作单一主体,后者则承认存在多个主体,只是我在自己的主体位置上观照全球。这是因为人总是从特定角度看待和认识世界的,没有人(哪怕汇聚优秀学人)可以全知全觉,做到完全客观。只要尊重各自的主体性,在主体平等的基础上展开论说,就不会重蹈以己度人的窠臼。我想,葛兆光教授说全球史写作应该“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便蕴含着这个道理。
于是我们看到,撰稿人通常从与中国相关的事物讲起,层层扩展,编织成繁复浩荡的多声部交响乐。在这部交响乐中,中国不一定始终是主角,但发生的一切都和我们息息相关。例如,尽管在船队规模、资源投入、航海技术等多项指标上,郑和下西洋“秒杀”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探险行动,但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却是后者。中国错失了历史机遇。不过,明清时期,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奠定了“白银时代”;美洲的玉米、土豆、辣椒也在中国广为栽种,养活了大量人口。可见,中国从未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
联系与交流是全球史的主旋律
无论是在书里,还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葛兆光都反复强调:“全球早就彼此联系。”这番用心,放在当前的语境中颇耐人寻味。
40多年来,全球化可谓高频词,尤其是随着“中国制造”遍布世界,互联网又无远弗届地延伸,人们一度乐观地以为“地球是个村”“世界是平的”。可事情总有两面性——有全球化,就有逆全球化。近年来,欧美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建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墙。也有人试图将特定区域说成人类文明的唯一发源地,其他古文明则一概被贬斥为“伪史”。
在我看来,《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正是形形色色逆全球化思潮最好的解毒剂。它致力于寻找和重构历史中有机的、互动的关系,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综观人类历史,联系和交流是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两河流域(又称“新月沃土”)的人们发明了小麦种植技术、青铜铸造技艺、楔形文字;古埃及人创造了太阳历、莎草纸、十进制计数法;中国古人贡献了丝绸、纸张、火药;波斯人、阿拉伯人则极大地推进了造船和航海技术。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精神领域则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中国虽自成一体,形成辐射亚洲东部的儒家文化圈,但也深受佛教影响。
古代的全球化到什么程度呢?罗马贵族穿着中国的华美丝绸,享用东南亚的香料;汉朝的皇家园林上林苑里,种植着西域的奇珍异草。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如数家珍地介绍唐代舶来品,从飞禽走兽到动物植物,琳琅满目,活色生香,而且这些物质已然渗入日常文本。白居易诗“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其中的“瑟瑟”,原指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呈天青色,用来形容碧波十分贴切。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长期交流带来的互通有无、相激相荡,而是每个地区各自为政、孤立发展,今天人类恐怕还生活在原始状态。美洲就是例子。大约一万年前,因海平面上升,淹没了连接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的白令陆桥,美洲与世隔绝。美洲没有铁器和大型牲畜,农业、手工业落后,因而尽管美洲人创造了像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古文明,但生产力水平一直很低。
15世纪末,欧洲航海家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路,将美洲纳入全球化进程。欧洲人给美洲带去马、牛、羊等家畜,以及小麦、甘蔗等农作物,美洲的玉米、烟草、咖啡等输入欧洲,进而传遍全世界。这叫“哥伦布大交换”。大交换过程中固然充斥着暴力和掠夺,对此,全球史从不避讳,但研究者同时会强调,它在客观上塑造了现代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史研究者普遍把1500年设为标志性节点。
当然,《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不可能尽善尽美。葛兆光教授坦言,把如此庞杂的内容整合起来要克服诸多障碍,当前的架构设计和内容撰写均属“权宜之计”。此外,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由于撰稿人较多,虽然经过打磨,仍难免出现文风、节奏不一致的情况。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广阔的未来正待中国学人们继续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