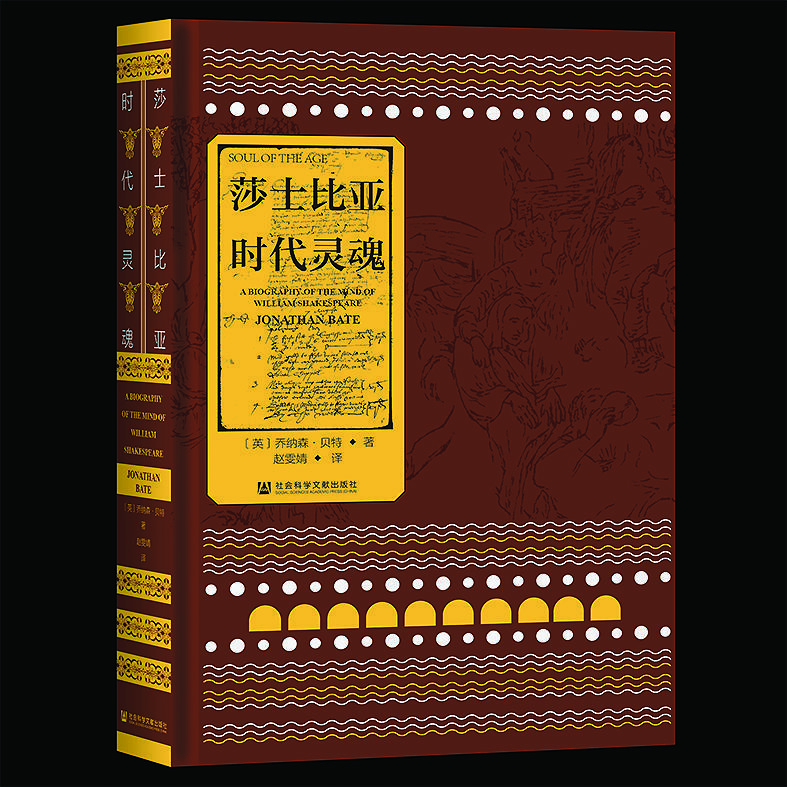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4-23 第27,939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作为果实的灵魂:莎士比亚的思想版图
莎剧中的人物
■许小凡“像果子挂在枝头吧,我的灵魂/直到树木枯死!”在莎士比亚晚年的传奇剧《辛白林》结尾,罗马青年波塞摩斯与不列颠公主伊摩琴之间的误解得到澄清,爱人相拥在一起,懊悔的波塞摩斯发出这样一声长叹。莎士比亚可以说是一位“充满灵魂”的写作者,剧中随处可见对灵魂的指涉。而阅读莎士比亚,也如同从思想的果园中摘取一颗最为饱满的完整果实,在它的汁液之中,蕴藏有关于早期现代英国思想史的一整套遗传信息。
莎士比亚的具体生平充满空白和争议,这也是传记写作者必须面临的挑战,但如果我们连一位传主是否真正跛脚(见十四行诗第三十七首)都不完全清楚,那么传记作者反而有可能获得一种自由,让他不致迷失于生平事实的丛林,这也往往通向一种更具想象力与新意的传记写作形式。作为英国重要的学者、批评家与传记作家,乔纳森·贝特的《莎士比亚:时代灵魂》(2008,中文版2023)与其说是莎士比亚传,不如说是以莎士比亚的文本与身世为线索,串联起一个时代的思想地图,而用传记方法写历史,这是普鲁塔克留给莎士比亚、又从莎士比亚递到贝特手上的遗产。为一个时代的思想立传,同时又具有文本的具体性,这是这部传记的迷人之处。
贝特沿用了莎士比亚的同代人本·琼生对莎士比亚的描述:“时代的灵魂。”这一描述首先是特指性的。它与贝特此前《莎士比亚的天才》(1997)一书所强调的莎士比亚跨越时代的普遍性不同,它更着眼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如何是它自身时代思潮的果实,又如何能安放在他时代的世界图景之中。与在它之前不久出版的另一本传记、斯蒂芬·格林布兰特的《俗世威尔》(2004,中文版2007)有些类似的是,它们都关注莎士比亚与给定历史阶段之间的互动,都基于大量的研究和史料支持,但格林布兰特所着眼的莎士比亚的“世界”(《俗世威尔》的英文原书名字面意义为“威尔在世界之中”)更多指莎士比亚成功周旋其中的世俗、物质与政治现实,而贝特更加关注的,是莎士比亚所继承、表达和对话的一套思想传统——也即题目中的“灵魂”一词。
贝特同样致力于还原这一灵魂所运行其中的时代及其变动的历史,但他尤为关注的还有莎士比亚身处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个世界,是那幅著名的迪奇利肖像中伊丽莎白脚下的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图,及领土之外“不稳定的法国、罗马天主教统治下的南欧、奥斯曼帝国势力下的地中海”和沿岸地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竞争。这样一副逐渐明晰的世界地图,为诸如《奥赛罗》《暴风雨》乃至莎士比亚同代才子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等文本带来较新的解读。同时,贝特也描摹了莎士比亚同时置身“两个世界”的历史图景:他灵巧地腾挪于乡村与城市、民间与宫廷、文学世界与世俗成功之间,又身居新教权威的树立和处死查理一世、宗教“奇迹剧”“神秘剧”与世俗剧院的繁荣、托勒密的古典宇宙秩序与对哥白尼的普遍接受,以及从都铎到斯图亚特王朝的转换之间。贝特潇洒几笔,就勾勒出这种新旧转捩间的机会与活力:莎士比亚与伽利略都出生于1564年,这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巅峰米开朗琪罗和日内瓦新教改革领袖约翰·加尔文去世的年份”,而这新与旧的撞击给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无穷的活力。从《李尔王》中的爱德蒙,到《理查三世》中的理查、《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的艾伦、《约翰王》中的私生子、《奥赛罗》中的伊阿戈——这些代表“新哲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让自幼在文法学校受到古典教育的莎士比亚既厌恶、又深受吸引,而这,或许恰恰因为莎士比亚是一个“旧世界中的新人”。
贝特邀请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的具体地理与空间,想象莎士比亚生活的真实际遇。全书以《皆大欢喜》中杰奎斯“人生如舞台”的著名独白为纲目,划分了莎士比亚生活的七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剧院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人生如舞台,激活这一譬喻的,恰恰是剧团在大部分时间内主导了莎士比亚的人生和主要社会关系这一事实,而剧院的空间政治又浓缩了具体时空中的瘟疫、竞争、宫廷扶持和政治监督等诸多力量。当他创作刚刚起步,剧院就因为瘟疫和约翰·纳什的《狗岛》可能引发的骚乱被迫关闭;生涯的晚期,詹姆斯一世统治伊始的瘟疫又关停了剧院。但这两次漫长的停演都促成了莎士比亚身份的重要转变;同时,后一次剧院的关停也间接导致莎士比亚从喜剧转向晚期复杂的大型悲剧与传奇剧的写作。他的剧团与剧院离不开宫廷:女王对戏剧的爱好促成了他的崛起,成名后剧团也常在宫廷演出,不过世俗剧院作为与教堂分庭抗礼的公共空间,它的煽动性也带来种种政治风险与限制。但莎士比亚创作的生命力并不主要来自宫廷:它是闹市而非王室或者书斋的产物。他的剧目要与童伶剧团竞争,他的台词里不仅有罗马古谚,还有酒馆里的街头智慧。他的灵感不仅来自奥维德与塞内加,还来自同时代最新鲜思潮的刺激——马洛的新剧、弗洛里奥翻译的蒙田、马基雅维利哲学、同时代的著名讼案(如《哈姆雷特》背后黑尔斯诉佩蒂关于自杀者地权的争论)。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剧作既呈现莎士比亚作为艺术家超凡的纵横能力,又映照出整个时代的灵魂,甚至说可以是一种最广义的集体创作的产物。
稽古和钩沉历史现场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莎士比亚:时代灵魂》又带着鲜明的当代问题意识,或用贝特的话说,它乐于“用历史(的谬误)照亮现在”。对于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些争议性事实,比如只把“第二好的床留给妻子”,比如十四行诗中黑美人和青年的身份乃至性向问题,这本书都有涉及,不过在表层事实层面的讨论之外,贝特更把这些问题当作一些更普遍也更当代的命题的引子,引出莎士比亚与法律、与权威之间关系的问题。它更关注的,是为什么莎士比亚没有被牵连进埃塞克斯叛乱的政治风波,哪怕伯爵的亲信手下刚刚在环球剧院观看了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而三年前同样书写了理查二世的政治史学家海沃德就被投进了伦敦塔?作为“政治信仰的变色龙”,莎士比亚究竟抱有如何扑朔迷离的史观,跟造神的都铎建国神话之间是否保持距离?《奥赛罗》旨在给詹姆斯一世什么样的现实政治提醒,而这种提醒又如何是后西班牙舰队时代的思想产物?好像总有一种思想——乃至灵魂的求知欲——带着这本书前行,而这对于有着类似好奇心的读者来说,是再过瘾不过的。
也许正是因为真正意义上传记性事实的相对稀少,《莎士比亚:时代灵魂》采用了一种更自由的、以思想史议题为纲目的写作形式。它并不严格按照从襁褓到坟墓的顺序,而是以问题统摄对具体剧目的讨论,如“学童”一章反而关注晚期剧作《暴风雨》,借此考察了莎士比亚的拉丁文水平、藏书数量,乃至斯多葛主义与新式人文主义和伊壁鸠鲁派思想的角力等问题。这一母题在贝特的近作《古代经典如何塑造了莎士比亚》(2019)中得到了更深入的阐发,而这种以问题带文本的进路不仅构成传记写作的一种形式创新,更让人想起一些类似形式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近作,如纵览莎士比亚剧目、每部聚焦一个核心问题的《这就是莎士比亚》(艾玛·史密斯著)。而“老叟”一章借《李尔王》对私生子与自然法权的讨论,与阿格尼斯·赫勒《脱节的时代》(吴亚蓉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出版)颇可对读。此外,虽然行文松弛、风格灵活、叙事一流,但贝特的文献研究与论证功夫却一点都不含糊。一个简单的例子:《冬天的故事》一节,不到三千字,有清晰的研究问题(莎士比亚对传奇故事的改编中对西西里亚和波西米亚两个国家的颠倒),结合翔实的文献、文本分析与地缘政治、宗教冲突史实,是学生与研究者足可模仿的、举重若轻的论述体写作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