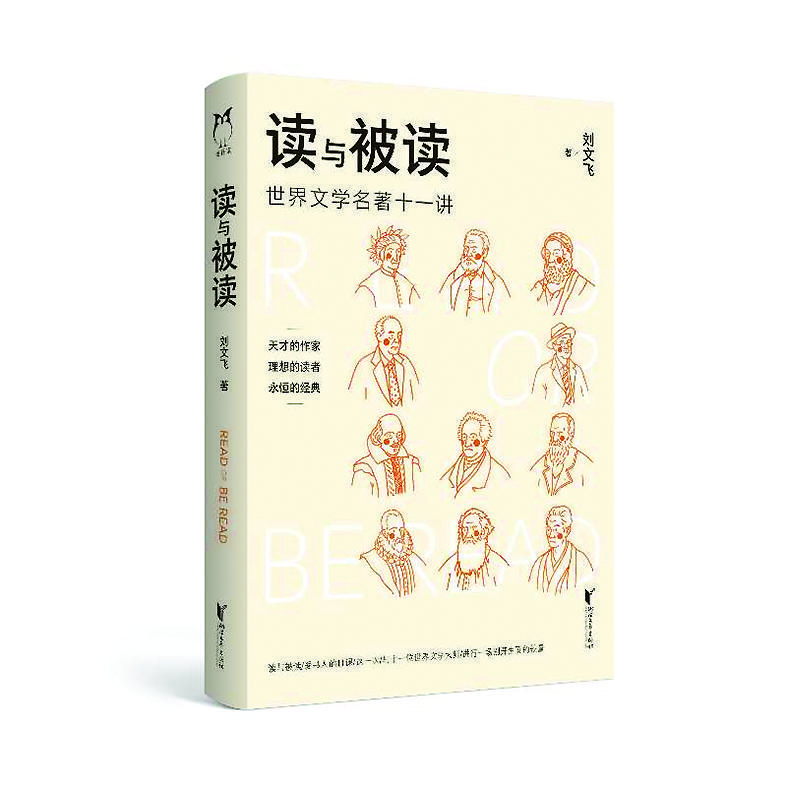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4-09 第27,925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打破牢笼,汲取新知
《读与被读:世界文学名著十一讲》 刘文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从彦在刘文飞看来,“读与被读”是一件与生俱来的事情,是一桩相伴终生的事业。他的新著《读与被读》打破语言牢笼,在汲取与表达中寻找完美的平衡,在对话与交流中觅得生活的美好,在限制与突破中实现心灵的富有。
众所周知,作者完成一部书并不意味着创作过程的结束,而只有当该作品被读者阅读之后,其方才完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如此一来,“读与被读”也可以被视作一次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的旅行。《读与被读》一书就以《荷马史诗》为起点,以《洛丽塔》为终点,全程访问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乔伊斯、川端康成、纳博科夫等11位世界文学大师,期间或钻研人物形象,或探讨文学属性,或谈论思想、生存等严肃话题,或从建筑、颜色等细节解构经典,最终奉上一场世界经典文学的思想盛宴。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位莎士比亚的读者都可以成为部分的莎士比亚,同时又可以超越莎士比亚。刘文飞是一位颇具洞察力的阅读者,他依靠对文本一遍遍的细读,发现了许多细节之趣。例如安娜发现了卡列宁的大耳朵,托尔斯泰发现了安娜的发现,纳博科夫又发现了托尔斯泰的发现。于是,读者跟着刘文飞发现并记住了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这个著名的细节。这种套娃式的阅读发现,不仅是字里行间的魅力,也是精读文字的奖赏。而这样的字斟句酌似乎也在提醒普通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双眼,也可以手持放大镜,甚至还可以架起高倍显微镜。
除了精读,刘文飞也指明了又一条阅读的明路:写作者的高度,是由他的阅读量来决定的;同理可得,阅读者的深度,也是需要依靠他的阅读量来支撑。譬如在《尤利西斯》面世前后,欧美文学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许多意识流文学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对于主人公“地下室人”的潜意识的传导,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于安娜卧轨之前心理活动的描写,又如别雷的《彼得堡》、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作者与读者的交替努力,共同汇成一道波澜壮阔的意识流文学潮流。再如为了读懂《雪国》的死亡主题,读者需要了解川端康成其他小说《禽兽》《千只鹤》《名人》《睡美人》《山音》等作品中描述的死亡,需要了解川端康成在未成年时先后送别了父亲、母亲、奶奶、姐姐、爷爷以及他的几位老师、远亲和朋友这样的个人经历,需要了解川端康成的自杀,需要了解日本文化和文学中的“物哀”传统,甚至要了解女主人公驹子的名字与中国古代的蚕马神话之间的联系。
作为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也时刻警醒自己——要提防那只读一本书的人。于是,他开始以俄罗斯文学名著为支点,去撬动世界文学名著的杠杆。譬如文学中所谓“双重人”的说法,最早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于1846年的中篇小说《双重人》;而在《哈姆雷特》这出戏中,哈姆雷特这个形象身上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性格的双重性。再如,荷马在他的两部史诗中对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所持的情感立场,构成了悲悯传统的源头,同时这种“悲悯”深远地影响着俄罗斯文学,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中主人公格里尼奥夫是一名忠于沙皇的官军军官,可他却因帮助过起义军首领普加乔夫而得到后者的宽恕;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绘俄国军民战胜拿破仑的辉煌胜利,可他却要借助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形象来表达他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博爱思想;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对军官格里高利及其命运的同情也构成了这部史诗巨著的情感基础。
读是一种吸收,被读是一种释放。可是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释放,因为读什么、如何读,已然构成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减缓甚至消弭生活的重担,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吸收,因为对用心的作者而言,他们十分在意读者的阅读感受,他们乐意倾听读者的阅读意见,他们迫切希望让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再上一层楼。聪明的他们深知他们吸收的是弥足珍贵的阅读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