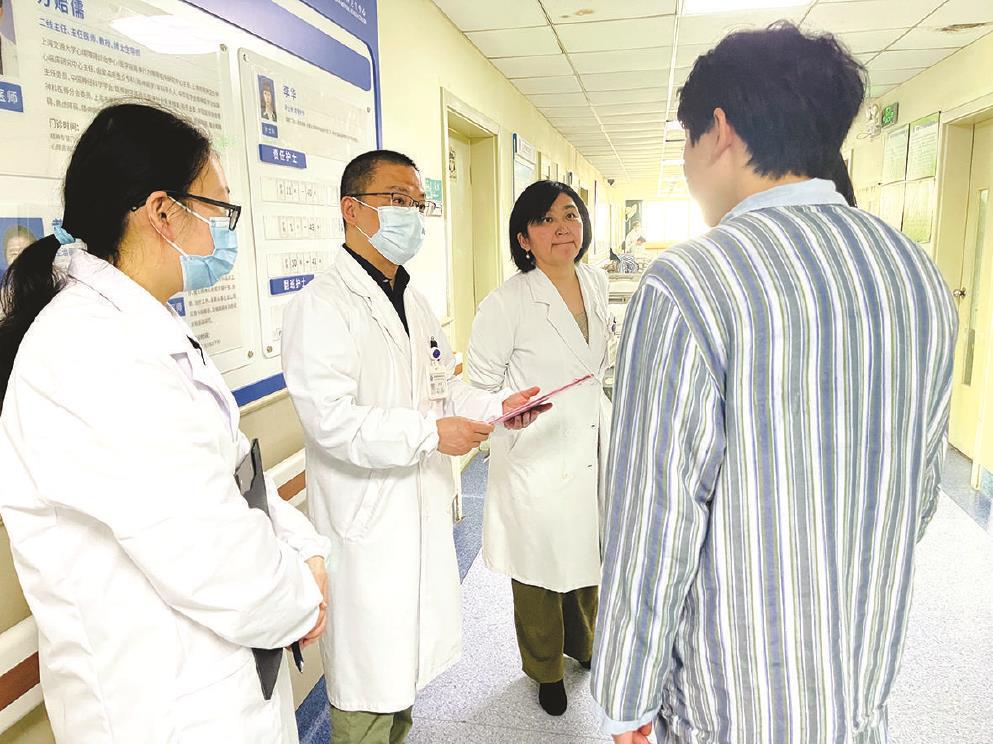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03-30 第27,915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今天是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彭代辉为他的特别来访者坚守这个冷门学科30多年——
给“困在情绪里的人”找一个出口
彭代辉(左二)与他的来访者交流。 (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记者 唐闻佳“如今,人人都流行说‘我emo(抑郁)了’。而且有不少人认为,抑郁症就是郁闷、不愉快。但是,抑郁、不开心,都是可以自我调节的,而患抑郁症的人无法自我调节,因为他病了,一定要看医生。”彭代辉常常需要跟人解释,到底什么是抑郁症,他到底在做什么。
彭代辉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科主任。在他这里,主要涉及两种病,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归结起来,也可指向一个都市流行词——情绪。在彭代辉这里,患者不叫患者,而叫“来访者”,是“困在情绪里的人”。
每年3月30日是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也是画家梵高的生日。医学界推断梵高正是这一精神疾病的患者。事实上,这一疾病日既是为纪念这名天才画家,也是希望由此提升公众认知。今年双相障碍日之际,记者走近彭代辉与他的来访者们。
疯子与天才间,他们在“燃烧”自己
因梵高、贝多芬、海明威、歌德等诸多名人被推测患有该病,双相情感障碍又称“天才病”,这多少给这一疾病蒙上几分浪漫色彩。
“这是美好的误解。”彭代辉告诉记者,之所以会有“天才病”一说,是因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典型表现就是时而躁狂、时而抑郁,处在“极端情绪的两头”,确实能具备一般状态下不具备的创造力。
“精神活动会非常亢奋,思维很敏锐,天马行空。”彭代辉的来访者里有一个擅长绘画的女孩,在抑郁阶段是“暗黑系”画风,躁狂阶段画风则无比明媚。还有一个音乐人,抑郁时就是朋克金属的创作风格……他们说,有时真希望保持“轻躁狂”状态,因为可以带来灵感。
“但其实这是病理状态,可能往中重度状态发展。而且届时可能出现幻觉,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而后会言行失控,可能有伤人、毁物的风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彭代辉感慨,这类患者其实在“燃烧”自己,发作的暴风骤雨过后迎来的是“耗竭”。
彭代辉说,不同于传统身体上的疾病,这些患者可能因病情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如果接受及时、规范的治疗,他们完全有机会回归社会、回归日常,而不再是“患者”。
精神科大夫要有情怀,共情是基本职业技能
有别于传统疾病的门诊,彭代辉的门诊上,一个初诊病人往往至少需要看半小时。而今,门诊量也在增加。
“并非发病率提高了,精神类疾病的发病率是相对稳定的。只是人们可能更关注自己的情绪状态了。”也因此,彭代辉总和学生说,精神科大夫一定要有情怀,“精神科有一个基本的职业技能叫共情,不是说病人哭,你也哭。而是他在非常压抑时,你要理解他为什么压抑。精神病人的社会地位很边缘化,没有情怀的话,很难建立真正的医患同盟。”
当然,作为一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也得明白“边界感”,不让自己卷进情绪困局。用当下流行词说,这个职业“很内耗”。
30多年前,这个职业选择更为冷门。彭代辉的父亲是医务工作者,1989年高考时,他听从父亲建议,考取了湖北医科大学(今武汉大学医学部)临床医疗系精神卫生专业,毕业后留校分配到附属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精神卫生中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精神科是冷门学科,学科发展也慢,精神病人常被认为是“神经病”,很多医生也不愿当精神科医生。但在这里,彭代辉看到了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它也可以救人性命!
“遗传学研究是我选的方向,同样被诊断为抑郁症,有的人治愈,有的人不能,这可以部分通过遗传学解答,不同的遗传特征,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后来,我们又投入探索脑部变化的研究。带着研究的思路看诊,我要帮到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彭代辉感慨,初入医门也有疑惑,这个学科成就感很有限,但越学越发现,相比其他学科,因为大脑的复杂,这里有更多需要研究之处。
很多问题无能为力,但爱可以创造“不一样”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是国内最早将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从传统精神科中单独划分出来的医疗机构,20多年前,这里成立心境障碍科,从最开始的10张床,发展至今两个楼面、108张床。为带动学科整体发展,彭代辉发起“上海心境障碍科学术沙龙”,全上海的精神科医生常常利用业余时间聚在一起,把疑难病例拿出来讨论,至今已坚持7年。
“这个学科掺杂太多的人文和社会因素。做一个精神科医生,必须要懂社会学,有人文情怀。”彭代辉感慨,在他的来访者里,大部分治疗其实很艰难,但总有成功者。
最近,一个男孩专程回国来到上海找彭代辉。男孩的父母都是教师,他在初中时,开始厌学,不愿去学校。初二时,一家人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找彭代辉。“他是少数能坚持的孩子——他坚持去上学。读到高中,抑郁发作了,他开始吃药。高二时他出国游学,出现躁狂状态,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他依然坚持治疗、坚持学业。吃药有瞌睡、发胖等不良反应,父母陪他一起面对、接纳这种状态。家属的支持太重要了。”令彭代辉更为感怀的是,这个男孩后来在美国读本科、在英国读硕士期间,依然保持在这名上海医生这里随访,并在最近一次回国时特地来上海告诉他:“谢谢你救了我,我想学心理学”。
彭代辉说,很多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但爱可以创造“不一样”。
如今,不仅这名曾经的来访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00后选择成为彭代辉的同行。“可能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人的自我觉察更感兴趣,而且国家对精神医学的重视与投入也有目共睹。”彭代辉说,“在这个巨变的世界,人们感到压力日益多元,我们在医学上称此为‘应激’。面对不同的困难、挑战,有些应激,也是一种保护。试想,如果不担心自己的成绩,可能就不会去努力学习。问题是,如何更好地自我实现、自我接纳,而不是困在情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