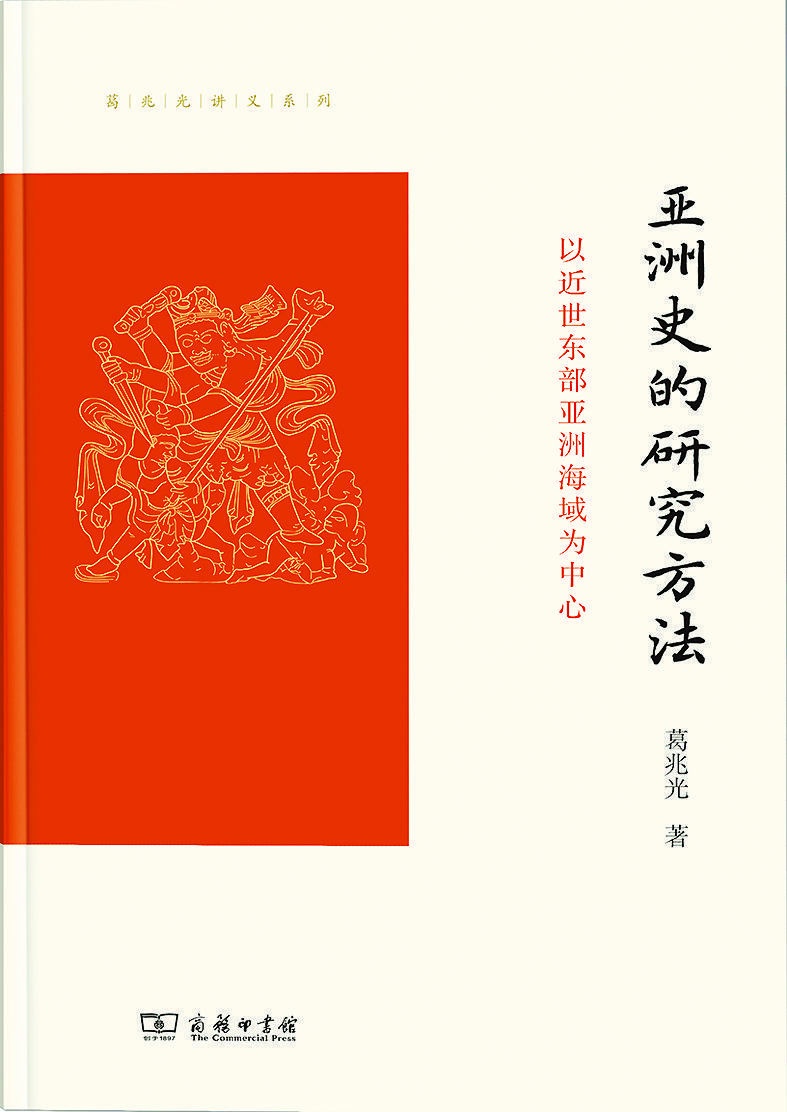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3-12-09 第27,803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看中国历史,不能缺一双“海洋眼”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葛兆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蔡怀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朝宰相魏徵此言,人人皆知,真正的理解者却少。回望历史中的无数次蹉跌,常有“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黑格尔)之叹。
一方面,读史方法有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史没读到。故“读史却不知兴替”。
以中国史而言,海洋史便极少被关注,人们对它的了解,远不如陆地史,可近代困境恰恰源自海洋。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明清屡屡禁海,为何水师建设总是滞后……当葡萄牙人开创线式队列、炮击为主、轮流发炮的新战术时,东方海军依然保持传统的“跳仓”战法,火炮无法精确瞄准,仅有震慑作用;而明末郑芝龙使用的火船突击、同归于尽的战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仍被当成奇招……
历史不断惩罚忽略它的人,这也提醒着当代读者:海洋史不可不读。
一波才息一波生
不读海洋史,因其难读。一是史料少,二是多中心,三是常变化。不像陆地史,给人以清晰的从上到下(或从中心到边缘)的秩序感、从古到今的线性感,只是这秩序感、线性感多由人造,易成认知枷锁。
该怎么读海洋史?葛兆光先生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为我们提供了门径。这本书是课堂讲义,深入浅出,重在方法。
从陆地史看“忽必烈东征日本”,只是“小事件”,意在消化南宋降兵,败于风暴等“偶然因素”,影响有限。可从海洋史看,元朝是“人类史上首次全球化”,它将不同文明纳入统一时间,即:“如今日头出的地方,日头落的地方,都是咱每(们)的。”这是一次格式化,中原传统儒家社会结构(士农工商)亦遭瓦解。“东征日本”是世界史扩张的必然一步,它的失败激发了日本、高丽的民族意识,使“后蒙古时代”从“合”又转向“分”。
再如“万历援朝战争”,从陆地史看,明朝、日本、朝鲜三方博弈,明朝消耗国力,亡国亦与此相关。但从海洋史看,葡萄牙人、暹罗人等都曾试图卷入,目的是修改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秩序”,日本挑战失败,转向锁国200多年,而保留旧秩序的代价是,在大航海时代一错再错。
其实,海洋史的材料并不少,本书介绍了朝鲜使节的《燕行录》、越南使节的《朝天录》、日本的《华夷变态》等,皆为巨制,另有碑刻、个人文集等,堪称浩瀚,许多细节让人耳目一新。以道光皇帝为例,正史较少提到他的相貌,官方绘图亦无大异,但越南史料称他“春秋四十五,而齿已尽落”,朝鲜史料也说他“齿尽脱”。可知所谓史料少,实为阅读少,而无知必有代价。
站在海洋史的角度,才能真正体会到“一波才息一波生”,历史盘根错节、此消彼长、互为因果,没有永远的中心,只有永远的流动性,勇于求变,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本书寄托深重,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之况味。
不受帝国保护的商人
“于是国王(亲自)前往中国,他杀死了抵抗者,将那里洗劫一空。”在塔巴里《历史》中,记录了也门国王“征服”中国的故事……
各国早期史中,不乏“先前阔”传说,正是这些传说,激励商人们不避艰险去开拓。早在公元713年,阿拉伯贸易使节已前往唐朝,8至10世纪,阿拉伯海商主导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之路常有战争不同,海上丝绸之路持续和平,印度洋上的商船很少携带武器。
在《东来西往:8-13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中,作者陈烨轩呈现了与“大航海时代”迥异的图景——无“仗剑经营”者,亦无“半商半盗”,政府很少参与海商经营。阿拉伯海商聚居在各港口,与当地人合作,东南亚诸国来华“贡使”,多由阿拉伯海商充任。黄巢之乱,广州城10多万阿拉伯海商罹难,只好迁往马来半岛的吉打,后逐渐迁回广州,又遇侬智高叛乱,损失惨重。
11到13世纪,宋朝海商成海上丝绸之路的主体,埃及、印度、东南亚……中国船占大多数,宋朝海商亦持阿拉伯海商的规则,只做“不受帝国保护的商人”,却忽略了阿拉伯海商的另一面——勇于冒险,在相当长时期,少有人能两次到中国,依然前仆后继。
宋朝海商落入阿拉伯海商同样的困境:大环境宽容,生意发达;大环境逼仄,陷入衰退。他们不想惹麻烦,可在传统社会,海商的流动性天然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苏轼便指责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
宋朝中叶始,沿海船民被编入海船户,此后政府的宽容政策屡遭各种原因打断。“置身事外”未能保障崛起的宋朝海商,因一次次错过历史机遇,王朝与海商走向双败。
历史无限复杂,亦有恒数:效率高者恒胜,效率低者恒败。无尽委屈,无数借口,都无法改变大趋势。阿拉伯海商东来,宋朝海商西往,皆在此基本律上行走。本书钩沉出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史的草蛇灰线,给读者别样的启迪。
寻找遗失的印度洋记忆
“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宋代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这样写道。龙涎香是抹香鲸肠道分泌物,只产于印度洋,宋商主导海上丝绸之路时,宋徽宗“青丝贯之,佩于颈”。郑和之后,中国海商退出印度洋,龙涎香渐成传说。
在《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中,作者杨斌钩沉了嘉靖皇帝与龙涎香的故事——嘉靖沉迷道教,急需龙涎香“斋修”,不惜高价购买,却“十多年来一无所获”。1556年,嘉靖甚至发动全国力量采办,勉强凑了2斤多,到1560年,才发现其中多数是假的,仅一两块是真的,还是从葡萄牙人手中买来的。此时葡萄牙人已掌控印度洋航线,只有他们才能找到龙涎香。靠龙涎香,葡萄牙人得以占据澳门。
《明史》指斥嘉靖荒淫,却未深究“受制于人”的原因。
从陆地思维看来,守成胜于进取,所以刘大夏敢于将郑和档案“取而焚之”(此说真伪有争议),终至印度洋“渐渐地和中国越行越远,越来越模糊,乃至隐而不见”。
本书意在找回遗失的“印度洋记忆”,从宋代沉船“泉州一号”,到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乃至南宋沉船“南海一号”,皆证明中国和印度洋曾有的紧密联系。
此外,贝币在中国流通上千年,明代南京有专门的贝币库房,而流通用贝币只产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西游记》中的人参果,宋代制造的无钉海船,乃至明人对马尔代夫“海港爱情”的曲折描绘……它们在杨斌的笔下,皆成通往过去的线索。
本书由21篇专栏文章组成,胜在多姿多彩,从不同侧面呈现历史的丰富性——中华文明亦向海而生,找回海洋中国的记忆,才能完整呈现它的风采。
海洋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宋代理学家程颐曾向老师发问:“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大地安在甚处。”
程颐之问的背后,是巨大的恐慌:我们所知的一切,来源皆可疑,却很少被追问。换言之,处于怎样的氛围,就会有怎样的定见,欲破定见,必先破氛围。羽田正的《从历史看海洋:东亚海域交流300年》即破围之作。
本书截取东亚史的三个百年,据海洋史的逻辑,分成三个阶段,每阶段都有它的中心任务,身处其中的中、日、朝三国,种种变化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历史的“规定动作”。
在开拓海疆阶段(1250-1350),不论南宋“向海立国”,还是元朝启动海漕,乃至日本南北朝终结,高丽与元朝的海道往来加强,均为陆地到海洋的跃迁。
在相互争夺阶段(1500-1600),明朝实行海禁体制,日本自建朝贡秩序,“万历援朝战争”将东亚三国卷入其中,而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也加入竞争,东亚海域与“大航海”相接驳。
在分栖共存阶段(1700-1800),清朝“一口通商”,日本“闭关锁国”,朝鲜“闭关自守”,在对抗“大航海秩序”的同时,彼此仍保持着交流与好感,互相救助船难渔民,却在政府层面保持冷漠。
三阶段起伏跌宕,但中日、中朝、日韩航路几无变化,各港均有对方侨民……可见,必有一种共识贯穿其间,基于它形成的认知,犹如大地,托起了历史,却难被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洗礼后的现代人理解。当现代人感慨“假如当初如何,则现在会如何”,当彼此执着于“这是我们的原创”,当“我为何如此不同”被反复提起……历史便偏离了海洋视角,“历史的垃圾时间”反而成主角。
本书的价值在于给读者一双看历史的“海洋眼”,字里行间,透露着深切的关怀:我们真地搞懂“大地安在甚处”了吗?如何不被叙事快感迷惑,体悟历史的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