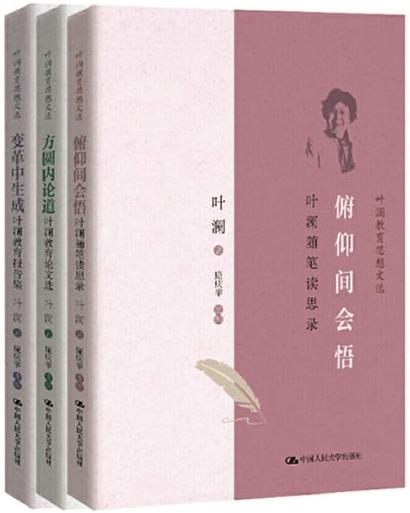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3-01-19 第27,479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叶澜:做有生命气息和实践芳香的教育学
■本报记者 陈瑜
在中国,教育学这门学科长期以来被视为“离根离土”的“舶来品”,带有西方价值观的深刻烙印。但有一个人和她所创建的教育学派改变了这一切,那就是教育学家叶澜。
她建构了中国原创性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它扎根和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与基础教育改革的热土,充满实践的泥土芳香和鲜活的生命气息。它是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归和创造性转化,用“育生命自觉”的传统教育智慧为中国教育奠定新的价值观。它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也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教育学人的自我主张。
叶澜曾说,“在我的教育学研究生涯中,最能打动我的两个字是‘生命’,最让我感到力量的词是‘实践’。”“生命”与“实践”,这两个关键词也贯穿了她教育人生的始末。
学术档案
叶澜,1941年12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本科并留校任教,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首创并主持“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建设30余年。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教育学科组成员和召集人,兼任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多项学术职务,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代表作有《教育概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等。
学人隽语
我从自己的60年人生中,体验着教育对于个人生命的独特价值。知识、技能的习得、运用和发展是人生一辈子不能没有,且是易见、易识和可变的,但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时代所经受的教育,对个人心灵、精神、气质的孕育,却留在生命的深处,在需要的时候,它会唤醒内在的力量,以一生的积累和独特的姿态,去回应所面临的时代,去圆心中的梦。
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有不同的历史印痕,但只要是生命深处的历史印痕,就会永远活在自己今日的生命和行动之中。
——摘自《留在生命深处的历史印痕》(《人民教育》,2009年第18期)
一直记着鲁迅先生评刘半农:虽浅,但浅的澄澈。我愿做清澈的溪,不做混浊的沟,从不故作深沉,也不模棱两可。发表文章,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多么博学,有才华,而是让别人听懂你的声音,由此或能共鸣、补充、生发,或能指出问题、错误,甚至全盘推翻,都有意义。
——摘自《叶澜教育思想文选》自序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选择了教育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这是一个异常复杂艰巨、极具挑战性的事业。我是一个喜欢迎风走路的人,喜欢挑战性的问题和思路。在我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时常横亘着许多疑问、嘲讽甚至人为的阻碍。我一直以这样的比喻激励自己:教育的理想与境界仿佛是一座高山,在攀登者最初登山的时候,遭遇了许多的困惑、嘲讽和质疑,声音嘈杂刺耳,且不去管它,只管往上攀登,在攀登的过程中,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可能会愈加密集,但攀登者只管往上走,集聚其全部的生命能量。愈往上走,那种声音就愈听不到了,等攀登者听不到它的时候,他可能是到了山顶了。
——摘自《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叶澜教授访谈录》(《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
【“新基础教育”研究:一项“上天入地”的事业】
1941年,叶澜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家庭。她的小学便在父亲任教的学校中度过。每天清晨走进校园,一声声扑面而来的“叶老师好”,每逢过年,毕业学生来家中看望父亲的温馨画面,都让她从小就萌生了基础教育的情结,“那时我就觉得当老师很好,长大了我也要当老师。”高中毕业,叶澜以第一志愿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因为在她看来,“要当好老师不懂教育学,就像要当好医生不懂医学一样不可思议。”
1962年,大学毕业后的叶澜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最初的两年需要去教学一线实践,她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并教语文。然而,叶澜很快发现,自己所具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在调皮的小学生们面前毫无用武之地。据她的回忆,这段不长的实践经历让她“‘重创’到几近崩溃”,“因管不好课堂纪律而常常哭鼻子”,“有时教室的喧闹声会把路过的教导主任引进教室,坐镇在教室的后面,才能让我把一节课上下来”。这段亲身体验让她对小学教师的艰辛有了一份理解与尊重,也让她意识到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1974年,叶澜主动请缨去西藏支教,因为参与西藏普及教育的教育调查,她也是“所有援藏教师里走的最多的人。”
1983年,叶澜开设了本科课程“教育概论”。这在当时是一门新设的课程,没有系统的教材,这为她思考并形成自己对于教育学基本问题的见解创造了条件。她以批判性的眼光反思了曾经学过的教育学理论,认为原先的教育学理论中缺少“人”的意识和“人”的研究,从而忽视了个体能动性和个人生命实践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正如她所说,“教育学只研究怎样把外部世界的知识教给学生,而不研究怎样发展学生的内在力量,我认为这是教育学必须补上的更为重要的另一半。”
1991年,叶澜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著作《教育概论》,对教育基本理论体系进行重新阐释。从开篇关于“教育”的概念界定,到最后关于“教育的基本特征”之结语,都是她多年教学过程中批判性思考和综合建构的产物。这些耳目一新的观点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叶澜并不满足于理论研究的“纸上谈兵”。面对当时教育学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漂浮于半空中的状态”,她呼吁加强教育科学的“自我意识”,提出著名的“上天入地”论:理论研究要“上天”,理论只有深刻才有力量;实践研究要“入地”,成果只有在应用中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始于1994年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便是这样一项“上天入地”的事业。对叶澜来说,“新基础教育”研究并不是发明一种方法,用一个模式到实践中去推广,而是从学校和课堂的具体实际出发,像“老中医”那样“一个一个搭脉,只有把老师的脉搏搭清楚,方可开出药方”。二十多年来,这样带着研究者生命温度与“草根情结”的新基础教育,贴地式深度介入全国10余省市200多所学校,将抽象而深刻的教育学理论内化为上千教师、数十万学生鲜活的生存方式。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高强度的忙碌与辛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曾这样记录叶澜当时的工作日常:“连续三天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几乎没有空隙,一直泡在学校和课堂里。上午连听四节课,下午前半段评课研讨,后半段与学校领导团队和中层干部讨论规划,晚上与当地教育局开会总结近期进展。”在李政涛看来,叶澜和她的新基础教育“带来了教育学者生存方式的改变,从思辨性书斋式转变为‘上天入地’式的生存方式,把实践作为教育思想生发的根基。”
扎根于新基础教育,叶澜开创了“以身立学”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以学校转型性变革实践研究为基石,以理论与实践交互构建为特征的教育学派。在其标志性著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中,叶澜这样动情地写道:“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表达‘生命·实践’教育学是怎样一种品性的教育学,我会这样说:‘生命·实践’教育学是属人的、为人的、具有人的生命气息和实践泥土芳香的教育学。”
【“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教育”的中国式表达】
作为中国原创的教育学理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具有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色。这源自于叶澜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反思——那是世纪之交,她承担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百年发展反思回顾的课题研究。在查阅大量资料后她得出结论:中国教育学百年发展存在的基本问题是“两个依赖”:依赖国外教育学,依赖其他学科。“中国教育学已经这样过了一百年,难道还要再如此过一百年吗?”“中国教育学有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地与个性?”她不断自问中国教育学发展的问题。2001年,她发表《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一文,提出要形成中国自己的教育学。“问题是中国的,资源是中国的,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是中国实践与文化滋养的产物。”这些对“中国”的理解,使她坚定要创建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派。
“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这是叶澜对“教育是什么”所作出的中国式表达。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天地之道为大道,言明人间世事所必须遵守之理。“天地”可以理解为自然科学,也可以理解为广阔的宇宙世界;“人事”指社会科学,包括人类文明的所有财富。“育生命自觉”是教育中指向内在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使命。这些都是中国教育传统的精华与智慧。但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知识越来越成为学习的显性目标和可测量的标准,而中国传统教育的育人价值却被淡化,学校往往记住了学科之“教”的任 务,却丢掉了“育”的使命。在叶澜看来,当代中国教育对人的生命关怀,最终须聚焦到个体“生命自觉”之形成,以此来改变中国近代教育将学科教学与人的精神世界、人格培养割裂的基本格局,将分化了的学科化的“天地”与“人事”之教学,再次贯通到“成人”这个教育主题上。
在叶澜看来,儒家教育传统中的智慧之一便是通过日常将高远的目标内化到每人每天的生命实践之中。而“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这一教育理念的实现,也需要“日常教学中春风化雨式的跬步之功”。为此,她提出了“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的教学改革目标。她希望打造这样一个课堂,师生不只是在其中教和学,他们还在感受生命的涌动和成长,学生能够获得多方面的满足和发展,教师的劳动也能够闪现出创造的光辉和人性的魅力。她觉得教师不应该将自己仅仅定位于“知识的传递者”,乃至辛苦的“搬运工”,而应被视为学校生活、教育世界的创造者角色,因为“教师在学生面前呈现的是其全部的人格,而不只是‘专业’”。在她看来,学校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大工厂”,而是师生开展教育活动的“生命场”。从“塑造人”转化为“成就人”,从“大工厂”转化为“生命场”,这是她期望达到的学校变革。
叶澜曾说,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目的,就是要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教育学者的声音。” 2018年,《回归突破》面向世界发行英文版,这标志着中国教育学开始走向世界,而不是只从西方“引进”。“‘新基础教育’学校变革实践颠覆了西方对中国教育的刻板印象,中国地方学校在主动创造方面积累了值得西方学习的独特经验;与这样的学校实践相关的教育思想,同样颠覆了西方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刻板印象。”英文版序言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康纳利教授这样说。
【读文字之书,也读无字的生活与自然之书】
最近这几年,虽然不慎大摔了一跤,但叶澜却说自己“老而弥坚”,“当然不是指骨头坚硬,而是信念、理想更坚定,没有人可以随便把这些推倒,我有自己的定力。”“我做不到孔子的“诲人不倦”,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学而不厌’。知不足而后学,学而不厌,常学常新。”传统文化的相关书籍是叶澜的案头新宠,艺术、国画、音乐,她都广泛涉猎,对她而言读书不为写文章,而是为了将自己再次打开。在她看来,从事教育学研究最大的好处在于,让她感觉自己永远学不够,时时处在一种渴望学习的状态。“教育是这样一项事业,你要作为一个教育者,你一定要使自己变得更美好,然后你努力地使学生通过你的教育变得更美好,这都是我的价值和目标追求,这就是我为什么讲‘生命·实践’的原因。”
叶澜曾经说,“我的人生读的就是两类书:第一类是无字的生活与自然之书,第二类是文字之书。”她为自己的随笔集取名为“俯仰间会晤”,天地人事、有字无字,生命中的任何点滴日常都能够成为叶澜沉思和感悟的对象。她在《梧桐知秋》里为“枝头挂着几片残叶……挺立着,等着寒冬的敲打”的梧桐而感动;在《草花马兰头》里为马兰头的开花而惊喜:“十二片菊花似得浅雪青色的花瓣,围绕着粉绿的花托上淡黄细腻的花蕊,这种和美的色调,犹如大家闺秀”;在《感谢芦花》里赞美芦花的“素雅和独立”,“即使生长在丛中,也不牵扯,更不依附什么而上、而立”……或许也正是这样充满诗意的生活方式,孕育了叶澜“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这样富有生命气息的教育学理论。
为了和自然朝夕相处,叶澜还亲手打造了一个30平米的小花园,并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紫园”——“紫”不仅呼应了园内花开三度的紫藤,也有“此园系我心”之意。她在散文《紫园花事》中写道,与园内的花草树木一切经历“初醒的春、蓬勃的夏、温醇的秋、渐寂的冬”,它们都“用自己无声的生命语言在告诉我,天地与人相通,必须通过这些看起来极普通,乃至被蔑视的,实际上却是集天地之精华的草木来实现”。这片生机勃勃的植物世界让她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顽强,使她的心灵世界得到活力滋养。“天地万物千姿百态、生生不息,我的生命与许多生命相遇,生活越来越乐观。”
这个叶澜悉心守护的“紫园”很像她一辈子教育学生涯的缩影。正如她所说:“教育学是研究造就人生命自觉的教育实践的学问,是一门充满希望、为了希望、创生希望的学问。我愿研究如何让人间每一朵生命之花绽放出自觉独特灿烂的学问而努力终生,并与所有的同行者共享生命成长的尊严与快乐,共享教育学研究特有的丰富与魅力。”
在中国,教育学这门学科长期以来被视为“离根离土”的“舶来品”,带有西方价值观的深刻烙印。但有一个人和她所创建的教育学派改变了这一切,那就是教育学家叶澜。
她建构了中国原创性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它扎根和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与基础教育改革的热土,充满实践的泥土芳香和鲜活的生命气息。它是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归和创造性转化,用“育生命自觉”的传统教育智慧为中国教育奠定新的价值观。它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也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教育学人的自我主张。
叶澜曾说,“在我的教育学研究生涯中,最能打动我的两个字是‘生命’,最让我感到力量的词是‘实践’。”“生命”与“实践”,这两个关键词也贯穿了她教育人生的始末。
学术档案
叶澜,1941年12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本科并留校任教,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首创并主持“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建设30余年。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教育学科组成员和召集人,兼任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多项学术职务,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代表作有《教育概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等。
学人隽语
我从自己的60年人生中,体验着教育对于个人生命的独特价值。知识、技能的习得、运用和发展是人生一辈子不能没有,且是易见、易识和可变的,但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时代所经受的教育,对个人心灵、精神、气质的孕育,却留在生命的深处,在需要的时候,它会唤醒内在的力量,以一生的积累和独特的姿态,去回应所面临的时代,去圆心中的梦。
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有不同的历史印痕,但只要是生命深处的历史印痕,就会永远活在自己今日的生命和行动之中。
——摘自《留在生命深处的历史印痕》(《人民教育》,2009年第18期)
一直记着鲁迅先生评刘半农:虽浅,但浅的澄澈。我愿做清澈的溪,不做混浊的沟,从不故作深沉,也不模棱两可。发表文章,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多么博学,有才华,而是让别人听懂你的声音,由此或能共鸣、补充、生发,或能指出问题、错误,甚至全盘推翻,都有意义。
——摘自《叶澜教育思想文选》自序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选择了教育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这是一个异常复杂艰巨、极具挑战性的事业。我是一个喜欢迎风走路的人,喜欢挑战性的问题和思路。在我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时常横亘着许多疑问、嘲讽甚至人为的阻碍。我一直以这样的比喻激励自己:教育的理想与境界仿佛是一座高山,在攀登者最初登山的时候,遭遇了许多的困惑、嘲讽和质疑,声音嘈杂刺耳,且不去管它,只管往上攀登,在攀登的过程中,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可能会愈加密集,但攀登者只管往上走,集聚其全部的生命能量。愈往上走,那种声音就愈听不到了,等攀登者听不到它的时候,他可能是到了山顶了。
——摘自《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叶澜教授访谈录》(《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
【“新基础教育”研究:一项“上天入地”的事业】
1941年,叶澜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家庭。她的小学便在父亲任教的学校中度过。每天清晨走进校园,一声声扑面而来的“叶老师好”,每逢过年,毕业学生来家中看望父亲的温馨画面,都让她从小就萌生了基础教育的情结,“那时我就觉得当老师很好,长大了我也要当老师。”高中毕业,叶澜以第一志愿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因为在她看来,“要当好老师不懂教育学,就像要当好医生不懂医学一样不可思议。”
1962年,大学毕业后的叶澜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最初的两年需要去教学一线实践,她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并教语文。然而,叶澜很快发现,自己所具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在调皮的小学生们面前毫无用武之地。据她的回忆,这段不长的实践经历让她“‘重创’到几近崩溃”,“因管不好课堂纪律而常常哭鼻子”,“有时教室的喧闹声会把路过的教导主任引进教室,坐镇在教室的后面,才能让我把一节课上下来”。这段亲身体验让她对小学教师的艰辛有了一份理解与尊重,也让她意识到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1974年,叶澜主动请缨去西藏支教,因为参与西藏普及教育的教育调查,她也是“所有援藏教师里走的最多的人。”
1983年,叶澜开设了本科课程“教育概论”。这在当时是一门新设的课程,没有系统的教材,这为她思考并形成自己对于教育学基本问题的见解创造了条件。她以批判性的眼光反思了曾经学过的教育学理论,认为原先的教育学理论中缺少“人”的意识和“人”的研究,从而忽视了个体能动性和个人生命实践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正如她所说,“教育学只研究怎样把外部世界的知识教给学生,而不研究怎样发展学生的内在力量,我认为这是教育学必须补上的更为重要的另一半。”
1991年,叶澜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著作《教育概论》,对教育基本理论体系进行重新阐释。从开篇关于“教育”的概念界定,到最后关于“教育的基本特征”之结语,都是她多年教学过程中批判性思考和综合建构的产物。这些耳目一新的观点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叶澜并不满足于理论研究的“纸上谈兵”。面对当时教育学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漂浮于半空中的状态”,她呼吁加强教育科学的“自我意识”,提出著名的“上天入地”论:理论研究要“上天”,理论只有深刻才有力量;实践研究要“入地”,成果只有在应用中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始于1994年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便是这样一项“上天入地”的事业。对叶澜来说,“新基础教育”研究并不是发明一种方法,用一个模式到实践中去推广,而是从学校和课堂的具体实际出发,像“老中医”那样“一个一个搭脉,只有把老师的脉搏搭清楚,方可开出药方”。二十多年来,这样带着研究者生命温度与“草根情结”的新基础教育,贴地式深度介入全国10余省市200多所学校,将抽象而深刻的教育学理论内化为上千教师、数十万学生鲜活的生存方式。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高强度的忙碌与辛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曾这样记录叶澜当时的工作日常:“连续三天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几乎没有空隙,一直泡在学校和课堂里。上午连听四节课,下午前半段评课研讨,后半段与学校领导团队和中层干部讨论规划,晚上与当地教育局开会总结近期进展。”在李政涛看来,叶澜和她的新基础教育“带来了教育学者生存方式的改变,从思辨性书斋式转变为‘上天入地’式的生存方式,把实践作为教育思想生发的根基。”
扎根于新基础教育,叶澜开创了“以身立学”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以学校转型性变革实践研究为基石,以理论与实践交互构建为特征的教育学派。在其标志性著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中,叶澜这样动情地写道:“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表达‘生命·实践’教育学是怎样一种品性的教育学,我会这样说:‘生命·实践’教育学是属人的、为人的、具有人的生命气息和实践泥土芳香的教育学。”
【“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教育”的中国式表达】
作为中国原创的教育学理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具有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色。这源自于叶澜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反思——那是世纪之交,她承担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百年发展反思回顾的课题研究。在查阅大量资料后她得出结论:中国教育学百年发展存在的基本问题是“两个依赖”:依赖国外教育学,依赖其他学科。“中国教育学已经这样过了一百年,难道还要再如此过一百年吗?”“中国教育学有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地与个性?”她不断自问中国教育学发展的问题。2001年,她发表《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一文,提出要形成中国自己的教育学。“问题是中国的,资源是中国的,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是中国实践与文化滋养的产物。”这些对“中国”的理解,使她坚定要创建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派。
“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这是叶澜对“教育是什么”所作出的中国式表达。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天地之道为大道,言明人间世事所必须遵守之理。“天地”可以理解为自然科学,也可以理解为广阔的宇宙世界;“人事”指社会科学,包括人类文明的所有财富。“育生命自觉”是教育中指向内在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使命。这些都是中国教育传统的精华与智慧。但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知识越来越成为学习的显性目标和可测量的标准,而中国传统教育的育人价值却被淡化,学校往往记住了学科之“教”的任 务,却丢掉了“育”的使命。在叶澜看来,当代中国教育对人的生命关怀,最终须聚焦到个体“生命自觉”之形成,以此来改变中国近代教育将学科教学与人的精神世界、人格培养割裂的基本格局,将分化了的学科化的“天地”与“人事”之教学,再次贯通到“成人”这个教育主题上。
在叶澜看来,儒家教育传统中的智慧之一便是通过日常将高远的目标内化到每人每天的生命实践之中。而“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这一教育理念的实现,也需要“日常教学中春风化雨式的跬步之功”。为此,她提出了“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的教学改革目标。她希望打造这样一个课堂,师生不只是在其中教和学,他们还在感受生命的涌动和成长,学生能够获得多方面的满足和发展,教师的劳动也能够闪现出创造的光辉和人性的魅力。她觉得教师不应该将自己仅仅定位于“知识的传递者”,乃至辛苦的“搬运工”,而应被视为学校生活、教育世界的创造者角色,因为“教师在学生面前呈现的是其全部的人格,而不只是‘专业’”。在她看来,学校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大工厂”,而是师生开展教育活动的“生命场”。从“塑造人”转化为“成就人”,从“大工厂”转化为“生命场”,这是她期望达到的学校变革。
叶澜曾说,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目的,就是要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教育学者的声音。” 2018年,《回归突破》面向世界发行英文版,这标志着中国教育学开始走向世界,而不是只从西方“引进”。“‘新基础教育’学校变革实践颠覆了西方对中国教育的刻板印象,中国地方学校在主动创造方面积累了值得西方学习的独特经验;与这样的学校实践相关的教育思想,同样颠覆了西方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刻板印象。”英文版序言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康纳利教授这样说。
【读文字之书,也读无字的生活与自然之书】
最近这几年,虽然不慎大摔了一跤,但叶澜却说自己“老而弥坚”,“当然不是指骨头坚硬,而是信念、理想更坚定,没有人可以随便把这些推倒,我有自己的定力。”“我做不到孔子的“诲人不倦”,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学而不厌’。知不足而后学,学而不厌,常学常新。”传统文化的相关书籍是叶澜的案头新宠,艺术、国画、音乐,她都广泛涉猎,对她而言读书不为写文章,而是为了将自己再次打开。在她看来,从事教育学研究最大的好处在于,让她感觉自己永远学不够,时时处在一种渴望学习的状态。“教育是这样一项事业,你要作为一个教育者,你一定要使自己变得更美好,然后你努力地使学生通过你的教育变得更美好,这都是我的价值和目标追求,这就是我为什么讲‘生命·实践’的原因。”
叶澜曾经说,“我的人生读的就是两类书:第一类是无字的生活与自然之书,第二类是文字之书。”她为自己的随笔集取名为“俯仰间会晤”,天地人事、有字无字,生命中的任何点滴日常都能够成为叶澜沉思和感悟的对象。她在《梧桐知秋》里为“枝头挂着几片残叶……挺立着,等着寒冬的敲打”的梧桐而感动;在《草花马兰头》里为马兰头的开花而惊喜:“十二片菊花似得浅雪青色的花瓣,围绕着粉绿的花托上淡黄细腻的花蕊,这种和美的色调,犹如大家闺秀”;在《感谢芦花》里赞美芦花的“素雅和独立”,“即使生长在丛中,也不牵扯,更不依附什么而上、而立”……或许也正是这样充满诗意的生活方式,孕育了叶澜“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这样富有生命气息的教育学理论。
为了和自然朝夕相处,叶澜还亲手打造了一个30平米的小花园,并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紫园”——“紫”不仅呼应了园内花开三度的紫藤,也有“此园系我心”之意。她在散文《紫园花事》中写道,与园内的花草树木一切经历“初醒的春、蓬勃的夏、温醇的秋、渐寂的冬”,它们都“用自己无声的生命语言在告诉我,天地与人相通,必须通过这些看起来极普通,乃至被蔑视的,实际上却是集天地之精华的草木来实现”。这片生机勃勃的植物世界让她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顽强,使她的心灵世界得到活力滋养。“天地万物千姿百态、生生不息,我的生命与许多生命相遇,生活越来越乐观。”
这个叶澜悉心守护的“紫园”很像她一辈子教育学生涯的缩影。正如她所说:“教育学是研究造就人生命自觉的教育实践的学问,是一门充满希望、为了希望、创生希望的学问。我愿研究如何让人间每一朵生命之花绽放出自觉独特灿烂的学问而努力终生,并与所有的同行者共享生命成长的尊严与快乐,共享教育学研究特有的丰富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