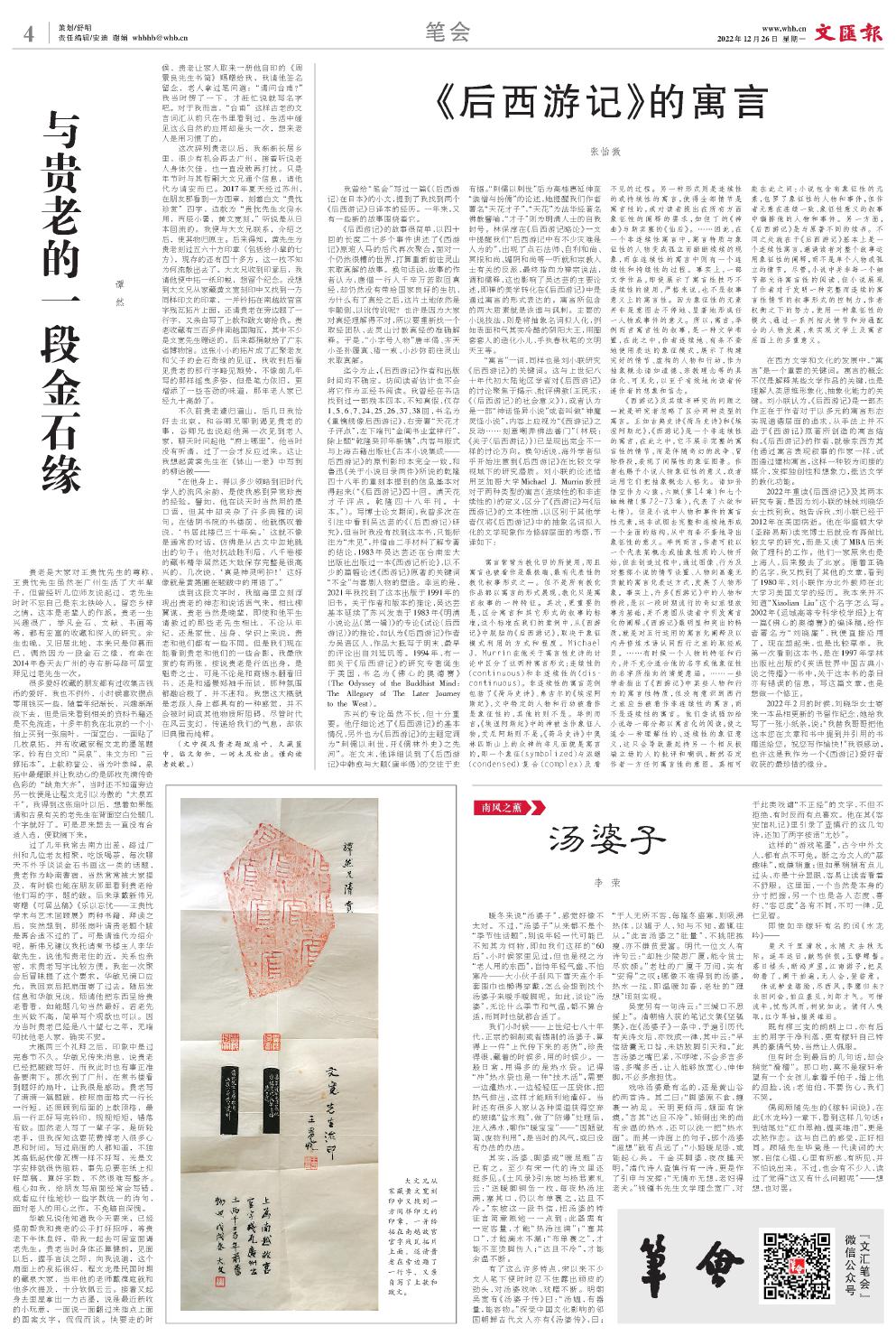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2-12-26 第27,455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与贵老的一段金石缘
大文兄从家藏黄文宽刻印中又找到一方同样印文的印章,一并钤拓在南越故宫官字残瓦拓片上面,还请贵老在旁边题了一行字,又亲自写了上款和跋文。
谭然贵老是大家对王贵忱先生的尊称,王贵忱先生虽然在广州生活了大半辈子,但曾经听几位师友说起过,老先生时时不忘自己是东北铁岭人,留恋乡梓之情,这本是老辈人的作派。贵老一生兴趣很广,举凡金石、文献、书画等等,都有宏富的收藏和深入的研究。余生也晚,又旧居北地,本来只是仰慕而已,偶然因为一段金石之缘,有幸在2014年春天去广州的寺右新马路可居室拜见过老先生一次。
很多爱好收藏的朋友都有过收集古钱币的爱好,我也不例外,小时候喜欢攒点零用钱买一些,随着年纪渐长,兴趣渐渐淡下去,但是后来看到相关的资料书籍还是不免流连。十多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小拍上买到一张扇叶,一面空白,一面贴了几枚泉拓,并有收藏家程文龙的墨笔题字,钤有白文印“吴泉”、朱文方印“云錞拓本”。上款称誉公,当为叶恭绰。泉拓中最耀眼并让我动心的是那枚充满传奇色彩的“缺角大齐”,当时还不知道旁边另一枚便是让程文龙引以为傲的“大泉五千”。我得到这张扇叶以后,想着如果能请和古泉有关的老先生在背面空白处题几个字就好了。可是思来想去一直没有合适人选,便耽搁下来。
过了几年我常去南方出差,路过广州和几位老友相聚,吃饭喝茶,每次聊天不外乎谈谈金石书画这一类的话题,贵老作为岭南耆宿,当然常常被大家提及,有时候也能在朋友那里看到贵老给他们写的字,题的跋。后来承戴新伟兄寄赠《可居丛稿》《乐以忘忧——王贵忱学术与艺术回顾展》两种书籍,拜读之后,突然想到,那张扇叶请贵老题个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可是请谁代为绍介呢,新伟兄建议我托请煮书楼主人李华敏先生,说他和贵老住的近,关系也亲密,求贵老写字比较方便。我在一次聚会后冒昧提了这个要求,华敏兄满口应允,我回京后把扇面寄了过去。随后发信息和华敏兄说,烦请他把东西呈给贵老看看,如能题几句当然最好,若老先生兴致不高,简单写个观款也可以。因为当时贵老已经是八十望七之年,无端叨扰他老人家,确实不安。
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印象中是过完春节不久。华敏兄传来消息,说贵老已经把题跋写好,而我此时也有事正准备要南下。那次到了广州,在煮书楼看到题好的扇叶,让我很是感动。贵老写了满满一篇题跋,按照扇面格式一行长一行短,还照顾到后面的上款顶格,最后一行正好写完钤印,规规矩矩,错落有致。固然老人写了一辈子字,是斫轮老手,但我深知这要花费掉老人很多心思和时间。写过扇面的人都知道,不独其高低起伏像瓦楞一样不好写,光是文字安排就很伤脑筋,事先总要在纸上拟好草稿,算好字数,不然很难写整齐。粗心如我,给朋友写扇面经常会写错,或者应付性地钞一些字数统一的诗句,面对老人的用心之作,不免暗自深愧。
华敏兄说他知道我今天要来,已经提前帮我和贵老的公子打好招呼,等贵老下午休息好,带我一起去可居室面谒老先生。贵老当时身体还算健朗,见面以后,握手言谈之际,向我说道,这个扇面上的泉拓很好,程文龙是民国时期的藏泉大家,当年他的老师戴葆庭就和他多次提及,十分钦佩云云。接着又起身去里屋拿出一方古墨,说是最近新收的小玩意,一面说一面翻过来指点上面的图案文字,侃侃而谈。快要走的时候,贵老让家人取来一册他自印的《周景良先生书简》赐赠给我,我请他签名留念,老人拿过笔问道:“请问台甫?”我当时愣了一下,才赶忙说就写名字吧。对于我而言,“台甫”这样古老的文言词汇从前只在书里看到过,生活中碰见这么自然的应用却是头一次,想来老人是用习惯了的。
这次辞别贵老以后,我渐渐长居乡里,很少有机会再去广州,接着听说老人身体欠佳,也一直没敢再打扰。只是年节时与其哲嗣大文兄通个信息,请他代为请安而已。2017年夏天经过苏州,在朋友那看到一方图章,刻着白文“贵忱珍赏”四字,边款为“贵忱先生文房永用,丙辰小暑,黄文宽刻。”听说是从日本回流的。我便与大文兄联系,介绍之后,使其物归原主。后来得知,黄先生为贵老刻过五六十方印章(包括给小辈的七方),现存的还有四十多方,这一枚不知为何流散出去了。大文兄收到印章后,我请他便中拓一纸印蜕,想留个纪念。没想到大文兄从家藏黄文宽刻印中又找到一方同样印文的印章,一并钤拓在南越故宫官字残瓦拓片上面,还请贵老在旁边题了一行字,又亲自写了上款和跋文寄给我。贵老收藏有三百多件南越国陶瓦,其中不少是文宽先生赠送的,后来都捐献给了广东省博物馆。这张小小的拓片成了汇聚老友和父子的金石奇缘的见证,我收到后看见贵老的那行字略见颓势,不像前几年写的那样摇曳多姿,但是笔力依旧,更增添了一些苍劲的味道,那年老人家已经九十高龄了。
不久前贵老遽归道山,后几日我恰好去北京,和谷卿兄聊到谒见贵老的事,谷卿兄也说起他第一次见到老人家,聊天时问起他“府上哪里”,他当时没有听清,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这让我想起黄裳先生在《钵山一老》中写到的柳诒徵——
“在他身上,得以多少领略到旧时代学人的流风余韵,是使我感到异常珍贵的经验。譬如,他在谈天时当然用的是口语,但其中却夹杂了许多典雅的词句。在惜阴书院的书楼前,他就慨叹着说,‘书居此楼已三十年矣。’这就不像是通常的对话,仿佛是从古文中忽地跳出的句子;他对抗战胜利后,八千卷楼的藏书精华居然还大致保存完整是很高兴的,几次说,‘真是神灵呵护!’这好像就是黄荛圃在题跋中的用语了。”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贵老的神态和说话语气来,相比柳翼谋,贵老当然是晚辈,即使和他平生请教过的那些老先生相比,不论从年纪,还是家世、出身、学识上来说,贵老和他们都有一些不同。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贵老和他们的一些合影,我最欣赏的有两张,按说贵老是行伍出身,是魁奇之士,可是不论是和商锡永翻看旧书,还是和潘景郑袖手而谈,那种氛围都融洽极了,并不违和。我想这大概就是老派人身上都具有的一种感觉,并不会被时间或其他物质所阻碍,尽管时代在风云变幻,传递给我们的气息,却依旧典雅而纯粹。
(文中提及贵老题跋扇叶,久藏箧中,临文匆忙,一时未及检出。谨向读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