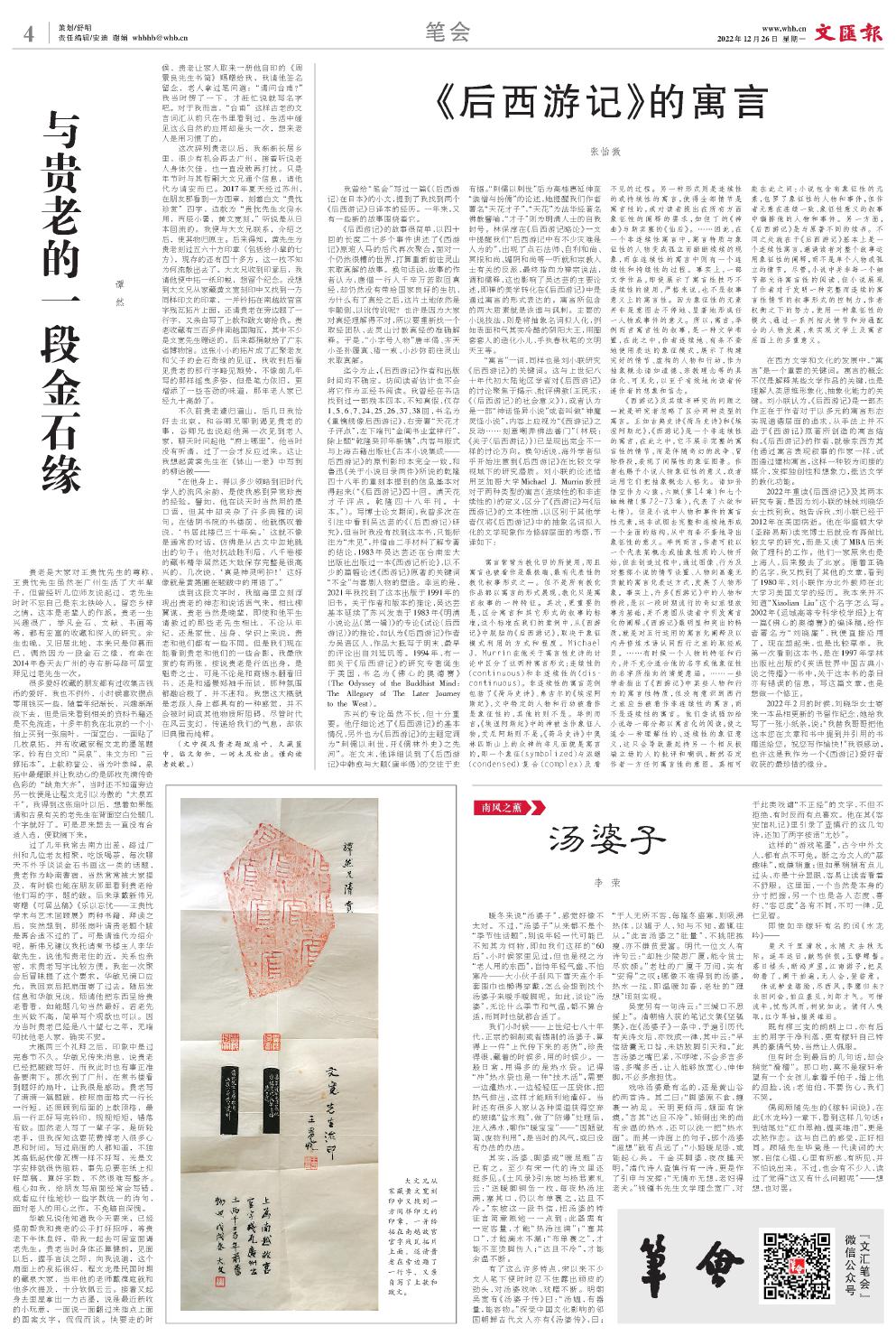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2-12-26 第27,455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后西游记》的寓言
张怡微
我曾给“笔会”写过一篇《〈后西游记〉在日本》的小文,提到了我找到两个《后西游记》日译本的经历。一年来,又有一些新的故事围绕着它。
《后西游记》的故事很简单,以四十回的长度二十多个事件讲述了《西游记》原班人马的后代再次聚合,面对一个仍然很糟的世界,打算重新前往灵山求取真解的故事。换句话说,故事的作者认为,唐僧一行人千辛万苦取回真经,却仍然没有带给国家良好的生机,为什么有了真经之后,这片土地依然是非颠倒、以讹传讹呢?也许是因为大家对真经理解得不对,所以要重新找一个取经团队,去灵山讨教真经的准确解释。于是,“小字号人物”唐半偈、齐天小圣孙履真、猪一戒、小沙弥前往灵山求取真解。
迄今为止,《后西游记》作者和出版时间均不确定。坊间读者估计也不会将它作为正经书阅读。我曾经在书店找到过一部残本四本,不知真假,仅存1、5、6、7、24、25、26、37、38回,书名为《重镌绣像后西游记》,右旁署“天花才子评点”,左下端刊“金阊书业堂梓行”,除上题“乾隆癸卯年新镌”,内容与版式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后西游记》的原刊影印本完全一致,和鲁迅《关于小说目录两件》所说的乾隆四十八年的重刻本提到的信息基本对得起来(“《后西游记》四十回。清天花才子评点。乾隆四十八年刊。十本。”)。写博士论文期间,我曾多次在引注中看到吴达芸的《〈后西游记〉研究》,但当时我没有找到这本书,只能标注为“未见”,并借由二手材料了解专著的结论,1983年吴达芸还在台南宏大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西游记析论》,以不少的篇幅论述《西游记》原著的关键词“不全”与喜剧人物的塑造。幸运的是,2021年我找到了这本出版于1991年的旧书。关于作者和版本的推论,吴达芸基本延续了苏兴发表于1983年《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的专论《试论〈后西游记〉》的推论,如认为《后西游记》作者为吴语区人,作品大抵写于明末、最早的评论出自刘廷玑等。1994年,有一部关于《后西游记》的研究专著诞生于美国,书名为《佛心的奥德赛》(The Odyssey of the Buddhist Mind:The Allegory of The Later Journey to the West)。
苏兴的专论虽然不长,但十分重要。他仔细论述了《后西游记》的基本情况,另外也为《后西游记》的主题定调为“刺儒以刺世,开《儒林外史》之先河”。在文末,他详细谈到了《后西游记》中韩愈与大颠(唐半偈)的交往于史有据。“刺儒以刺世”后为高桂惠延伸至“装僧与扮儒”的论述,她提醒我们作者署名“天花才子”,“天花”为法华经著名佛教譬喻,“才子”则为明清人士的自我封号。林保淳在《后西游记略论》一文中提醒我们“后西游记中有不少灾难是人为的”,出现了点石法师、自利和尚、冥报和尚、媚阴和尚等一听就和宗教人士有关的反派,最终指向为禅宗说法,调和儒释,这也影响了吴达芸的主要论述,即禅的美学转化在《后西游记》中是通过寓言的形式表达的。寓言所包含的两大质素就是诙谐与讽刺。主要的小说技法,则是将抽象名词拟人化,例如表面和气其实冷酷的阴阳大王,用圈套套人的造化小儿,手执春秋笔的文明天王等。
“寓言”一词,同样也是刘小联研究《后西游记》的关键词。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陆地区学者对《后西游记》的讨论聚焦于揭示、批评佛教(王民求:《〈后西游记〉的社会意义》),或者认为是一部“神话怪异小说”或者叫做“神魔灵怪小说”,内容上应视为“《西游记》之反动……刻意嘲弄佛法善门”(林辰:《关于〈后西游记〉》)已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讨论方向。换句话说,海外学者似乎开始注意到《后西游记》在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研究潜质。刘小联的论述借用芝加哥大学Michael J.Murrin教授对于两种类型的寓言(连续性的和非连续性的)的定义,区分了《西游记》与《后西游记》的文本性质,以区别于其他学者仅将《后西游记》中的抽象名词拟人化的文学现象作为修辞层面的考察,节译如下:
寓言常常为教化目的所使用,而且寓言也被看作是最极端、最有代表性的教化叙事形式之一。但不是所有教化作品都以寓言的形式展现,教化只是寓言叙事的一种特征。其次,更重要的是,区分寓言和其它形式的叙事的标准,这个标准在我们的案例中,从《西游记》中脱胎的《后西游记》,取决于象征模式利用的方式和程度。Michael J.Murrin在他关于寓言性史诗的讨论中区分了这两种寓言形式:连续性的(continuous)和非连续性的(dis-cont inuous)。非连续性的寓言范例包括了《荷马史诗》、弗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文中特定的人物和行动被看作是象征性的,其他的则不是。举例而言,《埃涅阿斯纪》中的神被当作象征人物,艾尼阿斯则不是。《荷马史诗》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的非凡面貌是寓言的,即一个象征(symbolized)与浓缩(condensed)复合(complex)及看不见的过程。另一种形式则是连续性的或持续性的寓言,使得全部情节是寓言性的,或对读者提出在所有方面象征性的阐释的要求,如但丁的《神曲》与斯宾塞的《仙后》。……因此,在一个非连续性寓言中,寓言特质与象征性的人物变成孤立而断断续续的现象,而在连续性的寓言中则有一个连续性和持续性的过程。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即使展示了寓言性技巧不连续性的使用,严格来说,也不是叙事意义上的寓言性。因为象征性的元素并非是意图去不停地、显著地形成任一人物或事件的意义。所以,寓言,举例而言寓言性的叙事,是一种文学布置,在此之中,作者连续地、有条不紊地使用表达的象征模式,展示了构建完好的情节、虚构的人物和行动,作为抽象概念诸如道德、宗教理念等的具体化、可见化,以至于有效地向读者传递作者的想象和信念。
《西游记》及其续书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者忽略了区分两种类型的寓言。正如古典史诗《荷马史诗》和《埃涅阿斯纪》,《西游记》是一个非连续性的寓言,在此之中,它不展示完整的寓言性的情节,而是伴随奇幻的战争、冒险桥段,表现了间隔性的象征图景。作者也赐予小说人物象征性的意义,或者运用它们把抽象概念人格化。诸如孙悟空作为心猿,六贼(第14章)和七个蜘蛛精(第72-73章),代表了六欲和七情)。但是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寓言性元素,远非试图去完整和连续地形成一个全面的结构,从中有条不紊地导出象征性的意义。举例而言,作者可能以一个代表某概念或抽象性质的人物开始,但在创造过程中,通过图像、行为及对整部小说的情节设置、人物刻画毫无贡献的寓言化表达方式,发展了人物形象。事实上,许多《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桥段,是以一段时期流行的奇幻旅程故事为基础,并不意图从读者中引发寓言化的阐释。《西游记》最明显和突出的特质,就是对五行运用的寓言化阐释及以内丹修炼术语认同西行之旅的取经成员。……有时候一个人物的特征和行为,并不充分适合他的名字或他象征性的名字所指向的清楚意涵。……一些学者指出了《西游记》中某些人物和行为的寓言性特质,但没有意识到西行之旅应当被看作非连续性的寓言,而不是连续性的寓言。他们尝试强加给小说每一部分都以寓言化的阅读,使之适合一种理解性的、连续性的象征意义,这只会导致激起持另一个相反极端立场的人的批评和嘲讽,断然否定作者一方任何寓言性的意图。真相可能在此之间:小说包含有象征性的元素,包罗了象征性的人物和事件,但作者无意在连续一致、象征性意义的叙事中编排他的人物和事件。另一方面,《后西游记》是与原著不同的续书。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西游记》基本上是一个连续性寓言,邀请读者对整个故事运用象征性的阐释,而不是单个人物或孤立的情节。尽管,小说中并非每一个细节都允许寓言性的阅读,但小说展现了作者对于发明一种完整而连续的寓言性情节的叙事形式的控制力,作者权衡之下的努力,使用一种象征性的模式、通过一系列相关情节和沟通配合的人物发展,来实现文学上及寓言层面上的多重意义。
在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中,“寓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寓言的概念不仅是解释某些文学作品的关键,也是理解人类思维形象化、抽象化能力的关键。刘小联认为,《后西游记》是一部杰作正在于作者对于以多元的寓言形态实现道德层面的追求,从手法上并不逊于《西游记》原著所创造的寓言结构。《后西游记》的作者,就像东西方其他通过寓言表现叙事的作家一样,试图通过建构寓言,这样一种较为间接的媒介,发挥独创性和想象力,抵达文学的教化功能。
2022年重读《后西游记》及其两本研究专著,是因为刘小联的妹妹刘晓华女士找到我。她告诉我,刘小联已经于2012年在美国病逝。他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读完博士后就没有再做比较文学的研究,而是又读了MBA后来做了理科的工作。他们一家原来也是上海人,后来搬去了北京。循着正确的名字,我又找到了其他的文章,看到了1980年,刘小联作为北外教师在北大学习美国文学的经历。我本来并不知道“Xiaolian Liu”这个名字怎么写。2002年《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有一篇《佛心的奥德赛》的编译稿,给作者署名为“刘晓廉”,我便直接沿用了。现在想起来,也是比较草率。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199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小说之传播》一书中,关于这本书的条目亦有错误的信息。写这篇文章,也是想做一个修正。
2022年2月的时候,刘晓华女士寄来一本品相更新的书留作纪念,她给我写了一张小纸条,说:“我替我哥哥把他这本您在文章和书中提到并引用的书赠送给您。祝您写作愉快!”我很感动,也许这是我作为一个《西游记》爱好者收获的最珍惜的缘分。
我曾给“笔会”写过一篇《〈后西游记〉在日本》的小文,提到了我找到两个《后西游记》日译本的经历。一年来,又有一些新的故事围绕着它。
《后西游记》的故事很简单,以四十回的长度二十多个事件讲述了《西游记》原班人马的后代再次聚合,面对一个仍然很糟的世界,打算重新前往灵山求取真解的故事。换句话说,故事的作者认为,唐僧一行人千辛万苦取回真经,却仍然没有带给国家良好的生机,为什么有了真经之后,这片土地依然是非颠倒、以讹传讹呢?也许是因为大家对真经理解得不对,所以要重新找一个取经团队,去灵山讨教真经的准确解释。于是,“小字号人物”唐半偈、齐天小圣孙履真、猪一戒、小沙弥前往灵山求取真解。
迄今为止,《后西游记》作者和出版时间均不确定。坊间读者估计也不会将它作为正经书阅读。我曾经在书店找到过一部残本四本,不知真假,仅存1、5、6、7、24、25、26、37、38回,书名为《重镌绣像后西游记》,右旁署“天花才子评点”,左下端刊“金阊书业堂梓行”,除上题“乾隆癸卯年新镌”,内容与版式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后西游记》的原刊影印本完全一致,和鲁迅《关于小说目录两件》所说的乾隆四十八年的重刻本提到的信息基本对得起来(“《后西游记》四十回。清天花才子评点。乾隆四十八年刊。十本。”)。写博士论文期间,我曾多次在引注中看到吴达芸的《〈后西游记〉研究》,但当时我没有找到这本书,只能标注为“未见”,并借由二手材料了解专著的结论,1983年吴达芸还在台南宏大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西游记析论》,以不少的篇幅论述《西游记》原著的关键词“不全”与喜剧人物的塑造。幸运的是,2021年我找到了这本出版于1991年的旧书。关于作者和版本的推论,吴达芸基本延续了苏兴发表于1983年《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的专论《试论〈后西游记〉》的推论,如认为《后西游记》作者为吴语区人,作品大抵写于明末、最早的评论出自刘廷玑等。1994年,有一部关于《后西游记》的研究专著诞生于美国,书名为《佛心的奥德赛》(The Odyssey of the Buddhist Mind:The Allegory of The Later Journey to the West)。
苏兴的专论虽然不长,但十分重要。他仔细论述了《后西游记》的基本情况,另外也为《后西游记》的主题定调为“刺儒以刺世,开《儒林外史》之先河”。在文末,他详细谈到了《后西游记》中韩愈与大颠(唐半偈)的交往于史有据。“刺儒以刺世”后为高桂惠延伸至“装僧与扮儒”的论述,她提醒我们作者署名“天花才子”,“天花”为法华经著名佛教譬喻,“才子”则为明清人士的自我封号。林保淳在《后西游记略论》一文中提醒我们“后西游记中有不少灾难是人为的”,出现了点石法师、自利和尚、冥报和尚、媚阴和尚等一听就和宗教人士有关的反派,最终指向为禅宗说法,调和儒释,这也影响了吴达芸的主要论述,即禅的美学转化在《后西游记》中是通过寓言的形式表达的。寓言所包含的两大质素就是诙谐与讽刺。主要的小说技法,则是将抽象名词拟人化,例如表面和气其实冷酷的阴阳大王,用圈套套人的造化小儿,手执春秋笔的文明天王等。
“寓言”一词,同样也是刘小联研究《后西游记》的关键词。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陆地区学者对《后西游记》的讨论聚焦于揭示、批评佛教(王民求:《〈后西游记〉的社会意义》),或者认为是一部“神话怪异小说”或者叫做“神魔灵怪小说”,内容上应视为“《西游记》之反动……刻意嘲弄佛法善门”(林辰:《关于〈后西游记〉》)已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讨论方向。换句话说,海外学者似乎开始注意到《后西游记》在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研究潜质。刘小联的论述借用芝加哥大学Michael J.Murrin教授对于两种类型的寓言(连续性的和非连续性的)的定义,区分了《西游记》与《后西游记》的文本性质,以区别于其他学者仅将《后西游记》中的抽象名词拟人化的文学现象作为修辞层面的考察,节译如下:
寓言常常为教化目的所使用,而且寓言也被看作是最极端、最有代表性的教化叙事形式之一。但不是所有教化作品都以寓言的形式展现,教化只是寓言叙事的一种特征。其次,更重要的是,区分寓言和其它形式的叙事的标准,这个标准在我们的案例中,从《西游记》中脱胎的《后西游记》,取决于象征模式利用的方式和程度。Michael J.Murrin在他关于寓言性史诗的讨论中区分了这两种寓言形式:连续性的(continuous)和非连续性的(dis-cont inuous)。非连续性的寓言范例包括了《荷马史诗》、弗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文中特定的人物和行动被看作是象征性的,其他的则不是。举例而言,《埃涅阿斯纪》中的神被当作象征人物,艾尼阿斯则不是。《荷马史诗》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的非凡面貌是寓言的,即一个象征(symbolized)与浓缩(condensed)复合(complex)及看不见的过程。另一种形式则是连续性的或持续性的寓言,使得全部情节是寓言性的,或对读者提出在所有方面象征性的阐释的要求,如但丁的《神曲》与斯宾塞的《仙后》。……因此,在一个非连续性寓言中,寓言特质与象征性的人物变成孤立而断断续续的现象,而在连续性的寓言中则有一个连续性和持续性的过程。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即使展示了寓言性技巧不连续性的使用,严格来说,也不是叙事意义上的寓言性。因为象征性的元素并非是意图去不停地、显著地形成任一人物或事件的意义。所以,寓言,举例而言寓言性的叙事,是一种文学布置,在此之中,作者连续地、有条不紊地使用表达的象征模式,展示了构建完好的情节、虚构的人物和行动,作为抽象概念诸如道德、宗教理念等的具体化、可见化,以至于有效地向读者传递作者的想象和信念。
《西游记》及其续书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者忽略了区分两种类型的寓言。正如古典史诗《荷马史诗》和《埃涅阿斯纪》,《西游记》是一个非连续性的寓言,在此之中,它不展示完整的寓言性的情节,而是伴随奇幻的战争、冒险桥段,表现了间隔性的象征图景。作者也赐予小说人物象征性的意义,或者运用它们把抽象概念人格化。诸如孙悟空作为心猿,六贼(第14章)和七个蜘蛛精(第72-73章),代表了六欲和七情)。但是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寓言性元素,远非试图去完整和连续地形成一个全面的结构,从中有条不紊地导出象征性的意义。举例而言,作者可能以一个代表某概念或抽象性质的人物开始,但在创造过程中,通过图像、行为及对整部小说的情节设置、人物刻画毫无贡献的寓言化表达方式,发展了人物形象。事实上,许多《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桥段,是以一段时期流行的奇幻旅程故事为基础,并不意图从读者中引发寓言化的阐释。《西游记》最明显和突出的特质,就是对五行运用的寓言化阐释及以内丹修炼术语认同西行之旅的取经成员。……有时候一个人物的特征和行为,并不充分适合他的名字或他象征性的名字所指向的清楚意涵。……一些学者指出了《西游记》中某些人物和行为的寓言性特质,但没有意识到西行之旅应当被看作非连续性的寓言,而不是连续性的寓言。他们尝试强加给小说每一部分都以寓言化的阅读,使之适合一种理解性的、连续性的象征意义,这只会导致激起持另一个相反极端立场的人的批评和嘲讽,断然否定作者一方任何寓言性的意图。真相可能在此之间:小说包含有象征性的元素,包罗了象征性的人物和事件,但作者无意在连续一致、象征性意义的叙事中编排他的人物和事件。另一方面,《后西游记》是与原著不同的续书。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西游记》基本上是一个连续性寓言,邀请读者对整个故事运用象征性的阐释,而不是单个人物或孤立的情节。尽管,小说中并非每一个细节都允许寓言性的阅读,但小说展现了作者对于发明一种完整而连续的寓言性情节的叙事形式的控制力,作者权衡之下的努力,使用一种象征性的模式、通过一系列相关情节和沟通配合的人物发展,来实现文学上及寓言层面上的多重意义。
在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中,“寓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寓言的概念不仅是解释某些文学作品的关键,也是理解人类思维形象化、抽象化能力的关键。刘小联认为,《后西游记》是一部杰作正在于作者对于以多元的寓言形态实现道德层面的追求,从手法上并不逊于《西游记》原著所创造的寓言结构。《后西游记》的作者,就像东西方其他通过寓言表现叙事的作家一样,试图通过建构寓言,这样一种较为间接的媒介,发挥独创性和想象力,抵达文学的教化功能。
2022年重读《后西游记》及其两本研究专著,是因为刘小联的妹妹刘晓华女士找到我。她告诉我,刘小联已经于2012年在美国病逝。他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读完博士后就没有再做比较文学的研究,而是又读了MBA后来做了理科的工作。他们一家原来也是上海人,后来搬去了北京。循着正确的名字,我又找到了其他的文章,看到了1980年,刘小联作为北外教师在北大学习美国文学的经历。我本来并不知道“Xiaolian Liu”这个名字怎么写。2002年《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有一篇《佛心的奥德赛》的编译稿,给作者署名为“刘晓廉”,我便直接沿用了。现在想起来,也是比较草率。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199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小说之传播》一书中,关于这本书的条目亦有错误的信息。写这篇文章,也是想做一个修正。
2022年2月的时候,刘晓华女士寄来一本品相更新的书留作纪念,她给我写了一张小纸条,说:“我替我哥哥把他这本您在文章和书中提到并引用的书赠送给您。祝您写作愉快!”我很感动,也许这是我作为一个《西游记》爱好者收获的最珍惜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