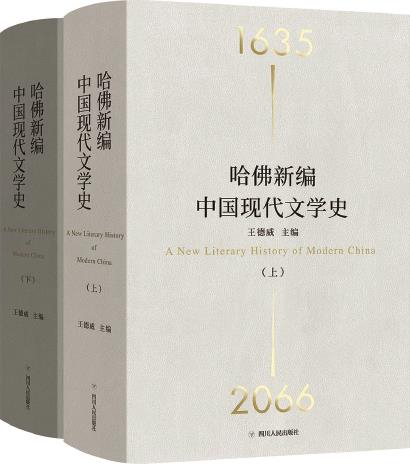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2-10-24 第27,392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一个“世界中”并开放的文学史实验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王德威 主编 张 治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徐德明四川人民出版社《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22年出版,是该书第三个版本,以下简称《新编》)新近面世,初版的哈佛《A New Literary of Modern China》已经五岁了。这书中英文译本的身份标记,可借鲁迅小说自评“格式之特别,表现之深切”一语来形容,因其“特别”而令人耳目一新,也难免让人耳目一眩。
“特别”或“深切”都是该书主编、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有意为之,“特别”在格式文风亦庄亦谐,“深切”的叙事见微知著。历史之崇高庄重,中西同理;它让人会心一笑的地方,也不容忽略。《新编》凭其格式可以别号“故事新编”,大到战争、革命“世界中worlding”,小至贾植芳某天做棉衣的琐事,回头看,波谲云诡的文史底下往往藏着许多荒唐可笑。而《新编》的正经叙事与幽默滑稽,被哈佛英文版封底荐语赞为“史无前例”与“异想天开”。有趣的是,哈佛版的页码共1001页,这“一千零一页/夜”的巧合,莫非是在呼应王德威“讲故事”的编史格式?
实际上,王德威在书中经常留下一些跨越古今和历史庄严的开“玩笑”的设计。四川版的封面,顶天立地的年份数字表示历史起讫:天头1635,地头2066,呼应封底荐语“漫长的现代”。这个起讫年份,可不是一般断代史的时间逻辑。《新编》第一章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用了复数beginnings,“1635,1932和1934”。这是在说时隔300年而同属于一个开端?不,这是他的对话的历史观,意指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三个年份与相关人的对话中开启,转瞬就是300年。这样的“异想天开”思路,让学界同人也未免琢磨不定。
《新编》哈佛版的封面是水墨画,繁体字版封面也有书、画两可之间的一抹墨痕,王德威喜爱。他是溥心畬的再传弟子,画的成就距师祖远近不好说,但哈佛版用中国画配中国的文学史,则是上佳选择。中国画的笔墨韵致和魅力在于勾勒点染,这与《新编》的特别格式符合若契。鲁迅《故事新编》的艺术精神在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新编》161篇故事各有“因由”,开篇那一笔“点”的位置方式各得天机/心机,143人写161篇,有人作多篇,每个“点”是唯一设计;《新编》之“染”衍化为辐射、发散,或说是“彰显”,在白纸上层层水墨湮染,有彰显也有遮蔽。
以文章为“史”,重点偏至于“论”。《新编》对公认的大作家,不大在意讨论其代表作,而注意种种契机时间点上人的作为。这是王德威的策略:人无我有,人有我略。英文版甚至以虚构小说代区域文学历史,与历史体例传统的期待视野相去甚远,四川版对这一点作了局部调整,而使其稍接近于“期待”。鲁迅的多脉络化,让他出现在不同文章中,至少三人论及《墓碣文》,而哈金叙述周树人如何做起《狂人日记》来,则是必然中的偶然。又如《老舍和美国》一篇,彰显中国现代作品翻译为外语的独特过程,所见处:老舍选择独特的翻译工作方式,与蒲爱德、郭静秋逐字逐句对面讨论原文及英文表达。此文尚有不见处:老舍与伊万·金的翻译竞争。后者以东方主义的眼光把《骆驼祥子》《离婚》都改为大团圆,为捍卫作品主体(悲剧主题)与版权,老舍在美国进行了中国人第一个版权诉讼。
因为每篇文章的事实是“因由”而非“始终”,《新编》留下了更多的对话空间。如果读者习惯以过去的文学史经验来看《新编》,会有“《新编》未完”的感受。的确,它不是历史完形,却是开放的,读者进入了此书语境,理清上下文关系,抓住了脉络,也发现了空隙,而当你下决心补苴罅漏,也就成为潜隐的作者了。
161篇文章,都是论事析理、包涵学术内容、深入浅出的文章。143个学者和作家,有人不止一篇。王德威本人作六篇,其中,《错置的时代:西洋鬼子、中国天师》解析源于《水浒》的《荡寇志》故事新编模型,嵌入科学技术与迷信并置的近世主题;《从摩罗到诺贝尔》从鲁迅写《摩罗诗力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彰显从反抗到协商的文学主体;《解冻时节》透视贾植芳一则日记,人生由颠沛复归平常的冷峭,其评析过程是抒情文学;《从西夏到东北》谈骆以军、齐邦媛两代作家,家族前世生活相关的地理、历史演绎为虚实故事,论者借以反观文学台湾。六篇文章风格与写法各异,没有一篇单音奏鸣,巴赫金复调仍是王德威的基调。
王德威的论著漫射着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的西方文论。钱锺书“锥指管窥”的文史叙述方式不是通史与大叙述,也不是断代史,而是“东西攸同”的复杂脉络。王德威时代的文类比钱锺书更其复杂,写作文学史而采用传统文体论不大行得通,所以,由史实、文论交汇与对话的文章整合的文学史必然产生,这不是文学史产业的延伸,而是发挥“论”的主体性的当代选择,但是它有一个弥补空隙的前提,要求此文学史的读者主动完形。一切都是“世界中”。《新编》未完,它是一个实验,也召唤大家参与探索的实践。
在我看来,《新编》写法固然具有实验意味,其实对读者而言,读法亦可实验。你可以拿《新编》当一个球,文章知识点星散于球面,161篇文章作者任意一点出脚踢球,它就滚动起来。踢者脚法不一样,球的运行轨迹与远近皆不相类,欣赏各自的脚法与球的轨迹就是最佳读法。如此说来,也不必按部就班于编年,顺序读、倒序读、跳着读皆可。拘泥于编年并无大益,《新编》叙事循“因由”,不是“纪事本末体”的有头有尾。最重要的是论述——论文衡史,文心为尚,理解论述主体,摸索所循古今文脉,在或隐或现中得其大意。寓古于今,现代文学30年,涵盖千百年文史,让传统活在论述中。
万变不离其宗,“世界中worlding”是根本,“现代”向未来、也向过去延伸,“中国”是国家也是文明,文学史讨论的过程就是面对彰显历史文化生命之文的生生不息。人在生生不息中,从英文到中文的《新编》是“世界中”的生态,王德威的这一学术方向也正“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