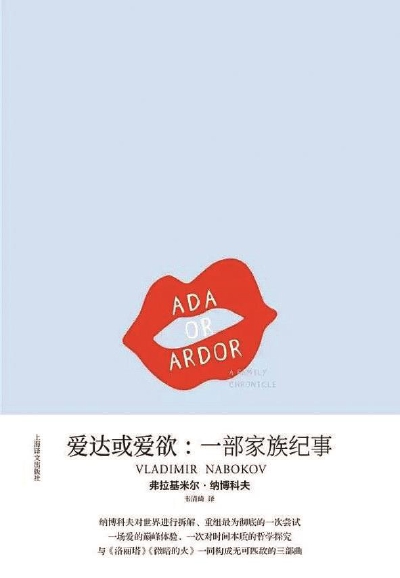■刘蔚
《爱达或爱欲》创作于纳博科夫的晚年,是其倾尽心血打造的巅峰之作。这部长篇小说与《洛丽塔》《微暗的火》一起,构成了纳博科夫最重要的文学三部曲。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反地界”的星球上。1884年夏天,14岁的少年凡·维恩来到阿尔迪斯庄园的玛丽娜姨妈家做客,初遇两个表妹——美若天仙的12岁的爱达与单纯任性的8岁的卢塞特。凡与爱达一见钟情,但是,爱达其实是玛丽娜与凡的父亲德蒙珠胎暗结的产物,后来德蒙娶了玛丽娜的妹妹阿卡,但阿卡因精神失常自杀身亡了。因此,凡与爱达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妹。虽然他们的不伦之恋为社会所不容,甚至有被“阉掉”的危险,但他们不管不顾,爱得偷偷摸摸,又轰轰烈烈。谁知,爱达的妹妹卢赛特也爱上了风流倜傥的表哥凡。在遭到凡的拒绝之后,绝望至极的卢赛特跳入茫茫的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炽热的命运之轮裹挟着三个表兄妹展开的长达近百年的爱情长跑中,他们或以身殉情,黯然消亡;或悲喜交加,抵达情爱的巅峰。忠诚与背叛、爱恋与仇恨、自私与忘我、冷酷与温情、喜悦与绝望,这些人性的所有元素,构成了一部跨越时空、丰饶浪漫的家族纪事。
纳博科夫以细腻灵巧的笔调,抒写了凡与爱达的惊世之恋从萌芽、生长、喷发到背叛、重逢、成熟的整个过程,千回百转,层次分明。荡气回肠。14岁的凡第一次在阿尔迪斯庄园与爱达相遇,作家细致地描写了她那直瀑般的秀发、苍白脸颊上的酒窝、合身的褶裙、雪白的小腿以及宛如东方催眠师般朦胧神秘的眼神,给凡留下的难以忘怀的印象。凡对“豆蔻梢头二月初”的爱达一见倾心,但直到四年之后在阿尔迪斯庄园重聚,他们才终于投入到了热烈、缠绵而又销魂的情欲的火焰之中。爱达对蝴蝶的迷恋、同样的博览群书,使这对少男少女有聊不完的话题,也让他们不仅有肉体的结合,心灵也靠得更近。然而,凡发现了爱达与一位伯爵的儿子和一个钢琴师的情感纠葛,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爱达给凡写了好多封信,表达了自己对他炽热的爱。多年之后,爱达的丈夫去世,凡则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学者,两人可以毫无顾忌地生活在一起了。两人见面后,凡发现昔日那个集颀长、优雅和野性于一体的爱达已经荡然无存,代之以圆润富态。时光凋谢了鲜花,岁月沧桑了容颜,不变的,是爱达是凡心中永恒的女神。她于他,就像贝雅特丽采之于但丁,格蕾卿之于浮世德。在他们再度相聚的瑞士“三只天鹅”宾馆,凡在房间的阳台上看见了走到下面的爱达,作家用极富诗意的抒情的语言描写了此时此刻凡眼睛中的爱人和他内心的渴盼:“她会抬头吗?她所有的花儿都发现了他,她微笑着,而她像女王般欠了欠身,向他呈送着群山、云雾以及游弋着三只天鹅的湖。”
《爱达或爱欲》是最能体现“纳式风格”的作品。纳博科夫以其娴熟的小说技巧,不断地变化叙述方式和视角,运用戏仿、暗示、反讽、隐喻、重构、象征、双关、音韵等各类修辞和语言手法,构建了一个繁复迷人、五光十色的游戏与爱情的迷宫,藉以解析时间流淌的肌理,探讨爱与人生的本质。少年凡初遇爱达,一见钟情,“他知道,真的。他喜欢吗?喜欢。实际上,他开始热烈地喜欢上了爱木、爱欲和爱达(arbors and ardors and Adas)……”arbor的原意是乔木、树,ardor的原意是激情、情欲,作家将这两个词汇与爱达的名字Ada搭配在一起,巧妙地押了头韵,语音响亮而流畅,表达了一种热烈奔放的情感。译者则巧妙地将其译为爱木、爱欲和爱达,既保持了原文的头韵特色,而又让译文神韵兼备。
按照新西兰学者博伊德的观点,小说中的中心场景阿尔迪斯庄园是对天堂的戏仿,那么,凡则可以理解为纳博科夫在这个令人爱恨交织的人物身上戏仿了欧洲民间传说中的风流浪子唐璜和卡萨诺瓦。甚至凡知道了另两个男人与爱达的情感纠葛后,怒气冲冲地前去决斗,也是对普希金与情敌丹特士决斗(或者说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奥涅金与连斯基的决斗)的戏仿。凡与爱达陷入了热烈的爱河之中,小说中的一句抒情之语——“金星挂上了苍穹,维纳斯嵌进了他的肉体”,就是对爱情在凡的心中扎根的比喻和象征。凡的父亲德蒙(Demon),英文原意是魔鬼,作家称凡的身体里“流有他父亲的魔鬼之血而变得强壮”,“魔鬼之 血”(demon blood)显 然 与“德蒙”(Demon)构成了一个绝妙的双关。小说中,顺序与倒叙、回忆交织,以凡的视角的表述与爱达的回忆互为映照甚至矛盾。比如,在凡的印象中,他第一次见到爱达:“爱达捧着乱蓬蓬的一束野花。她身披白色斗篷,配着黑色夹克,长发间嵌着一只白色蝴蝶结。”爱达则反驳他是在做梦,她从未有过这样的衣服,也不可能在大热天穿黑色夹克。爱达的表达可以视之为一种重构,只是没有完成。而德蒙和玛丽娜的偷情与凡和爱达的不伦之恋,阿卡的自杀与卢塞特的跳海自尽,前者都是对后者命运的一种暗示,暗示这个家族的情爱传统,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宿命的意味。
纳博科夫学识渊博,精通俄、英、法三种语言。他在小说中大量地使用各种修辞和写作手法,在三种语言之间不停地转换,将许多真实的地名、人名掐头去尾,又添油加醋,形成许多新的虚构的地名、人名,借以戏仿或反讽,层出不穷,乐此不疲。小说中由此出现了大量的注释,这难免有掉书袋之嫌,却也是作家和读者玩的烧脑游戏。可见,要成为纳氏小说的“伟大的读者”,是多么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