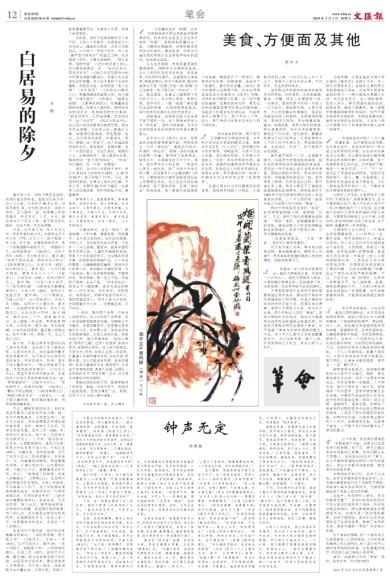徐建融
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寺庙中,大都设有钟鼓楼,用以播报时辰。一般以撞钟报晓,击鼓播晚,即俗称的“晨钟暮鼓”。如陆游《短歌行》所云:“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钟暮鼓无休时。”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古诗词中,自然也多闻晨钟的堂堂之音、正正之声,如“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常建)、“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岑参)、“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钱起)、“晓上篮舆出宝坊……已觉钟声在上方”(高翥)等等。
基于这样一个常识,对于唐代张继脍炙人口的绝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北宋的欧阳修便在《六一诗话》中提出了质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
不过,这一质疑也遭到了后人的反驳。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认为:“盖公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
但是,这样的解释,事实上并没有恰切地说明打钟的时间问题。在古代,不仅包括寒山寺在内的“吴中山寺”,天下寺庙皆然;不仅寺庙,甚至城市亦然,除了清晨拂晓,夜半也常被规定为打钟的时间。汉崔元始《政论》:“永宁诏:钟鸣漏尽,洛阳城中有不得行者。”三国魏田豫则有言:“年过七十而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后二句意谓夜半钟声响过之后,还在城中行走,不肯睡觉休息,等同犯罪的行为。无非清晨的打钟制度较为普遍并执行得相当严格,而且钟声嘹亮,人们已早起,故闻者众;夜半的打钟制度不太普遍并执行得相对宽松,而且钟声空寂,人多在深睡,故闻者罕。致使大多数人误认为打钟只能在清晨,不能在夜半。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提到:“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闻。”这里的“疏钟”,显然也是在深夜打响的。当然,它未必出于辋川山庄,而是来自远处的城市或寺庙。
尤其在寺庙中,除清晨和夜半之外,其他时间也是可以打钟的,其目的不一定是为了播报时辰,而是为了做功课、作法事、集聚僧众、接待香客等等,则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的仪轨了。
著名的“饭后钟”故事,打的是午钟,用来召集僧众用餐。王定保《唐摭言》记:“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至于暮钟,那就更清响不绝于古诗文中了,如“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沉夕……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韦应物《夕次盱眙县》)、“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李白《听蜀僧濬弹琴》)、“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王维《过香积寺》)、“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云又几重” (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欧阳修《晚泊岳阳》)、“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唯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苏轼《和梵天僧守诠》)、“晚度孔间谼,林间访老农;行冲落叶径,坐听隔岸钟”(贺铸《题田家壁》)、“鸟外疏钟灵隐寺,花边流水武陵源”(洪炎《四月二十三日晚同太冲、表之、公实野步》)等等。“西湖十景”的“南屏晚钟”,更为众所周知。这些钟声,不外是做功课、作法事、召集僧众、接待香客时所撞发。它的意义,与播报时辰基本无关,而是重在“扬声息苦”。
据佛经所载,昔罽昵吒国王贪虐作殃,受马鸣大士教化,殁后生大海中作千头鱼,常受剑轮斩截,苦不胜忍,唯闻某寺钟声,剑轮暂停,苦亦少息。王致梦白维那曰:“惟愿大德垂怜,矜悯击扬,延之过七日已,罪报毕矣。”以是因缘,西域诸寺,不时扣钟震响,遍地咸闻。我国则肇始于梁武帝问志公:“朕欲息地狱苦,宜以何法?”曰:“冥界惟闻钟声,苦能暂息。”于是遍诏天下佛寺,凡击钟声,随缘不时,宜舒其声,庶几无尽法音,响震重泉,超拔冥界,惊醒尘寰,护佑福报,广大教化。
今天,无论城市还是寺庙,基本上都已不再用钟鼓来播报时辰。即使大年三十(除夕夜)的“烧头香”、“撞头钟”,也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但寺庙里凡做功课、作法事、召集僧众、接待香客等活动,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撞钟的仪轨。自然,这时钟声在什么时候响起,是因人因事,随缘无定的。
以我个人的经历,浙江慈溪的伏龙禅寺,是与我十分亲近的一座千年古刹,寺中的大部分建筑包括钟鼓楼,早已毁于日寇的兵火。一口大钟,便只能置于重建的琉璃宝殿内。我每次上山,一般多在薄暮时分,首先到大殿中上香礼拜,礼毕,便在住持传道法师的引导下撞钟三响——这钟声,同样不是按规定的时间所击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