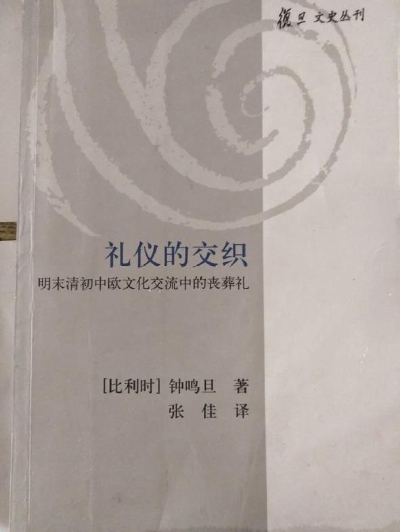冷战之后的新一轮全球化,造就了规模空前的跨地域和跨文化交往,它究竟会带我们走向何方?是和谐共处的乌托邦还是对立冲突的索马里?有的学者对此非常乐观,比如弗里德曼就宣称世界是平的,但更多的学者并不乐观。美国学者亨廷顿断言异质文明必然爆发冲突。看看如今遍地狼烟的中东,其说几成先知之论。不过,亨廷顿的观点并非严格的学术分析,因此,众多跟风讨论大都陷于中西义理之辩,纠结于抽象概念,比如文明究竟是什么?是否可以笼统地看待文明?如何看待各大文明中像儒释道和新教与天主教等不同文明的支派等等?结果,文章越来越多,概念反倒越来越模糊,至于具体考察东西方文明冲突发生学更是不可求了。
一片喧闹之中,《礼仪之争》一书仿佛一股清流。作者李天纲教授深受朴学影响,不在中西价值理念上空发议论,而把考察对象落在无处不在的礼仪层面。这种研究路径可察、可证、可辩,远比泛泛宏论中西本质更能理解文明的差异是如何演变成矛盾乃至冲突的。李天纲利用先前很少人注意的明末清初传教士和罗马教廷的文献,追本溯源满清与罗马教廷从分歧到矛盾到冲突的前因后果:大搞文字狱的康熙沐猴而冠,犹嫌不足,居然异想天开,想效仿亨利八世搞国教,最后自然踢到铁板。尽管《礼仪之争》开创了礼仪为对象的文明交往研究新维度,但其结论却似乎强化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宿命论。
难道不同文明就没有融合的空间和可能吗?20年后,同样比较东西方礼仪制度,同样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性的比较研究方法,比利时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新作《礼仪的交织: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礼》却发现了另一个可能:异质文明绝非如本质主义论者所言是互不兼容、互相对立的,相反,一定条件下的自发互动会走向礼仪契合共荣的道路。
钟鸣旦研究的是丧葬之礼。按理说,中西丧葬礼截然不同,几乎处于对立两端。服饰上,中国人从白色,欧洲则袭黑衣;时间上,中国人丧葬分离,为时可达数年,而欧洲则丧葬合一,不过旬日;场所上,中国人丧礼主要在家中举行,而欧洲主要在教堂;墓址上,中国葬在郊外,欧洲则是城中教堂;参与者而言,中国人按照血缘上差序格局依次敬礼叩头,偶有僧道法事,而欧洲则是牧师主持,家庭与社区成员组成送葬队伍;丧物方面,中国设灵牌或画像,供奉食品,而欧洲绝无此类。巨大的反差背后是不同的信仰。中国人视死如生,相信先人有灵,丧葬礼仪则是体现孝道的最重要途径,所以才会有磕头、供食、子女长时间守孝等规矩,而天主教则相信死亡之后就是天堂地狱两途,人生大事是面对上帝而非父母,所以没有孝道之说。显然,中西丧礼从里到外处于高度张力之下,看似水火不容。可是,令人惊奇的是,丧葬礼非但没有引发儒教与天主教的对立与恶斗,反而在17世纪出现了传教士李安东1685年在广东草拟的《临丧出殡仪式》,建立起一套兼容儒教的《家礼》与天主教的《罗马礼书》的丧礼制度。那么,这一融合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呢?《礼仪的交织》主要论述的就是这个问题。
该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综述理论框架和相关文献。作为汉学大师许理和的高足,钟鸣旦不仅精通古汉语和传统考据方法,熟悉明末清初中文和拉丁文的文献,也受过专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训练。他明言自己着眼于文明的“互动”,而所用的是历史人类学而非思想史的研究路径,移今法入古境,类似格尔茨所说的“深描”方式详细考察礼仪变迁。这种研究方法自然要依靠大量古代文献。钟鸣旦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收集了大量17、18世纪有关中国丧葬礼的中西方文献。有的是利玛窦、金尼阁、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和曾德昭等前仆后继来华的耶稣会士等所记载的中国丧礼,这些记载散落在各大介绍中国风土的百科全书中;有的是各类改进传统丧礼的建议,比如传教士李安当在广东草拟的《临丧出殡仪式》和中国地方教徒提出的《口铎日抄》等。第二部分从第三章节到第七章一步步展开论述天主教丧礼本土化进程。按照钟鸣旦的论述,这个过程经历了价值判断、认知调整、自发创造和自觉改进等四个阶段。最初传教士并不知道丧葬之礼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因为祭祖和灵牌等表象而斥责中国丧礼充满偶像崇拜,中国的儒生们反过来指责天主教轻视丧葬礼仪,不尊孝道,有害华夏。传教士们逐渐认识到华夏文明不同于先前他们遇到的土著,在教育文化程度上比肩欧洲,甚至在礼仪制度上要比欧洲更为精致。平等的交流使得他们改变了认知。利玛窦们尊儒教而拒释道,着儒服、学汉语,一方面赞同儒家推崇的《朱子家礼》,认可设置灵位并叩头等行为,宣称这些是国民(civil)礼俗而非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又依据《家礼》与儒生一起排斥堪舆纸钱等佛道邪礼。与传教士相呼应的是中国民间社会一批信仰天主教的乡绅。他们在各地自发地开始丧葬礼革新。比如,著名天主教徒杨庭筠的葬礼虽然也供奉食品,但这些食品分享给了穷人和监狱囚徒而非五服之内的亲戚友朋,与16世纪西方社区慈善举动别无二致。“这些新创立的礼仪,试图在传统的孝道表达方式与天主教正统之道中间,保持一种平衡,他们只是为了纪念死去的父母而非崇拜。”(第106页)。越来越多的自下而上的礼仪创新促使传教士们开始自觉地进行本土化改革。在1667年底的广州会议上,20多位传教士“不再只是被动的容忍这类仪式,而是积极地对它进行提升改造,并将其纳入到天主教活动中来”。由此,中国天主教徒丧葬礼上,传统要素比如画像、丧服、蜡烛、香、香水、贡物和音乐等一样没缺,但却赋予了天主教内涵:天主教士或者天主教团契的会长取代了僧道,教会祷告和吟唱取代了佛教的念经,贡物不再是给亡人的食品,而是给社区共同体成员的分享。在第三部分,钟鸣旦进行了理论总结。他以《天工开物》里织布作为比喻来显示中西文化彼此交流中丧礼制度嵌合的复杂性。透过仪式制度的变迁,作者进一步指出变化的背后是群体或个体身份认同重新建构的过程,因此,丧葬礼融合的重要性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在中国建构了一种内在和谐的新型复合身份,即信仰天主的基督徒与遵循传统礼教的中国人可以合二为一。
钟鸣旦的《礼仪的交织》无疑是中西礼仪制度比较研究的又一本重要著作。表面上,他得出的观点似乎与李天纲的研究大相径庭,其实细细咀嚼,两人的研究其实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如果说李天纲把视野放在满清朝廷与罗马教廷,看到的是专制君主颟顸自大对文明交往的负面作用,那么钟鸣旦则是下移视野,从王公贵族和宫廷传教士转向民间无数知名或者不知名的乡绅和普通信徒,从他们的活动中寻找互动和融合。他的研究显示,文明交流中民间底层无数普通人交往与制度创新对于文明融合常常产生巨大的有时却被低估的价值。总之,钟鸣旦的研究大大推进了明清日常宗教实践活动的研究,他所采用的各种方法,无论是历史人类学还是文本阐释学,都堪称研究范式的典型,对日后学者研究文明交往与宗教互动都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