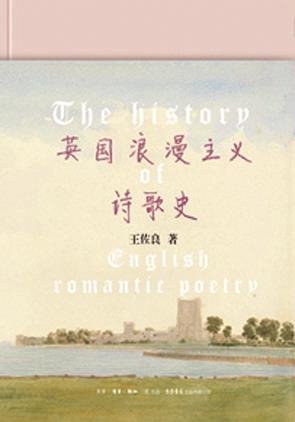■张家鸿
翻译家王佐良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中,遗憾鲁迅与闻一多未竟于文学史研究,同时又认为他们俩其实树立了“用优美的文笔来写文学史的先例”。
真正的文采并非刻意的舞文弄墨,而是“文字后面有新鲜的见解和丰富的想象力,放出的实是思想的光彩。”可见在王佐良看来,真正的文采最应被看重的是思想,其次是见解与想象力,文字的筹措与选择仅仅是铺垫而已。王佐良在书中以时间为线索,收录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济慈、司各特等人的小传与作品。履历与作品相对应,知人论世与作品解读互为依傍与衬托,思想的光芒在两者的互相交替中闪烁。
农民诗人彭斯在《致拉布雷克书》中这么呼唤着:“我只求大自然给我一星火种,我所求的学问便全在此中!纵使我驾着大车和木犁,浑身是汗水和泥土,纵使我的诗神穿得朴素,她可打进了心灵深处!”在我看来,整首诗的节奏朗朗上口,如民谚般通俗,从头至尾酣畅淋漓的表述皆源于无处不在的土地和大自然。谈到苏格兰民歌给予彭斯的影响时,王佐良认为绝不仅仅只是某种形式或音乐性,而是一整个独立的诗歌世界,“其根基是深厚的苏格兰人民传统,古老而纯朴,没有书本气,特别是没有英格兰文学的书本气。”读过王佐良的评介,我深感他与作者之间已然建立起牢固的心有灵犀。
在我看来,王佐良的文字正如他眼中创作《唐璜》时的拜伦:“他把读者当作一个秉烛夜谈的朋友,要使他听得有趣,而且一直听下去”。在追记诗人的人生历程时,作者努力挖掘他们隐秘又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者倘若跳过诗歌,只读诗人的履历是可以的。倘若跳过诗人的履历,只读王佐良的评论也未尝不可,因为某些文字其实可以独立成篇。王佐良自有一种组合文字的魔力,让它们自我聚合、包裹成一道可供咀嚼、赏鉴的美丽风景。
“为了写好文学史,应该提倡一种清新、朴素,闪耀着才智,但又能透彻地说清事情和辩明道理的文字。”把自家观点置于序言里,可知他对鲁迅、闻一多等前辈未竟之业的有心继承,可见他多年研究之中不遗余力的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