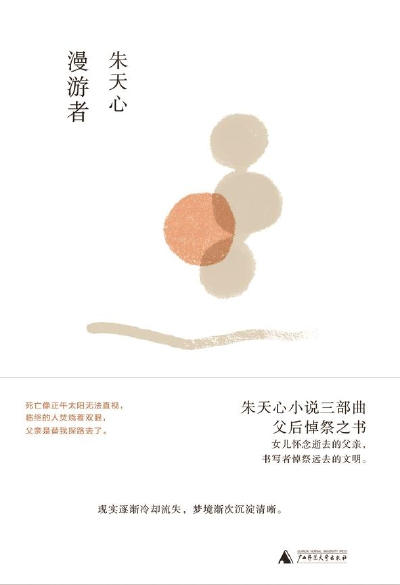■蟠龙海
濒死的体验以及死后的世界无从传递和保留,描摹起来也颇具难度,但死后之事和后人的感受终是可以被记载的,因此,悲悼悯惜亡者构成了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朱天心就是通过《漫游者》的文学想象,重建与亡父中断了的生命关联和情感交流,如书名所示,悲恸和思念呈现无边无涯之势,漫漶于四野八荒。能把死之恐惧加以美化,写得如此散逸,必对人生抱持着深邃的观望和透彻的觉知。
很明显,朱天心受到了爱伦·坡等前人的启示,但她笔下的死亡,并不苍凉,反而生就出一丝丝人间烟火气。死神的踪迹也烟消云散,这便是得益于朱天心偏偏把死亡暗合在阳间的世界里去写,造成了“人鬼并不殊途”的意境。追悼亡父,反而使朱天心保持着对生命的省察与觉悟,拓展出对自我疆域的认识,从而最终完成对死亡的超越,这便营造出另一番“死,而不亡”的希望所在。这让人不禁想起台湾电影《父后七日》中的两幅场景:小时候,父亲用单车载女儿回家;父亲的葬礼结束,两者对调位置,女儿把父亲的遗像挂在后座,那一幕,仿佛恰好例证着朱天心笔下的“漫游”二字——血缘生命体的对接、代际情感的追溯、无垠时光的奔逝……无不可以解释张爱玲何以在《对照记》里指着祖父母的老照片幽幽地说:“等我死的时候,他们会再死一次。”
文学是关于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意识的总体性的审美呈现,死亡,只不过是以否定的形式去确证生的价值,死亡彰显的生命有限性,恰恰可以促进每个人探寻、规划和省察自身活着的意义——死亡虽是短暂肉体的终结,但往往又意味着精神的升华,直至永恒。死亡意识、死亡叙事皆对推动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等发挥着显性或隐性的影响,故而说文学真正的诞生地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文学,两者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绝非危言耸听。
恰是因为与死亡的勾结与媾和,使得古今中外许多文艺作品读来格外荡气回肠、动人心魄:黛玉之死、安娜之死、维特之死是所在作品中最打动读者、最令人深思、也最具美学价值的经典桥段。村上春树、川端康成、渡边淳一等日本作家群体常借樱花、白雪意象之瞬美、易逝,创造出的独特的“物哀美”……笔墨间,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和幽玄的虚无感。传奇般的经历和独特复杂的遭遇,强化了海明威对生命的理解,人生后期的沉病重疴,更造就了他对死亡情结有着神经质般的敏感,因此,其作品中的人物时不时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着,但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是平静的,所释放出来的那种大无畏以及从容,分明展现出海明威对死亡的理解和尊重——能以坦然心态,理智地接受死亡,并领悟其真谛,这是一种蔑视死亡、无畏死亡的硬汉精神。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展现了各种形态的“孤独”和形形色色的“死亡”,两者紧密相连——孤独必然导致死亡,孤独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爱伦·坡将死亡意识糅进诗歌中,对生命加以形而上的沉思,在书写中将死亡意识与生命沉思融化为一种审美特质,并通过诗句将死亡的场景寓言化,通过散文诗《沉默——一个传奇》和诗歌《海中之城》《不安的山谷》这些文本,印证了语言与死亡之间那天然不可割舍的联系。
通常来看,文学家们通过文字不外乎表达对于死亡的三种态度:第一,肯定死亡;第二,否定死亡;第三,超越死亡。《漫游者》通过瑰丽而饱满的想象力,带着父亲的亡魂重游、复刻他的人生路,借此来启示我们生命形式是不朽的,所谓的“死亡”仿佛也只是暂时的,它最终将转化为另外一种存在,与茫茫天地同行。生既是死,死就是生,朱父的“死”与朱天心的“生”之间形成默契十足的回环:“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体。”(庄子《南华经》)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须从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现象。”人是必死的存在,不妨说得更诗意点,人终归是向死而生的。或哀戚,或悲壮,总之,死亡成就了文学的核心审美和情趣。死亡之于文学家,正如蛋炒饭之于厨师,考验的都是简中见繁的真功夫。亡父之死,成就了朱天心,既让她跨越年代的鸿沟,对上代人陡增几许了解与敬意,更对生活之况味多有觉知和感怀,从《漫游者》可观之:向死而思,类似于向死而生,贯穿了生与死之间的通途,特别是朱天心把死亡当起点来写,以“死”写“生”,把生的美好当作目标,展现的都是高级的笔意和笔法,无论如何铺陈死亡场景,抑或建构死亡意象,朱天心笔下的文字终极的眷注是征服死亡的凛冽,反其道地歌颂生的快意。换言之,无论死亡何等荒凉、凄厉和恐怖,她都着力激励人们追寻一种生命的真实,死亡造成的天人相隔、生死殊途等悲苦和创伤被她换就了一番团圆、再生姿态。于是,书写,在它远离时间、空间和肉体世界之时,反而体现了生命的大美——死即生,死即美,死亡赋予了写作者以天眼,看到了横亘于幽明两界间的种种可能的图像。
文学终究让死亡显影,而死亡,反过来,让文学愈发深刻。若读懂了黛玉临死时的种种表现,便可深刻地体悟出林妹妹的爱恨情仇,同理,读懂了《漫游者》里的呼唤和嗫嚅,便可知:凡胎陨灭了,肉眼紧闭了,但灵魂的眼睛却睁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