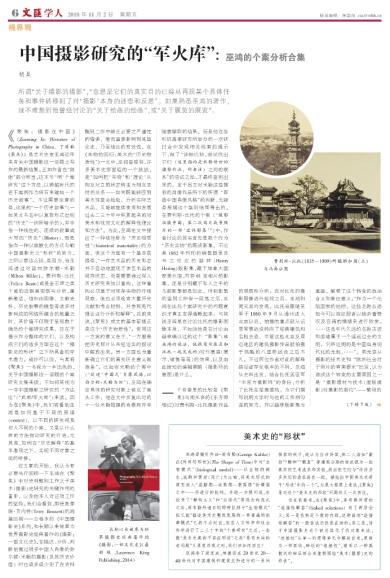巫鸿曾援引乔治·库布勒(George Kubler)在《时间的形状》(The Shape of Time)中对“生物模式”(biological model)——以生物的诞生、成熟和衰老(死亡)为比喻,将美术形式的演变放入“滥觞期—成熟期—衰落期”的模型之中——所进行的批判,并进一步提问说,在经受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等观念的洗礼之后,库布勒所追求的那种区别于“生物模式”但又能“描述美术史整体发展的一种普遍的叙事模式”已然不合时宜,但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了二三十年的“个案研究”之后,一些像“美术史真的不存在形状”之类“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又再度浮现之时,我们该如何回应?
巫鸿举了梁思成、林徽因在20世纪20—40年代对中国建筑和建筑史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的例子,他认为应该将梁、林二人诸如“豪劲”“醇和”“羁直”等建筑分期的尝试视为一些真实的艺术追求和实验,然后把它们与“许许多多类似的追求连在一起,描绘出中国美术史若干‘形状’中的一个”。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聚焦》是对这个“美术史的形状”问题的又一次回应。
但在我看来,在《聚焦》中,库布勒所谓的“连接性解答”(linked solutions)有了两层含义:其一是在特定个案的内部,这种面向“连接性解答”的一般尝试仍然是在场的;其二是,对于中国摄影史这个被总体化了的对象来说,“连接性”从单一的逻辑单元中解放出来,更新为一种新的、辩证的“连接性”,继而以一种离散式的辩证综合来重新图绘“美术(摄影)史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