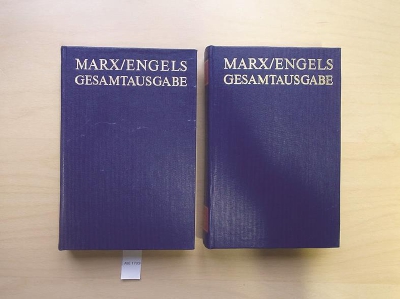杨洪源
文本学研究所呈现的马克思思想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动态过程。正是其思想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特别是他思想成型过程中留待解决的疑惑和困境,使得马克思能够与19世纪以后的时代发生“接触”,从而超越那些仍属于且只处于19世纪的思想家而历久弥新。只要资本还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就值得为人们所研究。
时间推序到21世纪的今天,距离马克思诞辰已过去整整200年。适逢其时,以马克思主义为符码的思想研究与社会运动,继续推进到了新的高潮。随着这位公认的“千年第一思想家”又一次成为理论工作者乃至普通民众的谈资,由形形色色的解释所构成的“马克思热”迅速产生。这一由特殊纪念意义引发的热潮,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强烈的仪式色彩;由之,形式远远大于内容的现象层出不穷。对于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的思想而言,形式诚然可以作为必要的手段,但手段绝不能完全取代目的。如果言说马克思只流于形式,其真实的思想就会被遮蔽起来。加之不同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异,一个具有宽广思想视野、浓厚人文情怀、深邃历史意识和丰富哲学内涵的“活”的大思想家形象,就很可能会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直至完全消失,只留下一个供人顶礼膜拜的空洞的神像。上述可能的后果无疑将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悲哀。
回溯马克思步入人类历史舞台以来的不同时期,关于马克思思想阐释的 “新热”迅速且不留痕迹地取代 “旧热”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折射出来的不仅是只注重形式而忽视作为本质的思想本身,而且是长期困扰着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困境,即如何才能真正地“走进”或“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世界,他之于现时代究竟价值几何。
面对上述境况和问题,对马克思的思想作溯本清源式的系统梳理,不失为一种良策;对作为马克思思想载体的文本进行细致且深入的研究,则是这一方法论的基点。对于大的思想家来说,其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的丰富性与深邃性,绝非体现为一些表述清晰的论断及其有机“排列组合”,而是深藏于这些论断的探索、辨析、论证与检验等过程中。因此,只有深入马克思文本内部进行的条分缕析和细致解读,方可堪称对马克思思想的内部反思;否则,所谓方法论云云只能沦为一种外在的表面形式。20世纪 60年代,勃兴于德国理论界和思想界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即为一个很好的佐证。无独有偶,21世纪初中国学界关于 “回到马克思”与 “马克思的当代性”之争,也充分说明了上述结论的合理性。
不可否认,文本解读或经典阅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是,文本解读的方法有很多种。受其所处时代及其重大问题的影响,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将文本解读理解为回答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绞尽脑汁去觅得文本的思想细节与其“身后”的现实问题之间的耦合性。这样做的后果,轻则使表征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经典阅读失去意义,重则使人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给改造现实世界的社会运动带来灾难性的损害。对此,通过文本“走进”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则应当首先竭力避免。事实上,马克思生前就坚决反对将其思想热捧为理解人类全部历史,以及解决特定民族发展道路的“万能钥匙”。他强调,只有对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加以深入的研究,然后再进行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锁钥。
究其实,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说明从而避免它们,只是对马克思思想世界的一种“被动式”理解,尚且属于应用研究的范围,与思想研究相去甚远。何况我们根本无法预料、也不可能穷尽一切随时出现的问题。更为复杂的是,马克思一生的著述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根据目前国际上较为权威的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结合主要的书志学研究成果作不完全统计,共有独著 1600多部(篇),合著 300多部(篇)。其中,完全成型的书稿较少,绝大部分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的著作的准备稿、过程稿和补充稿,多以笔记、札记、提纲的形式出现。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原始手稿尚未面世。这意味着通过文本解读来建构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是一件极其繁琐、复杂、困难的长期性工作。而个人精力的有限性决定了研究者根本不可能在其有生之年将马克思的全部著述研究通透,进而梳理出他的思想演进的完整脉络。
任何复杂的研究工作都是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的。纵使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有再多的空白需要填补,也得以文本个案研究为起点。鉴于此,我们退而求其次,选择那些体现马克思思想的特质、内涵与发展趋势的经典文本,作为研究的重点对象,从而有助于客观呈现马克思思想世界的大概面貌。这些文本大致都经过了马克思的深思熟虑,耗费了他大量的心血,因而篇幅较大且大部分内容已经成型,甚至在他生前已经付梓。诸如:《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伊壁鸠鲁笔记》《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等。尽管我们过去对这些著作有了详实的研究,取得了诸多颇具影响力的成果,但由于在资料搜集、解读方式和观点概括等方面存在误差而具备重释的必要性。
当然,文本研究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的指导。从马克思著作的普遍特性即未成型性来看,以还原写作的原始情境、文献状况及主要细节为内容的文献学研究,似乎是“走进”马克思思想世界的正确方式。但是,只完成版本考证和文本解读,对于文本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散见于其中的“主线”即他的思想及其逻辑,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进而完整且清晰地呈现出来。偏执于版本的枝节甄别与内容的表述变化,从而忽视对思想的总体观照与把握,是典型的舍本逐末,与过去忽略具体语境而断章取义的做法如出一辙。版本研究和文本解读的成果必须运用于思想研究中才具有合理的价值。只有实现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统一的文本学研究,才是“解锁”马克思的复杂思想世界的正确“代码”。文本学研究之于文献学研究,犹如中国古人所讲的“大学”与“小学”之辩;前者必然以后者为基础,而两者的不同则在于 “道”与“术”之别。
那么,文本学研究究竟能给重释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文本学派”的最新成果来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理清了马克思思想演进的总体历程:(1)马
马克思思想起源与西方传统思想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2)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逻辑线索及其实质揭示;(3)马克思与其先驱之间思想的传承与决裂过程辨析;(4)劳动异化、交往异化及其扬弃之径的探究;(5)异质思想的剥离对于马克思新思想的锻造意义;(6)在批判中建构“新哲学”框架思路及意旨的厘清;(7)“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意义辨析;(8)“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9)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10)“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进;(11)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与逻辑的审视;(12)资本主义史前史的求解及其意义。很明显,上述内容在直观上业已呈现出一个与以往不同的马克思形象。
在描述与总结大贤的思想历程方面,中国古人曾有过这样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说法:“十而有五志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年龄是虚岁,而非周岁。)有趣的是,文本学研究所勾勒的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竟然与此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出生于1818年5月5日的马克思,很早就开始了写作,尽管他直到读大学时 (1835年10月)才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和保存自己的作品。1833年,15周岁的马克思在其阅读的大量人文经典的“塑造”下,写下了题为《人生》的诗歌,初次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时光带走的一切,/永远都不会返回。”“生就是死,/生就是不断死亡的过程。”从这些诗句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在“志于学”时便领悟到“向死而生”这一哲学终极命题的真谛。基于时间长河来观照有限的生命,再来思考人生的追求与意义,就会发现大多数人所苦苦追求的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他们恰恰遗忘了欣赏人生短暂路途中的那些绚丽多彩的“风景”。正如少年马克思所说:“人贪婪追求的目标,/其实十分渺小;/人生内容局限与此,/那便是空虚的游戏。”这些出自一个少年之手的诗句,对于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与追求个性发展相伴随的、陷入追名逐利“病态”中的芸芸众生来说,无疑是一剂醒世 “良方”。长期以来,接受过正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们,何曾想到马克思会有这样的人生观。殊不知,这正是一个活生生的大思想家思想起源的真实写照!
正是有了这样的人生观,少年马克思将整个人类的幸福和个人自身的完美视作选择职业的指针。在他看来,人的本性不是个人追求与人类幸福的相互排斥,不是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相互冲突,而是它们的有机融合。“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这种追求促使马克思“回到”表征着“真”“善”“美”的古希腊的城邦时代,通过对“原子论”哲学的深入探讨,表达了对打破既有体系束缚的自由理性的向往。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此时理解的自由理性,绝非外在于人的世界的抽象原则;相反,它正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彰显,是普罗米修斯精神的化身:绝不对“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抱有幻想,“宁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为宙斯效忠”。
对自由理性的美好向往不可避免要遭受现实 “无情”的“打磨”与“摧残”。甫一接触社会现实中的物质利益问题,如新闻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摩泽尔河沿岸农民生活状况、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马克思便发觉现实中充斥各种反理性的事物,认识到不是自由理性而是物质利益支配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行为,并最终导致普遍自由的沦丧。正所谓“不破不立”,为解决物质利益问题这一 “苦恼的疑问”,马克思转变了自由理性主义者的立场,开始“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阐明 (批判的哲学)”。在上述过程中,他不仅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哲学(“副本批判”),揭示其“思辨结构的秘密”,从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以真正进入市民社会内部;而且还反思了其思想起源期的“引路人”,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全面清算自己旧的哲学信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最终能够 “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彻底扬弃了自我意识如何观照现实世界这一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形成了自己的“新哲学”和新的历史观。1847年,而立之年的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一书,通过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方式,对其“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第一次科学的概述,从而标志他的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作为马克思重要批判对象和思想对手的蒲鲁东,在其具有理论基石意义的代表作《什么是所有权》中标榜的也是“不破不立”(Destruam et oedificabo)。
1848—1849年爆发的欧洲革命,使得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理论研究工作,投身于波谲云诡的革命斗争中。遵循其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入手论证经济危机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普遍贫困导致政治革命,再通过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的变化来分析政治革命的走向,最后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政治革命的前景。但事与愿违,政治革命的具体时机与最终走向都偏离了马克思的预期。1850年,随着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到来,工人运动开始步入低谷。此时,马克思正面临着唯物史观之于现实的解释力的巨大困惑。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从而能够真正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够达到的界限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机。1857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使正值不惑之年的马克思看到了欧洲革命的新希望,促使他决定立即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纲,并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约50个印张的内容,以便在革命的“洪水期到来之前”把一些问题搞清楚。
尔后,经历了 “十年磨一剑”,品尝到各种人生的艰辛,甚至牺牲掉个人的健康、家庭和幸福,马克思于知天·命之年即1867年正式出版了 《资本论》德文第一卷。他通过剖析资本及资本逻辑,揭露出维多利亚时代新兴资本家的世界的实质,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力求以改变现实世界的方式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围绕这一主线,马克思探讨诸多与其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的重大思想议题,如资本的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社会有机体及其结构,资本的本性,资本拜物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与结局等,从而达到其思想的又一座高峰。
伴随着《资本论》的影响力的日趋广泛,逐渐步入耳顺之年的马克思也对外界的各种批判的反应,不再像早年那样作出猛烈的“批判的批判”。例如,杜林曾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上撰文攻击《资本论》,说它是对黑格尔式诡辩的拙劣模仿。对此,马克思只是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通过强调他的学说的新唯物主义性质以作简单回应,并没有写出类似于恩格斯《反杜林论》这样篇幅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受包括新兴金融资本主义和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问题等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中断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修订工作,转向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基于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来找寻引导世界发展走向的其他因素,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此的思想深度和思想广度,不正说明了马克思正朝着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方向迈进吗?
总之,文本学研究所呈现的马克思思想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动态过程。正是其思想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特别是他思想成型过程中留待解决的疑惑和困境,使得马克思能够与19世纪以后的时代发生“接触”,从而超越那些仍属于且只处于19世纪的思想家而历久弥新。只要资本还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就值得为人们所研究。他的著作根本没有被掩埋在柏林墙的瓦砾中,而是正在显示出它们真正的意义,并且持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力。大思想家及其经典著作之所以影响恒远,其原因就在于此。(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