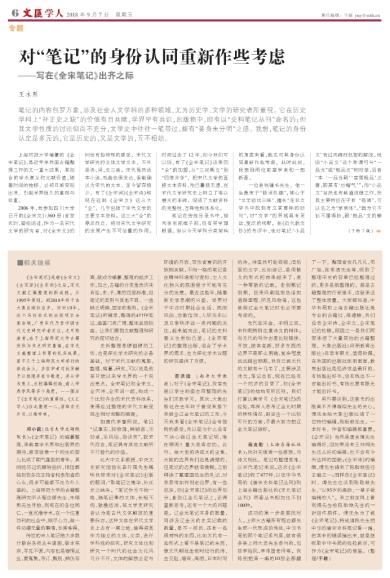《全宋笔记》是继《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之后,宋代文献汇编整理的新成就。从1995年策划,到2018年终于由大象出版社出齐,历时19年。这个马拉松式的出版项目全面告竣,广受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学者关注。尤可称道者,在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作为宋史研究重镇,在宋代文献整理上积累的扎实成果。前不久于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多位学者对此贡献予以梳理并表示敬意,并从学术意义、点校编辑经验、前人学养学风等多个角度,一一圈点了《全宋笔记》的重要性。《文汇学人》在此整理一二,留取吉光片羽,以飨学林。
邓小南(北京大学文研院院长):《全宋笔记》的编纂整理,承载着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期待,感觉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长成了朝气蓬勃的青年。其间经历过的辗转曲折,相信都铭刻在各位主持者和参加者的心头,很多可能都不足为外人道的。上海师范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从程应鏐先生、朱瑞熙先生开始,到现在的各位同仁,一直沉潜学术,在一个注重功利的社会中,倾尽心力,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非常难得。
传世的宋人笔记绝大多数分散在各类丛书里面,版本芜杂,寻觅不便,内容也是错愕丛生,要蒐集、考订、甄别、辨伪存真,就成为编纂、整理的起步工作。加之,古籍的分类虽然历来有经、史、子、集的四部标准,但笔记的类别与其他不同,一直缺乏明确、固定的准则。《全宋笔记》所辑录、整理的477种笔记,涵盖门类广博,整体品质较高,让我们看到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密切结合。
史料整理是硬碰硬的工作,也是深化学术研究的必备基础。对于宋代文献的蒐集、整理、编纂、研究,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一个突出亮点。全宋笔记和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一起,构成一个比较齐全的宋代资料体系,使得经过整理的宋代文献呈现出相对完整的概貌。
如唐代李肇所说,笔记“记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就宋代而言,笔记具有其他文献所不可替代的价值。
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嘱咐我带来对《全宋笔记》出版的题词:“取笔记之精华,补正史之缺失。”笔记作为不拘一格、随笔记事的文体,长短不拘,散漫活泼,被文学史研究者认为是古代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这种文体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将其作为独立的文体、文类,进行学科性的探究。研究文体也和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风习分不开,文体的解放必定与环境的开放、写作者意识的开放相关联。不拘一格的笔记是在精神环境相对宽松、士人文化勃兴的氛围里才可能有充分的发展。最近这些年,随着新史学思潮的兴盛,学界对于中古时期社会生活、民间风俗、宗教信仰、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秩序这一类问题的关注,越来越突出,笔记的史料意义也更加凸显。《全宋笔记》的整理出版,迎合了学术界的需求,也为深化学术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查洪德 (南开大学教授):对于《全宋笔记》,我首先是以学生的姿态向整理的先生们求教学习。其次,大象出版社在去年终于督促我接下来做全辽金元笔记的工作,今天我来看《全宋笔记》会有独特的感受。我以前为什么没有下决心做辽金元笔记呢,难在哪呢?量大是肯定的。此外,做大型的诗或文的全集,大致的边界我们还是清楚的,但笔记的边界就很模糊。之前拜读了戴建国先生的札记,对我思考如何划定边界,有一些启发。但《全宋笔记》的边界划分,拿到辽金元笔记上,还得重新思考。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辽金元笔记本身的数量,同涉及辽金元的史实记载的数量,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东西。比如元代有一些形式上看不是笔记的东西,像元代朝廷出使时纪行的诗,去交趾、缅甸、高丽、日本时写的诗。诗虽然可能很短,但后面的文字,比如游记,是用散文的形式把诗串起来了,是一种零散的记载,走到哪记到哪,回来向朝廷报告诸如道路里程、所见风物等。这些是做辽金元笔记时也必须要考虑的。
元代在宋金、宋明之间,宋和明特别注重诗文的辩体;而元代的写作态度比较随便、开放,破体变新,好多东西的边界不是那么明确,复杂程度远远超出预期。我自己做元代的文献有十几年了,主要涉及诗文,笔记也有,现在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目录了,和《全宋笔记》的结构有所区别。我们打算认真学习 《全宋笔记》的经验,再深入思考辽金元时期的特殊情况,制定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尽最大努力把辽金元笔记做好。
高克勤 (上海古籍社社长):我补充强调一些感想。与诗文相比,笔记的整理更难,以宋代笔记来说,这次《全宋笔记》收了477种,以往中华书局的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宋元笔记丛刊》两套丛书相加也不到100种。
成功的第一步是要找对人。上师大古籍所有程应鏐先生那一代形成的传统,中华书局的那个笔记系列里,就有很多是上师大老先生参与的,包括李裕民、李伟国老师等。我特别把第一编的10册全都翻了一下,整理者有孔凡礼、邓广铭、张希清先生等,吸取了整理宋史的前辈已经整理过的,更多是新整理的。都是古籍整理的行家里手,这就保证了整体质量。大家都知道,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专业的古籍社,很遗憾,我们没有全宋诗、全宋文、全宋笔记的校辑。原因之一是我们两家承担了大量其他的古籍整理。大象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非常有眼光,值得钦佩。在我国的出版社体制里面,教育出版社是经济效益最好的,有钱能出好书,但有钱也不一定能出好书,有钱也要有眼光才能出好书。
另外要谈到,这套书的出版离不开傅璇琮先生的关心。傅先生给大象出版社请了一位特约编辑,陈贻焮先生。一本好书,作者和编辑都重要。《全宋词》当然是唐圭璋先生编得好,但如果没有王仲闻先生这么好的编辑,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全宋诗》的编缉,傅先生请来了陈贻焮担任主编之一;同样在《全宋笔记》时,傅先生也谈到陈贻焮先生,“以93岁的高龄,一辈子做编辑的人”。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傅先生给陈贻焮先生的一封信件原件,傅先生为了做《全宋笔记》,特地请陈先生把中华的唐宋史料笔记看一遍,把其中的错误摘出来,就是想吸取中华书局的经验教训,可作为《全宋笔记》的借鉴。
(整理/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