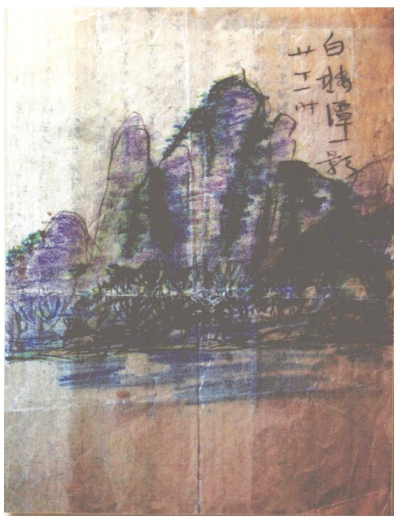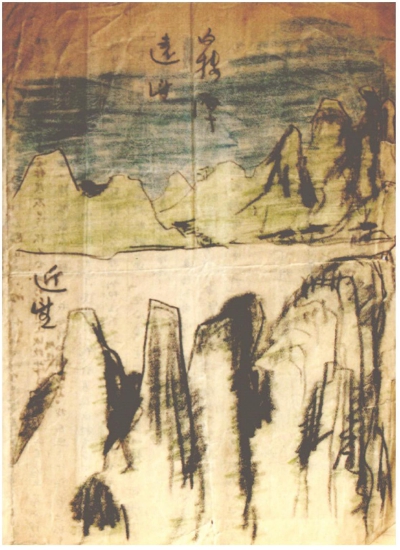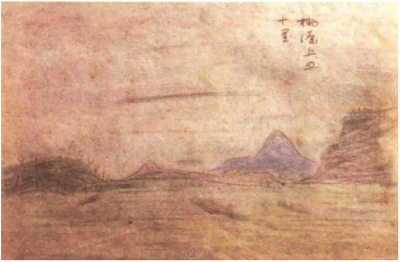张新颖
《沈从文的前半生》是学者张新颖的新作,当年,他以《沈从文的后半生》获得鲁迅文学奖。谈及为何先写 “后半生”再写 “前半生”?张新颖说,写完沈从文的后半生后,回头再看他的前半生,见出了新的气象,因此抑制不住写作的冲动。确实,了解沈从文,得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人生经历着眼,才能深刻理解他内心精神世界发生的变化。在我们今天刊发的这篇 《作为大学教师的沈从文》中,可以看到时代环境的变化如何逐步影响他的心境。——编者
1930年 在武汉大学任助教:
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合乎他心性的亮点
一九三〇年四月末,杨振声赴国立青岛大学出任校长,之前拖延的筹备工作就此走上正轨。六月,杨振声到上海延揽教师,北京 《现代评论》时期结识的这位朋友向沈从文发出了邀请,并于八月寄来了路费。沈从文从中国公学辞职后,一个去处,即是青岛,但学校能否按期开学,还是个问题,如果 “开不成学,就不知道走什么路好了!”所以同时也另做打算,给朋友写信打听: “若青岛十月无法开课,我或来北平住,不知有可以生活事业不?”
胡适、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去武汉大学,从陈西滢六月给胡适的信来看,这事颇为不易:“从文事我早已提过几次,他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我极希望我们能聘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系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都连语体文都不看的”。最终,陈西滢的努力还是促成了武大聘请沈从文;给的职称只是助教,由这一点来看,这个聘请当然有些勉强。
沈从文从上海动身,九月十六日到达武昌。而他未能前去报到的青岛大学,九月二十一日即告正式成立并开学。
九月十八日,沈从文致信胡适:
初到此地印象特坏……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样子,各处有脏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 (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则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饭馆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
我到了三天,吃饭地方还不能解决,但时昭潭先生到得更久,还无办法,大教授因为一间最小的宿舍,还吵过架!……
……
到此借了些钱到手,舍妹方面已寄了点钱去,学费可缴一半,其余或等一会都可缴齐。……
我住处还得我每天用呼吸温暖它,使霉气去掉……
我在此一个礼拜三小时,教在中公一类的课……
沈从文教的课,还是新文学和习作。武汉大学印行了他以新诗发展为内容的讲义 《新文学研究》,铅印线装,前列 “现代中国诗集目录”,然后编选分类引例为参考材料,后半部分是六篇文章,分别论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的诗。十一月初,他把这个讲义寄了一份给王际真:“那个讲义若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点。”
同时来任教的还有孙大雨,来之前即与沈从文在上海相识,来后两人常常一起上小饭馆。孙大雨比沈从文少三岁,但留美归来,待遇自是不同。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里说:“大雨是大教授,我低两级,是助教。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别人要我教书,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生的要求。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 “大雨在此做他的诗,还快乐,因为他会快乐。我是不会快乐,所以永远是阴暗的、灰色的。”
沈从文教课的压力倒是不大,隔一天上一次课,空余的时间很多,做些什么事呢?大致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到图书馆看书, “看得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他还请教胡适,“我想得先生指示一下,关于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王国维的是看过的。”
陈西滢 (通伯)是文学院院长,“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作,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 自己也写写字,随手画画,这个长久的习惯,心情很坏的中公时期也没有废掉,现在仍旧。
还有一件说了好多年要做的事,终于做了起来。十一月五日致王际真信: “我这几日来从大雨、时昭潭学英文,会读 ‘一个桌灯’或‘我不是大头’这类话了”——挺难想象的。
再就是为一些年轻的文学朋友,看稿、寄稿、卖稿, “我近来就成天为这些人转寄稿件,我的穷,在这事上也有点关系。……我有时一切也厌倦了,但有时,是又因为想到有许多人在另一个地方,也是那么寂寞,那么孤单,且因为要使这些人活得有气概一点,来为他们工作一下的。”
更可注意的是,即使心情处在糟糕的状态,眼见的当时现实烂污恐怖,沈从文还是能够发现日常生活中隐蔽的合乎他心性的亮点,看到他想看到的情景,并把它们 “挑选”出来,为之 “发生兴味”: “这几天我到街上去,常常停顿在那些脏极了的小铜匠铺前面,看黑脸铜匠打水壶,细细的膊子,圆圆的眼珠,望到那些人,总使我忧愁。还有每天可见到的小剃头匠,担了小担子满街走,敲打小锣,常常按了一个大而圆的头颅,用刀沙沙的刮头。太阳照到这些人的背上,一定非常温暖,我就爱这些活人,欢喜他们,理解他们。”——这样的眼光、兴味、情感,将越来越清晰地在他的文学中凸显出来。
十二月底,学期一结束,沈从文就离开待了三个半月的武汉大学,回到上海过寒假,与孙大雨暂住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
1931年 任职青岛大学:
挚友徐志摩的死亡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
一九三一年八月,沈从文应聘任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九月七日开学,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九妹岳萌相随到青岛读书。
一年前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校长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当时闻一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不久。文学院设中文系、外文系、教育学系,梁实秋为外文系主任,兼学校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中还有专攻戏剧的赵太侔,一年后任教务长。沈从文来的这个学年,文学院同时新聘的讲师有赵少侯、游国恩、杨筠如、梁启勋、费鉴照。
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时明显不同,沈从文的状态要放松、从容得多。同事间宽和、亲切,常在一起聚饮,沈从文来之前,戏称的“酒中八仙”——杨、闻、梁、赵之外,还有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再加上一位女作家方令孺——就已经豪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沈从文既不喝酒,也不划拳,但这样的人事氛围至少不让他感到压抑;况且,有几位“新文学”的朋友——一九三二年春,闻一多又请来二十一岁的诗人陈梦家担任助教——在大学里同处,也不必再为自己是个写小说的而低人一头。
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环境的特殊敏感,青岛的海天水云,在沈从文的感受中,就不仅仅是宜人的风景,更是滋养生命的阔大空间。自从离开湘西,他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自然的“教育”了。似乎是,青岛让他又恢复了与自然的联系:多年后他在《水云》里回忆说,“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时间长,次数多,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灵魂里。我虽寂寞却并不悲伤。因为从默会遐想中,体会到生命中所孕育的智慧和力量。心脏跳跃节奏中,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和调子柔软而充满青春狂想的音乐。”
十一月十三日,沈从文写信给徐志摩,说方令孺离开青岛大学到北平,希望能援手为她介绍工作;又说,“你怎么告陈梦家去选我那些诗?我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如今一来,倒有点难为情。一看到《诗选》我十分害羞。”——两个月前,新月书店出版了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选收了沈从文七首诗:《颂》《对话》《我喜欢你》《悔》《无题》《梦》《薄暮》。特别说,“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原文中如此。编者注)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徐志摩出生于一八九七年一月,离五十岁大寿还早着呢。最后说到自己的写作,“近来我心里很灵活,手下很笨”,预备按照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
十九日致王际真,说“近日来在研究一种无用东西,就是中国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们中国的观念与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发展,从有史以至于今,关于他的源流、变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仪式,作一种系统的研究。”这项研究,应该与创作苗公苗婆的故事密切相关。
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喝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徐志摩在济南遇难。沈从文连忙搭夜行火车,第二天一早赶到济南齐鲁大学见朱经农校长,接着匆匆赶到津浦车站,与北平来的梁思成、张奚若、张慰慈会合,找到料理丧事的陈先生,又遇南京来的郭有守,大家一同往城里偏街停柩的一个小庙,瞻看遗容。徐志摩十九日乘邮政航班从南京飞往北平,到济南附近遇大雾,飞机触撞开山焚毁。躺在小庙一角棺木中的徐志摩,已经换上一套寿衣,瓜皮小帽,绸袍马褂,“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格外突兀,让人很难接受。下午张嘉铸和徐志摩的长子从上海赶到,晚上棺柩抬上火车南行。当夜十点沈从文坐上回青岛的火车。
二十三日早晨,沈从文一到青岛即写信给王际真,“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二十四日,写信给胡适,谈纪念和追悼的事。
十二月十二日,又致信胡适:“若事情还赶得及,我想告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音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于送徽音看。八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音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他,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徐志摩不满三十五岁而意外死亡,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件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的事,“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而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写《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叙述赶赴济南料理后事的经过;一九八一年,写《友情》,从访美期间拜访阔别五十余年的王际真说起,历历在目地重述当年往吊遇难遗骸的不堪情形。其实,在当时悼亡的沉痛里,沈从文默默写了两首诗,《死了一个坦白的人》和《他》,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
一九三一这个年份,几乎是在用“死亡”来“教育”这个即将走向而立之年的人。新年的第一天得知消息,父亲在家乡病逝,张采真在武昌被斩首示众;接下来,早年行伍间的朋友满振先在桃源被自动步枪打死;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似乎这些还不够,又加上徐志摩,“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经历了一连串沉重的变故,这个人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沉溺于恶劣的心绪而不可自拔,不再那么自我感伤,不再那么自己可怜自己;脱掉了青年时期紧张而脆弱的浮表外皮,本性坚强沉实的质地愈发清晰,人显得开阔健朗起来。
1938年至1946年 西南联大岁月:
巴金眼中老友的变化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时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的杨振声向朱自清提议聘请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教师,朱自清时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兼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他日记里记此事,感觉“甚困难”;朱自清找罗常陪商谈,十二日日记:“访莘田,商谈以从文为助教。”十六日,“从文同意任联大师院讲师之职务。”二十七日,联大常务委员会第一一一次会议通过决议,“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月薪贰百捌拾元,自下学年起聘。”
联大九月份开学,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学年沈从文开设的课程有:在文学院中文系,与吴晓铃合上“国文一(读本、作文)”;独自上“各体文习作(一)”,文学和语言专业二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文学专业三年级选修课。在师范学院国文系,上“各体文习作(一)”,二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文学专业三年级选修课等。
为募集清寒学生特别救济金,沈从文写了二十张小条幅参加“义卖书展”,这是他第一次把“习字”和“经济”发生联系。
十月十三日,日军二十七架战机轰炸昆明,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办公处及教员宿舍多处震坏,沈从文和卞之琳合住的小楼宿舍屋顶和墙面局部洞穿,邻室半坍。空袭后师院借昆华工校校舍上课,沈从文搬到文林街二十号楼上。转年一月二十九日,新住处周围再遭空袭,他的一间宿舍幸免被毁,只在房顶“大开天窗,落下一堆泥土。”在这里,他一直住到一九四六年初。
五月二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作题为《短篇小说》的演讲。前面提到的《小说作者和读者》,是上一年八月三日他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的演讲。
七月,巴金第二次到昆明探望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萧珊,上一次是去年七月,两次都住了将近三个月,过了整个暑假。巴金和萧珊乘火车去呈贡看望沈从文一家,沈龙朱还记得,父亲和巴老伯带他出去玩,正躺在草地上看天空,敌机就从面前飞向昆明,继而听到轰炸声;没过多久,飞机折返,在他们头顶不远的地方,忽然有一架扔下炸弹。“父亲赶紧叫我们翻起来,‘趴下趴下’,他用自己的身体捂在我们身上,趴下。瞬间,轰隆一声,我们没看见,但是炸弹爆炸了。”近处一个插秧的农妇被炸死了。
巴金看得见老友的一些变化,感受得到他处境中的某些方面:
一是,“生活水平降低了,吃的、用的东西都在涨价,他不叫苦,脸上始终露出温和的微笑。我还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饭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有西红柿,还有鸡蛋,我们就满足了。”
二,与过去两人在一起时很不一样,“我们不再辩论了,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们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血淋淋的尸体。过去一段时期他常常责备我:‘你总说你有信仰,你也得让别人感觉到你的信仰在哪里。’现在连我也感觉得到他的信仰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或者眼里的闪光,我觉得心里更踏实。”
三,老友遭受误解,一方面,“开明书店愿意重印他的全部小说,他陆续将修订稿寄去。可是一部分底稿在中途遗失,他叹息地告诉我,丢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写社会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更不了解我了。’”另一方面,“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一点寂寞,偶尔也发发牢骚,但主要还是对那种越来越重视金钱、轻视知识的社会风气。”
八月十四日,联大遭受敌机轰炸,新校舍内学生宿舍四栋,北区常委会办公室、训导处、总务处、图书馆藏书室及两处教室,南区生物实验室,昆中北院师院教职员宿舍,昆中南院女生宿舍均被炸。沈岳萌在图书馆遭遇轰炸时,热心帮助别人抢救东西,等到警报解除,回到自己住处,发现房间已被小偷洗劫,值钱之物席卷一空。大轰炸和遭盗窃,沈岳萌深受刺激,精神趋于失常。
秋天,张兆和转到龙街的育侨中学教英文。沈从文在呈贡时也去上过几堂义务课,结识了一批年轻的华侨朋友。他在联大,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学年的课程有:文学院中文系,与周定一合开“国文壹 G(读本)”,一年级必修课;独自上“各体文习作(一)”,文学和语言专业二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创作实习”,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在师范学院,上“各体文习作(一)”,师范教育系二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师范教育系三、四年级选修课等。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各校复员计划启动,沈从文被北京大学聘为国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