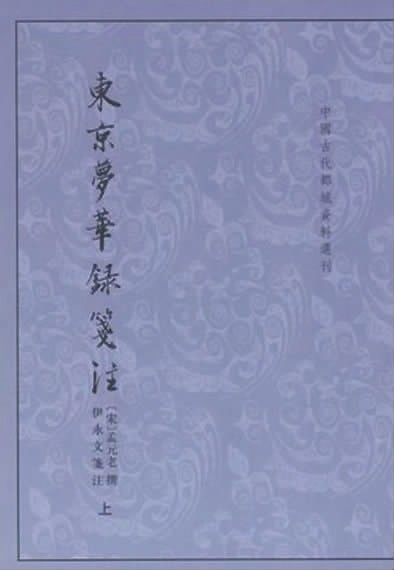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在农耕时代,过年是一场长长的期待,每做一天的准备,过年的欢喜也就累积一点,先民在种种仪式里投入了生活的热情和渴望。先民们也是风雅的,他们把农闲季节的时光打发得充满活泼声色,把“年”过成了一种隽永的艺术。
一一编者
农耕时代,迎新春是一场漫长的期待
《红楼梦》 里,贾府过年是很隆重的,刚进腊月,王夫人就指点王熙凤筹备起来。寻常百姓家没那么浮夸,但也要忙活整一个星期,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意思是正式地进入“新年时间”。在年节文化特别发达的宋朝,朝廷官员们从腊月二十三这天开始放年假。民间有“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意思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百姓家在二十四、水上人家在二十五举行祭灶仪式,正式地迎接过年。从腊月二十三到除夕的这段时间,称为“迎春日”。有童谣唱: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买爆竹;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贴倒有;三十日,阖家欢乐吃饺子。过年是一场长长的期待,每做一天的准备,过年的欢喜也就累积一点,先民在种种仪式里投入了生活的热情和渴望。
关于祭灶,《帝京岁时纪胜》 里说得详细:“二十三日,扫除炉灶,以净泥涂饰,谓之挂袍。”意思是家家户户要清洗灶具,灶头用新泥抹过,涂上白灰,厨房里也打扫干净。“送灶王爷上天”的风俗按民间喜闻乐见的说法,是不愿他到老天爷那儿说人间的坏话。其实,在科技并不发达的旧时,祭灶根本是出于卫生的考虑。紧接着祭灶的就是扫房子,民间叫“扫尘日”,大扫除从腊月二十四持续到年三十,干净清爽地迎来新一年,屋子和内心都是敞亮的。传说尧舜时代已有“扫年”的习俗,《礼记》 有载:“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先民的扫年活动既是为了卫生,同时有“驱鬼”的朴素愿望,这“鬼”主要是指藏在角落里致病的鬼,以及自身体内的病鬼。农耕时代,好身体是生活的本钱。冬春之交,既是农闲时节,又逢万物复苏,此时大扫除,不仅制造年节的热烈气氛,更对健康有利。到宋代,扫年之风已很普遍,《梦粱录》 里写:“十二月尽,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阁,去尘秽,净庭户,以祈新岁之安。”
既要忙活家务,也不能耽误买买买,无论什么年代,置办年货总是很欢喜。看 《东京梦华录》 里,汴京腊月的市场多热闹:“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道符及回头鹿马、天行帖子,或卖干茄瓜、马牙菜、饺牙饧之类,以备除夕应用。”到了清代,更有“年市”这个词,《清嘉录》记载了苏州的年市:“市肆置南北杂货,备居民岁晚人事之需,俗称‘六十日头店’。熟食铺、豚蹄鸡鸭,较常货买有加……鲜鱼果蔬诸品不绝。锻磨磨刀杀鸡诸色之人,亦应时而出,喧于城市。”这段声色俱全的描绘,有铿锵的市井声,年市里最热闹的,当属杀鸡宰猪。农耕文化的背景下,物质是有限的,“酒肉”不是日常的饮食,普通人家只在年节放开了吃鸡吃肉。再者,新年里忌讳动刀剪,于是家家户户赶集囤起“年肉”。
按着老法,初一到初五不仅不能动刀,还不能动火,所以有年谣唱:“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打年糕、蒸馒头,这是备吃食。贴花花就是贴窗花、桃符和门神的统称了。有俗语云:“正月十五贴门神,迟了半个月”,意思是除夕前务必把门神和桃符贴妥了。早在南北朝时,祭门神就是大事,有一套庄重的仪式,《荆楚岁时记》 描述,“望日祭门,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祭了门神,要挂个桃木做的符,因为桃树被认为是仙木,可以制鬼,如 《太平御览》 里总结:“桃者,五木之精也,压服邪气者。今作桃人梗著门以压邪。”
逐渐,门神取代了“桃人”。门神的身份一直在变,唐朝时最富盛名的门神是捉鬼的钟馗。宋代靖康年间以前,中原人民不太介意门神的身份,画上大汉模样威武就行。宋元之后,秦叔宝、尉迟恭、赵云、岳飞、孙膑等名将陆续加入了门神的行伍。老百姓觉得,门神为人时的身份越显赫,越能镇鬼驱邪。有的人家贴门神时还附上对联:昔为唐朝将,今作镇门神。
做完了全部的准备工作,翘首期待的年三十到了,所谓“除夕”,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在这天,祭祖是头等大事。《诗经·小雅·楚茨》记录了一次祭祖的全过程,诗里有一句:“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意思是,我们把酒食来献祭,请祖先安坐享受,求你们赐福后人。这是一项虔诚严肃的活动,总是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率领族人在祠堂或家庙里缅怀祖先的功德,在《红楼梦》 里,曹雪芹描写贾府的年事,浓墨重彩的一笔,便是贾母率子弟在祠堂祭祖。
忙完祭祖,这年节真正进入了玩乐的时间。吃和玩都较平常放肆些,尤其是放爆竹这桩新年特权。这种风俗的源起,是因为先民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认为坏事是鬼神带来的,燃放爆竹则能驱鬼。参照 《神异经》 的描述,“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余,性不畏人,名曰山臊,犯之令人寒热。尝以竹著火中,爆扑而出,臊皆惊惮。”《荆楚岁时记》 也说:“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可见,“爆竹”最先是个动词短语,指“火烧竹子”,后来变成了名词,就像 《通俗编俳优》 里总结:“古时爆竹,以真竹著火爆之,唐人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曰爆竹。”虽则唐代诗人来鹄有诗:“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但新年燃爆竹这习俗,是在宋朝盛行起来。《东京梦华录》 记载,当时开封街头,有专门生产爆竹的作坊,当时火药已经被发明,爆竹从竹筒演变成纸糊的筒里裹着火药,还有用麻绳把单响的爆竹连成串子,即是最早的“鞭炮”。
至于燃爆竹的时机,是除夕夜还是初一凌晨? 古人是不介意的,反正除夕要守岁到天明。通宵不睡,却不尽是为了玩乐狂欢。守岁是一种寄托了心愿的仪式,如孟浩然在 《田家元旦》 里写的,“田家占气候,共说此丰年。”庄稼人守岁通宵,是要从子时到黎明不断到院子里观看天象———如果东方天色先发白,新一年宜种棉花和小麦;天色发黄,种玉米和小米;天色发红,种高粱;天色发黑,种黑豆。这些说法如今看来全无科学依据,但在靠天吃饭的时代,这些风俗和经验之谈反映着先民盼望丰收的朴素愿望。
“年”这一字,始于土地的收成,延续于对更多收成的美好期待。
过年,是风雅的
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中,“远游”不多见。古人认为,过年是家族团聚的时刻,不作兴浪游在外。年假是那么长,农闲季节的时光又特别的闲散,这假期要怎样过得充满活泼声色呢? 在这个问题上,古人们是很风雅的,他们把“年”过成了一种隽永的艺术。
比如,新年穿新衣,新衣需得是青衣的,以此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后汉书·礼仪志》 里记载:“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春旛,以示兆民。”那时,人们相信春季是万物复苏生长的季节,草木葱茏,天地之间大片苍翠,这个时节对应的颜色是青绿色。皇室和贵族很隆重地把穿青色的袍服当作正经仪式,是为表示自己与“天意”的联系。同时,春季对应的方位是“东”,所以皇帝要声势浩大地领着文武百官在都城的东门外迎春。
过年饮酒不稀罕,但如果这酒像 《楚辞》 里形容的:“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就散出了别样的芬芳。蕙肴兰藉,桂酒椒浆,有酒时必有花。来看晋人董勋的描述:“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贡樽。”这是用花椒泡酒,还会放些冬日可得的花朵。比如 《四月民令》里提到“梅花酒”,“元日服之却老。”春节喝酒,喝其美味,也取吉祥的愿景,在饮酒的醺醺然中,对抗衰老,抵挡时间无情的流逝。董勋还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当一家人和和美美坐在一起喝酒时,要让小孩子先喝,因为他们人生正在展开,年长一岁是可喜可贺的。而越是年长的成员越排在后面,毕竟一年年地老去了,时间对生命不停息的碾压,实在不是值得庆贺的事。《荆楚岁时记》 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自那时起,古人确立了这套新年的饮酒礼仪,到了唐代,白居易在 《三年除夜》 里写道,“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很有画面感了。
冬春交替的日子,是一年里农事消停的时候,所以,群体的娱乐活动也就热络些。在诸如灯会、庙会和游春的社交场合,青年男女们都是爱打扮的,姑娘们通常会画上一种“梅花妆”。这个妆容的来历,和南北朝的一则宫廷轶闻有关。据传,某年农历正月初七 (俗称“人日”),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卧在含章殿的檐下小憩,有一阵微风把几朵梅花吹落到她的额头上,经汗水渍染,公主前额留下了花痕。皇后见了,十分喜欢,此后,爱美的寿阳公主时常摘几片梅花贴在自己前额,宫女们跟着仿效起来,这种“梅花妆”很快从宫廷传到民间,受到了女孩子们的喜爱。到唐朝时,姑娘们的妆容越来越复杂,发展成往脸上贴金箔花钿,有“斜红、面靥”,相当于现在的腮红和修容,“万金红、大红春、内家圆”则是名目繁多的唇妆。唯独“梅花妆”仍被当作特别的春节假日妆容。宋代的《太平御览》 里写,“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自后有梅花妆。”张岱的 《夜航船》 里也记了一笔:“刘宋寿阳公主,人日卧含章殿檐下,梅花点额上,愈媚。因仿之,而贴梅花钿。”
除了化妆,还要剪彩绸,做燕子头饰。最早见于 《荆楚岁时记》:“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燕子被认为是代表春天的鸟,彩燕迎春,就是想要像它们一样轻巧地迎接新春呀。
到了宋代,不仅姑娘们戴头饰,男人们也戴起花来。和“簪花”“赐花”有关的文字常见于唐人宋人的笔记。《景龙文馆记》 提到,“正月八日立春,内出采花赐近臣。”元月里天气尚冷,鲜花不多,这一习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贵族的特权。《东京梦华录》 说:“自郎官御史以上皆赐春旛胜,戴归私第。”《闻见近录》 则说:“绍圣二年上元,幸集禧观,出宫花赐从驾臣僚各数十枝,时人荣之。”可见君王赐花于臣子,是一种级别很高的恩典。《水浒传》 里有一回,元宵将至,柴进和燕青在酒楼上,看到楼下“往来锦衣花帽之人”,当两人被告知,“翠叶金花”是徽宗钦赐、戴宫花者能自由出入宫廷,他们是相当羡慕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男人簪花是身份的标识。
饮酒穿戴种种,终归是诉诸于物质层面的。相比之下,“新春御风”则把风雅的意蕴烘托到极致,近似一个行为艺术作品了。参看陆机在 《要览》 里的描写:“列子御风,常以立春归于八荒,是风至,草木皆生。”御风者,便是君子驾驭着风,乘风而行,这构成了一幅写意抒情的画面,也是一种非常文艺的行为: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春天正在来到,人也如同草木一般,要“生发”,要打开感官体验春日。
新春新春,最动人的,还是春天的气息呀。
书影自上而下:
《帝京岁时纪胜》
《荆楚岁时记》
《东京梦华录》
左图为清福贵 《岁朝图轴》
右图为唐张萱 《游春图》
题图为清郎世宁 《乾隆岁朝行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