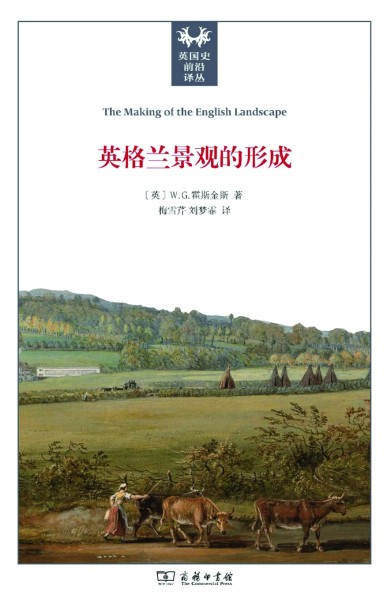■梅雪芹
终于,跟随霍斯金斯先生的步伐,在纸面上和想象中到英伦大地游历了一番。这一番游历,也即是一次古今穿越,上迄公元5世纪中叶英格兰先民到这里定居之前的“远古时期”,下至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在现代城市中生活的“今日时刻”。在此期间,我们越过高地低丘,蹚过河湖海面,走过大街小巷,进过乡村客栈,听过野兽嚎叫,赏过鸟语花香,因而收获了异常丰富的知识,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那引人入胜的,那启发思考的,那感时伤怀的,点点滴滴,莫不让人欣喜。
在这部《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中,霍斯金斯不仅用细腻的文字刻画了多彩多姿的景观,而且用大量的图像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景观,图文并茂,引人入胜。这可能是景观史著作的一大特色吧,而霍斯金斯对这一特色的把握可谓得心应手。
从文字来看,书中的景观描述可说是细致入微,让我们引述一段略加品味。譬如,关于诺曼征服时期英格兰的景观,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尽管到诺曼征服时大多数英格兰村落已经有模有样,当然其他许多村落业已消失,但是广大的地区仍保持自然状态,期待着人声唱响。许多地区的原始森林,像肯特郡和萨塞克斯郡的安德里德的大片森林,或米德兰的大森林,仍然“在悄悄地抖掉落叶,萌发新芽,可是却无人驻足观赏,也无人为此感时伤怀”。其他地方,譬如在萨塞克斯郡和肯特郡海岸边,在英格兰东部神秘的沼泽地带,在萨默塞特平原,在低地各处的小块田地,许多这样的景观中只见大群水鸟栖息。内陆地区,特别是遥远的西部和北部,还保留了上百万英亩的石漠荒原,唯有野兽的嚎叫声经常回荡,老鹰和渡鸦自由自在地盘旋。什罗普郡的厄恩伍德村和德文郡的雅恩斯康比村就是对从前某座“老鹰森林”和“老鹰河谷”的纪念。与此同时,位于约克郡西区远方高处利顿谷地上方的石灰岩悬崖,为这些高贵的鸟儿提供了筑巢之处,没过多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安克利夫村就得名于这座“老鹰悬崖”。在那里面一些遥远而僻静的处所,除了风声雨声,只有绝对的寂静笼罩上空。
这一段文字,几乎涉及11 世纪初诺曼征服时英格兰各地的景观风貌,其类别包括人类社会的村落、田地,自然世界的森林、海岸、沼泽、平原、荒原、河谷、悬崖,还有经常嚎叫的野兽,自由盘旋的鸟儿。这些丰富的文化与自然元素,一同绘出了特定历史时期英格兰景观的细密画像,后世之人可以透过它们而感知彼时彼地景观之外貌和内涵,尤其是那自然的辽阔与寂静,和着风声雨声野兽声,力透纸背,令人难以忘怀。而这样的文字刻画所体现的不同时期英格兰景观的特色和细节,在书中处处可见。
与文字相辉映的是从达特莫尔的中央荒原、罗马大道、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农庄、中世纪的渔村和桥梁、伊丽莎白时代的庄园大宅,到议会圈地产生的田地模式、特尔福德所建的运河桥梁、1848年柴郡的克鲁火车站、林肯郡的波士顿教堂与集市、经过规划的城镇等英格兰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景观画面。作者甚至还用了一幅图来告诉人们,他心目中“地道的英格兰景观”是什么模样。如果说,图像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常用的信息载体,是对客观对象的一种相似性的、生动性的描述或写真,那么,霍斯金斯在运用这一载体来承载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时,也力求它们对英格兰景观的描述达到生动、逼真的效果,这是令人钦佩的。
作为一部致力于探讨英格兰景观形成、发展的历史著作,与一般的关于英格兰景观风貌以及整体上研究英格兰地形地貌的作品不同,作者自己对它的定位是:如实地“呈现英格兰景观,竭尽所能解释它到底是如何呈现出当前的模样,那些细节到底是如何添加的,是什么时候添加的”,因此,它关注一切改变自然景观的东西,并极力回溯其背后的历史,力求为英格兰景观框架增添鲜活的内容和细节。这样一来,该书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启发我们如何更全面、更深入地思考和探讨与英格兰景观形成相关的诸多历史问题。其中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分析,令人印象深刻。这里仅举一例,即霍斯金斯有关敞田制及其塑造的乡野景观随议会圈地运动开展而消失的论述。对此,他特别以北安普顿郡北部的海帕斯顿荒野为例作了具体剖析。他引述了两位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的英格兰诗人的相关描述,谈及局外人和局内人的不同认识和表现:
克雷布在《村庄》一诗中也描述了那片荒地,用语有些粗野。毫无疑问,他们都描绘了那里的村民们的艰苦生活,以及一如克雷布所见的其周遭环境的贫穷;但克雷布不像克莱尔,他不是农民,他以局外人的身份理解这里的景象,因而将它描绘得丑陋不堪且令人不适。克莱尔对于那片荒地的看法更真实一些,因为那是作为局内人的农民的见解。他在这里土生土长,是它的一部分。尽管他从没有故意去美化它,或假装它不过是“大自然的荒野”,但克莱尔在其中还是看到了克雷布全然忽视或敌视的东西,并感受到了它们在变化和“改良”到来时出现的损失。
这两位诗人,一位是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1754-1832),一位是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1793-1864)。前者出生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海滨城镇奥尔德堡,是外科医生、牧师兼诗人,对于北安普顿郡的乡村海珀斯顿来说,他显然是外乡人或霍斯金斯所说的“局外人”。后者在海珀斯顿出生、成长,与那片由荒野和树林构成的小世界融为一体,“是它的一部分”,并成为了“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劳工诗人”。因为与那个地方的关系和身份的不同,所以他们对同一片乡野及其命运转变的态度和感受就判然有别。
霍斯金斯的这种分析和评述启发我们,在研究和讨论某时某地的历史变化、分析变化的影响和得失时,除了需要了解它的外表如何、它的经济系统如何运作、外在的观察者如何描述它之外,更需要倾听身处变化之中的人们的心声,深入了解他们真切的得与失以及面对变化时茫然无措的感受。这种内外兼顾的方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显然是需要倍加重视和普遍运用的。
更需要提及的是,在上述内外兼顾的分析和评述中,自然渗透着作为历史学家的霍斯金斯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这一点,在对近现代时期英格兰景观变化的历史叙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也是作者本人确定的历史学家在地质学家构建的景观框架基础上所应添加的鲜活内容之一。对此,作者在最后一章“现代英格兰的景观”的叙述中多有体现。其中他说到,自19世纪末年,“尤其是1914年以来,英格兰景观上的每一点变化要么使它变丑了,要么破坏了它的意义,要么两者兼具。”这样的说法,不免让人觉得有几分感时伤怀,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然而,它毕竟是作为生于英格兰、长于英格兰的英国史家,一位像19世纪的克莱尔那样的“局内人”,在见证自己所生活的20世纪英格兰的诸多变化时产生的真切感受。因此,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在谈论这个世纪英国取得的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时,一定不要忘了听一听作为局内人的这位英国同行的凄美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