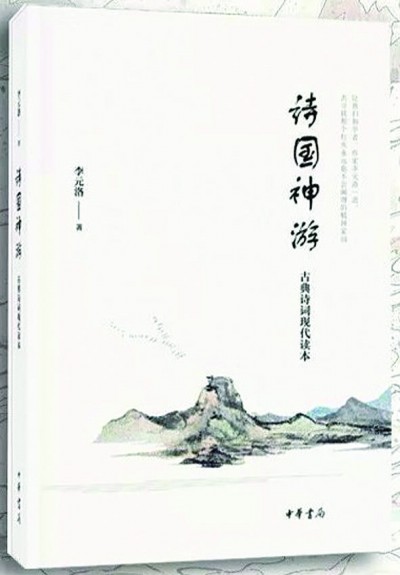朱文杰
古典诗歌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当现代白话与古典诗歌相碰撞时,若要成为这些诗人及其文字的知音有着诸多障碍。李元洛先生在《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自序中指出,“作为欣赏者,必须具备审美欣赏的兴趣、愿望、能力”,兴趣与愿望,作为古典诗词的爱好者,我们自然有之,然能力或因生活环境、个人阅历的不同而略有缺失。李先生正是通过散文化的语言,以自身的阅读欣赏体验带领读者在这些古典诗歌的杰作中寻幽访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将抽象的诗论化为形象的文字,让喜好古典诗歌的我们在诗歌的精神国度里遨游,去寻找那个灯火永远也不会阑珊的精神家园。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回答当然是:不可。诗歌是诗人内心的写照,古典诗歌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每一位诗人、每一位创作者赤诚的心灵。李先生开篇所讲便是诗人的襟抱,“一等襟抱一等诗”,语出清代诗人沈德潜《说诗晬语》, 意思是有第一等的胸怀抱负,第一等的学问知识,才会写出真正第一等的好诗。李先生以屈原《橘颂》为例,为我们讲述如何将“橘”之形象与屈子之品格相结合,进而扩展到古代咏物诗的赏析,娓娓道来,深入浅出。
李元洛先生是湖南长沙人,听他讲家乡的人物更是觉得亲切。在《生命品格与高远襟怀——刘禹锡〈 秋词二首〉》一文中,他由“常德诗墙”这一现代与古典的桥梁,带我们走进中唐诗人刘禹锡在朗州(今湖南常德)的那段岁月。而立之年由政治中心长安被贬荒凉小郡,家道艰难,妻子病逝。在这样的境遇下,他竟然写出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诗句,不禁让我们崇敬其“顽强的生命品格、豁达豪放的内在襟怀”。
如果说诗人的“襟抱”是神,那么诗歌的构思、技巧便是骨。骨不易见,却是支撑的关键。诗歌是凝练的,构思、技巧往往化于无形之中,李先生便带我们擘肌分理,探究诗句的本质技巧。“天机云锦用在我”语出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这首诗本就是陆游谈论自己的学诗之感;“鸳鸯绣了从教看”出自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亦是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诗论作品,这两篇从构思、方法两方面集中探讨了“诗艺”的问题。由于中国诗论的语言过于抽象,李先生便另辟蹊径,在文中更多地引入西方诗学理论来进行阐释,与此同时对应穿插中国古典诗论,使得现代读者在理解上少了一些隔膜。
李先生采用以诗带讲的模式,每一小节以一首具体诗作为讲解对象,又集中抽取“诗眼”为读者展开论述诗歌的创作方法,语言优美,让读者得以跟随其文字在中西方诗艺中徜徉。细读下来,所获颇多,原来“儿童相见不相识”是用“典型瞬间”这一片段来加深读者印象,突出回乡的整个历程与心境,而“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所以戛然而止,是用“期待视野”来刺激读者的想象,丰富诗的形象;原来“绿水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巧妙地运用了动静对照的艺术手段,着一“合”字,“静态的树有了跃动的姿态和生命”,着一“斜”字,“静态的青山有了生动的气韵”;原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可以用“意象脱节”来解读,只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六个名词便将商山早行之时间、地点、所听所见之景描绘出来,“语不接而意接”,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李先生在后记中谈及创作原则时说:“纵向适当联系‘五四’以来包括当代新诗与旧体诗词的创作,横向适当联系西方的文论与诗论,力求汇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增强时代感与当代性。”他正是这样付诸实践的。
语言是诗歌的血肉,是“襟抱”的载体,是构思及技巧的依托。“清词丽句必为邻”语出杜甫《戏为六绝句》, 这一篇是从诗歌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语言文字来进行阐释。或是炼字炼句的精雕细琢、同字叠字的回环往复,或是常字新用、平字见奇的别出心裁,或是用典的意味隽永,或是以口语入诗的化俗为雅……让我们对诗歌语言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风格是诗歌之“气”,是诗人之“气”,是神、骨、肉的融合与升华。李先生最后一篇讲解的便是风格。风格是一首诗或一类诗的意境,“百般红紫斗芳菲”,其多样性正如春天百花齐放,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通过前面对诗歌的襟抱、构思、技巧、语言等各个方面的探究,读者大体已经具备了“寻幽访胜”的能力,对古典诗歌的鉴赏想象力也有所增强。
“高明的欣赏绝不只是作品内涵的再现与复制,而是作品的延续、扩展、升华。欣赏者在获得审美初感之后,静观默察的审美理智使他展开‘视通万里’的空间联想和‘思接千载’的时间联想,对诗的意境进行审美再创造,得到属于自己的更多的审美发现与审美喜悦”,这是李先生在自序中对读者的进一步期待。人类之情感具有共通性,诗歌虽是古典诗人的生命体验,我们也可通过共情的方式去理解他们,从而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进一步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