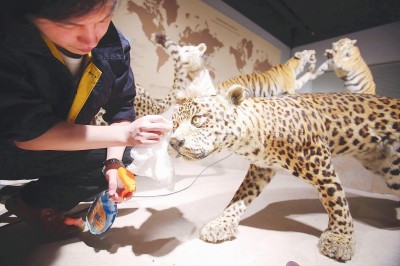本报记者 李静
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建成三年来,以大量珍贵动植物标本和新颖的展示方式、生动有趣的教育活动,提升了市民和青少年的科学素养,丰富了市民生活,年吸引观众约200万人次,是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和公众社会文化交流平台。但很少有人知道,馆里还蕴藏着另一座“宝藏”———一支朝气蓬勃的自然史科研团队,使得沉寂多年的博物馆自然史科研重新启航。
这支团队正对标世界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在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征程中,为提升城市文化科技软实力助一把力,让市民“足不出沪”就能领略更深刻、更丰富的“演化乐章”“生命画卷”和“文明史诗”。
鸟儿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市政协委员、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自然史研究中心主任周保春回答说:“是一个更好看的世界!”不仅因为它们翱翔蓝天,天然拥有“天空视角”,还在于人眼看到的是红绿蓝三原色光构成的世界,而鸟儿的眼睛,在三原色光之外还能感知到紫外线,所以颜色更丰富、世界更好看。这是周保春正在开展的鸟类视觉进化研究项目得出的初步结论。
此外,他和同事们还在研究长三角地区的土壤昆虫、外来鱼类入侵历史和特征、北冰洋化石表征的古代气候变化等自然科学项目,以期寻找到地球及地球生物、环境演化的规律和痕迹,预测未来。
周保春给记者做“科普”:自然史研究通过观察、研究、描述、记载等方法归纳自然现象及规律,和实验科学一样,是认识自然的重要方法;最妙的是,它可以重复研究下去,不研究的时候做展示、科普。在欧美多个国家,自然博物馆因为有充足完备的收藏空间、藏品保存技术和管理系统,一直是自然史科研重镇。
“自然博物馆研究最基础的动植物系统分类学,是生态学、遗传学等研究的参照系和基础。”周保春说,今天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和调整都能从自然博物馆的收藏和自然史研究中寻得答案,这是打开生物和环境进化的“密钥”———从全球变暖过程,预测未来气候变化,需要不同时期收藏的标本来复原物种地理分布变迁史;为遏制外来物种入侵,可以用不同时期的标本计算外来物种入侵的速度及其遗传变化速度;评估环境污染给生物的伤害,为保育生物学提供依据,可用化学分析和同位素分析方法还原自博馆馆藏的生物食性变化等特征。
长期以来,人们惯常认为自然博物馆是展陈和科普单位,忽略了其科研功能。周保春认为,自然博物馆的科研、收藏和科普三大功能中,科研功能至关重要,是收藏展示和科普功能的根本,“科研做到家了,才能讲出更有趣的自然史故事。”他说。
尽管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展陈广受好评,但周保春坦言,与世界公认的一流自然博物馆相比,我们的科研和收藏能力还需长期积累、不断深耕。“美国史密森协会下属的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有1.45亿件藏品,英国大英自然博物馆有8000万件,日本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有440万件,而我们目前只有几十万件,对照世界最高标准,我们的科研、收藏规模和水平亟待提升。”他还建议,充分利用自博馆的专业储存、科研和展陈优势,以租借等方式从民间收购藏品,创新藏品收集方式等。
“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在藏品和科研人数等方面都还有一定差距,但这支科研队伍很有希望。”周保春坚定地说,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好契机,自然史科研绝不能落下,更要探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