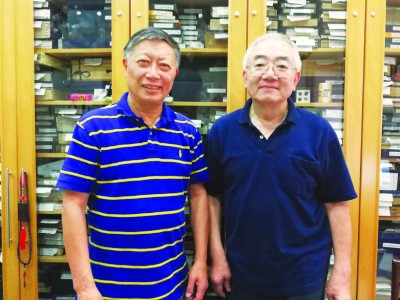沈津 董天舒
林章松先生能集印谱收藏之大成,一是独到的眼光,二是对印谱的执念,三是雄厚的财力做支撑,当然也少不了平日里的节衣缩食、宽打窄用。然而追根究底,成就林先生今日收藏印谱之规模的,是他兀兀穷年、矻矻终日的勤谨和笃学。
一
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某所中学的国文课上,有一个对艺术方面很感兴趣又勤奋刻苦的学生,深得他的国文老师喜爱。由于这位学生在书法、绘画、篆刻以及篆刻收藏方面都有些涉猎,所以老师告诉他,爱好广泛固然好,可是广博便不能专精,希望他能够在这些爱好里找到自己最为热爱的一项仔细钻研。这位学生经过认真思考以后,决定要专攻篆刻。这一学,就是50余年。
1978年的某天,香港某渔业老板觉得给他做商标设计的年轻人是个可塑之才,便跟他打赌:三个月的期限,年轻人给老板推销海产。若年轻人入了此行,他就给老板打工;反之,老板付给年轻人一年的薪水。年轻人对这个赌约信心十足,他太清楚自己对渔业的一无所知;老板则对年轻人的做事能力慧眼识珠,知道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三个月过去,年轻人竟然如老板所料,生意做成了一单又一单,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诧,原来自己竟有这方面的天赋。于是,年轻人跟着老板做起了海产生意。这一卖,又是40余年。
这个习篆的学生,如今收集的印谱之多、之稀有,远远超过国内的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在国内的印谱收藏界首屈一指;这个卖鱼的青年后来创设了自己的渔业公司,规模庞大。其实,卖鱼的青年和习篆的学生是同一个人,他就是林章松先生。教他国文的老师就是对林先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曾荣光先生。林先生将海产和收藏印谱这两件事结合在了一起,以海产供养收藏,以生计满足爱好。每逢国内各种重要的古籍拍卖会,林先生总是要花大把的时间查核拍卖图录中的印谱,特别看重的是自己所未藏的印谱或别人不入眼的残谱、剪贴谱。林先生能集印谱收藏之大成,一是独到的眼光,二是对印谱的执念,三是雄厚的财力做支撑,当然也少不了平日里的节衣缩食、宽打窄用。然而追根究底,成就林先生今日收藏印谱之规模的,是他兀兀穷年、矻矻终日的勤谨和笃学。也许,从商人的角度看,他是在经商之暇收集印谱,但从收藏的角度来说,他的重心却在于研究印谱,从商倒成了他搜集印谱的
途径,而非目的。
二
中国人对印谱的研究,大约是从宋代宣和年间开始的。印谱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极强的艺术性和收藏鉴赏的价值。今人研究印谱,大可于方寸之中,领略篆文的字体以及印文的排列疏密、参差、错综的美感;也可驰目于毫厘之外,去感受古人的思虑通审,以及各种流派的不同篆刻风范。从明清到当代,有人嗜好收集,有人喜欢临摹古代印章,有人讲究考证学术,目的不同,出发点也就不尽相同。篆刻家和收藏家将留存下来的印章荟萃成谱,而流传至今,除了继承艺术传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供考证印人的流派。
中学毕业后,林先生常到曾荣光老师府上学习篆刻书法。最初,他每周按时到老师家听篆刻理论课,或者观察老师如何操刀。老师为他布置作业,下节课即修改点评。林先生的篆刻初学黄士陵,体会其中的气韵和美感,后又临摹赵之谦、吴让之等人,从上世纪60年代到如今,林先生所刻的印章居然达千余方之多。
曾先生带他走访了不少香港地区有名的收藏家,以此开拓眼界,打破停滞不前的关口。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老师带他到某位收藏家家中看一部很著名的印谱,但去了三次,都无功而返,因为那位收藏家对他们只说印谱找不到了,而林先生却无意间瞥见那部印谱就在桌下。经过这件事情,曾先生悟出了一个道理,即印谱不宜私藏,应为大众所用。曾先生也因此将毕生所集藏印谱全部转赠于他,希望他日后继续收集流落坊间的印谱,成立一间印谱资料室,让所有的篆刻爱好者都能共享资源,也给相关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一处治学之地,免得他们为找资料而四处碰壁。这是曾先生对他的期望。林先生后来所做的种种亦是恩师之嘱,就连他所写文章的署名也作“天舒”,那是他将老师的笔名“楚天舒”去掉前面一个“楚”字。当然,林先生一脉相承的除老师的笔名外,还有老师的勤奋与风骨。
随着林先生的收藏数量递增,种类也越来越丰富,这使他对印谱的版本有了新的认识。一些重要的印谱,在流传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版本,每种版本所收印章又有数量上的不同。印谱的版本复杂,如西泠八家的印谱就有很多版本,需仔细判断、区別。像汪启淑辑的《飞鸿堂印谱》,内分不同年份的钤印,或有汪启淑像及释文,或无汪启淑像及释文;有的卷数一样,但所收印却多寡不同。而无释文的要早于有释文的。再如《求是斋印稿》四卷,四册,乃道光时黄鵷篆刻并辑,有的本子题“古闽黄鵷朗村氏篆”,蓝框,有手绘黄鵷像,原钤本有印释文。但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又有雕板印为绿框者,黄像也改为雕版,释文亦为摹刻,所以印谱也有版本之别。
序和跋中的文字,对于印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至于艺术篆刻的技巧,提笔奏刀,可反映出印人不同的精神面貌,诸如:苍劲雄放,自成家数者;遒丽流畅,疏逸自然者;挺健平正,不假修饰者;敦厚园秀,英健正雅者多有呈现。历来印人之原印,人们所见甚少,或无可得见,但印谱中多为原印钤拓,后人可以参考对比,也可仿刻学习。
林先生所藏的印谱除了老师的赠与,新增添的部分得自国内,据他估计,存世的印谱约在6000种左右,分散在世界各地,林先生收藏的就有2000余种。至于日本、韩国,也藏有将近2000部之多的印谱。当年香港的集古斋、中华书局,有了新的印谱就会通知他去买,此外,包括上海、天津、广州的古籍书店都和林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
善于思考,是智者的特质之一。林先生前几年就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些印谱有效地为研究者所利用,那就是建成一个数据资料库。他开始将印谱中的信息一字不漏地敲进电脑里,有些信息可以在原书中找到,但大部分的数据是要经过查证和考据的,需要花费一天、数天,甚至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获得确切的信息。林先生设有自己的博客,博客名为“天舒的博客”。博客中每一小段文字,都可能是他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翻了很久,或在网上百般寻觅,然后结合材料写出来的。林先生对印谱的查证特别仔细,为的是避免因误判而引后人入歧途。尤其是对于一些使用同一斋名的作者,做这类的查证更是谨慎。查明资料以后,要把整本印谱一张张地扫描,而后录入谱名、卷数、篆刻者、页数、序、跋、再加上篆刻者的小传。这是一个繁琐且工作量很大的工程,耗时、耗力,所以林先生每天睡眠仅四、五个小时,平时只有在身体极度不舒服的情况下才会休息一会。这项工作,林先生日复一日,居然做了二十年。
印谱真正见于公家藏书目录著录的很少,讲印谱的著作则更少。前人对古铜印章并不重视,认为仅是雕虫小技,故藏书家亦不重视。甚至《四库全书》存目中收录印谱也甚少,仅存明代杭州人来行学刊刻的《宣和集古印史》八卷、明代吴县人徐官撰《古今印史》一卷、明代上海人顾从德撰《印薮》六卷、明代松江人何通撰《印史》五卷、明末胡正言撰《印存初集》二卷、《印存玄览》二卷。私家书目中涉及印谱的著录则更是十不一二。叶铭《金石书目》末附传世印谱,虽然有150多种,然而多半是后人的钤印本,与古铜印谱并列,而且仅著书目,撰写得很简略。
林先生对印谱最为敏感了。他费尽辛苦完成了《松荫轩藏印谱目录》,其中的罕见印谱,他是明察冰鉴、了然于心。家藏的700余种罕见印谱,深印于脑海。他除记谱名外,又对这700种印谱进行校对,曾在一年时间里校对了230多种印谱,写成37万字。四年前,国内某图书馆委托林先生将该馆所藏印谱目录加以校对,因此他将以前所写的《松荫轩藏印谱目录》初稿核对改动,这一工程比重新写还巨大,涉及事项更多也更为广泛,在改动中更发现了以前记录及印人题跋的失误之处。
林先生收藏印谱不是为了保值,而是为了探讨印学发展史,并补充以往研究者的缺漏之处。印谱中的序跋如与某些历史资料进行校对,会发现有些历史记载值得商榷。其次,还可以补充和考证许多名人的表字、别号、生卒年、籍贯、交友、书斋号等等,当然,这些都要细读印谱才能知悉。
传世印谱有数千种,然而林先生却重人之所轻,轻人之所重。当收藏界对不可多得的名谱趋之若鹜,而对小谱、残谱、伪印之谱不甚重视时,他却有自己的见解。比如在拍卖场合拍得一册表面上看还算完整的印谱,然而收到之后才发现没有任何序跋及边款记载,这样的情况于林先生而言亦是多见。他就像一位经验老道的刑侦专家一样,去找寻蛛丝马迹,翻阅有关资料。幸运的话,几天便能查证出答案,当然,他有时费数月之劳,仍是徒劳无功。几十年来,林先生已经配齐了十几部残谱,其中有一部印谱仅存上半部,而下半部,他从广东、上海分了三次才陆续凑齐,使之延津剑合,破镜重圆。
再如林先生收藏的小谱《三近草堂印草》,单看此谱名,鲜有人知,或对这部印谱不屑一顾,但若提起主人名号,便众所周知了。“三近草堂”主人原来是李上达(1885—1949),辽宁人,长居北京,字达之,号五湖,室名为三近草堂。他是金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同门中翘楚,也是湖社、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国书画研究会成员。据说在收藏界中,要看李上达的画轻而易举,但要看李上达的印却很难,知道李上达有印谱存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这是林先生眼光独到之处。
除了残谱、小谱,林先生对伪印也有关注。有人问林先生是否参与某次拍卖,林先生说:此套印谱其实都是伪印为主,但要作为资料保存,就算是伪印,亦希望能保存全套,以便后来学者能看到全貌。林先生虽然也追求完美,却不苛求,残谱也好,伪印也罢,只要是对他人考察取证有用处,他都不遗余力地躬身为之。若收藏印谱只为了保值,大可不必计较这些,但若为了保存先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查证史实,这却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
金石藉人而传,人亦藉金石以名。篆刻始于祖龙,有印即有印人,所以印人自古有之,不过古时印人由于地位低微,被时人称为工匠,因而没留名史册,殊为可惜。为印人事迹作小传者,乃为传古人于不朽之善举。最早为清周亮工之《印人传》三卷,收58人,附见5人。清乾隆间,汪启淑有《续印人传》八卷之作,收罗128人,较周多至一倍有奇。后又有叶铭辑《广印人传》十六卷,收1551人,上自元明,下迄同光,搜辑史传,旁参志乘,以及私家纪述,600年来,专门名家,不问存殁,悉著于录。如今,坊间所见当代辑录印人传之书也有所见,所载印人较之前人所载更为丰富,但存世印人之多,不胜枚举。除了开宗立派的名家以及有代表性的篆刻家外,一般名气稍弱的印人多被人们所遗忘,如:尹祚鼒(及郎)、李相定(寇如)、李僡(吉人)、孙贇(汉南)、倪品之(品芝)等等,很少有人还记得他们的生平。
林先生致力于为清代印人编写小传。若没有林先生的记载,可能许多优秀篆刻家,他们的姓名就将会永远归隐于古籍之中无人问津,稀有印谱所呈现出的众多不同侧面也将杳无可寻。而且林先生不去记载大家熟知的人物,他为之立传的都是鲜为人知以及被人遗忘的人物。那一方方硃红色的印痕,透过色彩古朴的硃泥、质地轻盈的纸张,向林先生传递着各自的命运,而制造它们的印人也因为林先生的著录而名垂青史。
林先生在寻找印人资料的过程中,总是要翻阅多省地方志、《艺文志》、《印人传》、《人物志》以及各类人物资料书,他意识到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寻找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印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如江苏一带印人的小传,可以有《江苏印人传》参考,但对友人所托查寻的某吴中印人,即便是殚精竭虑,也无从查证。且不说明清、民国时期的印人资料难以寻觅,就连有些近现代的印人资料也无从下手。所以林先生决心将自己所掌握的所有印人资料都予以公开,免得前人资料湮灭,后人研究没根可寻,无源可考。
在多种印人小传中,林先
生以两个专题来进行研究:一是“莫愁前路无知己” 系列、二是“谁人曾予评说” 系列。这两个系列是有缘由的,前者源自高适《别董大》,其一为“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写给“高才脱略名与利”的琴师董大,诗中饱含着高适对这样一位身怀绝技却无人赏识的友人惺惺相惜之意。林先生引用此句写名不见经传的印人,与这些不曾谋面的印人进行着精神上的往来,个中深情尽在这详尽扎实的小传里了。而“谁人曾予评说”的上半句是“千秋功罪”,林先生说,他不评说千秋功罪,只是客观评说印谱的成书年份、作者、内容、品相,适当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如今,“莫愁前路无知己”系列已经写竣,序跋不计算在内,共有200篇,印人200位,这200位印人中,部分是有典籍记载、大家较为熟悉的,而大部分印人却失载于各种工具书、参考书,难以找寻其生平资料。所以,能写成生平小传,一是靠谱中的印作,二是靠谱中的序跋,将这些零碎点滴资料,汇录辑成。
对民国篆刻家林洵的查证,就是他编写印人小传的一个典型范例。林先生在广州购得《林洵印稿》四册,当时他并不知林洵其人,只觉得印刻得不错,后来翻查了很多书籍,都查不到林的资料,偶然读到一本小册子,才知道他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篆刻家,存世的印不多,印谱亦只有他自己收藏而已。这部《林洵印稿》,林先生记录了印稿名称、册数、尺寸、板式、印的数量、内容、序跋有无、成书年份、印人资料,并将其图片发在博客上。
再如对《萧儒怀印集》的著录,除了对印谱的基本介绍外,对印人小传部分记载得格外详细。因为萧先生生活在渔梁,他只属于地方性的名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殁后,其生平事迹就被历史慢慢冲刷掉。若不是林先生有集藏之好,世人根本就不会知晓历史上曾有此人存在。
林先生每天整理印谱并将查获的信息详细记录在自己的博客上,供有兴趣的人参考查阅,这其中也有趣闻。林先生在广州集雅斋购买了一册印谱,谱名为《止园印存》,印谱第一页就是一方白文印“鼎奎私印”,林先生将其拿回比对,确定此人为赵鼎奎,并将其记录在博客上。赵的后人看到林先生的博文激动地在下面留言说,上世纪7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曾祖父将所刻印章全部赠予嘉定文物部门,家里一方未留,希望与之联系。林先生在印谱间行针走线,不觉中竟留下这段接续某个印人家族断线的佳话。
三
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是中国人崇尚的美德。林先生帮助他人从不计回报,对他人所求则倾囊相助,这类事例举不胜举。比如遇到友人所求没有旁证的印谱,林先生会抽丝剥茧地解读其所载印拓,凭借蛛丝马迹去考察取证。不少圈内人每到香港必定要拜访林先生,他是有求必应。也有人在先生博客中留言说明所求的印谱,林先生不问来路,尽力相助。这其中,也有林先生曾经帮助过的朋友,事成后反咬一口,林先生却不以为意。他从别人的快乐中感受到欣喜,并不求别人日后的记挂。精明的人笑他傻,也许习惯计较得失的人看到老实敦厚的人总有那么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其实林先生哪是真“愚”,只是大智若愚,不同于精明人的斤斤计较。林先生踏实做事,清白做人,免除了那些无谓的精明和算计,反而常生自在和欢喜。也有希望资助林先生的外国友人,林先生则当即谢绝,他不希望日后因为资金问题,欠下人情债,也为避免自己辛苦收藏的印谱最后沦落他乡。林先生善于筹谋远虑,即便自己节衣缩食,也不向外人伸手,由此阻断了不必要的纷争。
林先生是大爱之人,某次拍卖会中出现了一些林先生所未藏的稀见印谱,他很想得到,但时值印尼海啸和汶川地震,林先生权衡之下,毅然将购买印谱的大笔款项全都捐了。我所知道林先生想的是,这些印谱能得一安身之所,亦是印坛之幸。他收集印谱的目的不在于能否予他所能集藏,而是要唤起大家关注印谱这种小众之物,不要因为此物的“小众”,而让先贤留下之文化遗产湮灭在我们这一代。
收藏印谱的圈子非常小,但人们关心的不仅是林先生收藏的印谱,更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常为他的健康祈祷。一到雨天,气压走低,林先生的身体就异常敏感,血管痉挛、胸闷乏困。但比起身体的病痛,更沉重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前几年,琴瑟鹣鲽、结缡数十载的爱人离去,让林先生难于释怀。宋代诗人蒋捷曾做过一首《虞美人·听雨》,有云:“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然而林先生坚强地挺过来了。很多时候,林先生是在与自己的身体做斗争,且这场拼搏旷日持久。只要身体稍有好转,他便要开始工作,也顾不上双手肿胀、奇痛莫名。为了不让亲人和朋友挂念,他还忍着痛苦照常握筷吃饭,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一天,濡湿的气候,再加上工作的劳累,他在取车时竟然在停车场晕了过去,幸亏抢救及时,才未导致事故。体力的透支、状况的不断反而让林先生更加刻苦,他要赶在思路还清晰的时间里,将所见印谱整理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这项工作是他心头上的结,这个结标志着他对有志于篆刻艺术者以及印谱藏家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曾先生嘱托的回应。
印谱是林先生的毕生收藏至爱,除此之外,他还收集不少古钱币、字画、佛像、砚台以及古铜印。佛像雕塑不仅各个体态不同、神情各异,且不同的材料包括金银铜铁木石等,制造工艺水平之高,都深深吸引了他。林先生收集佛像的原因有四:一是其高堂生前信佛,二是看到老师收藏的精品佛像而喜爱,三是因为对佛教事件的了解而产生浓厚兴趣,四是对佛像造型之美有好感。佛像的造型,美在其静谧、庄严、慈悲、安然,林先生对佛像的情感,并没有朝圣者对佛祖的祈求之心,虽少了几分仰视,但却衬托出纯粹的爱慕与敬畏。林先生喜爱的是佛像所传达出的古人的厚重历史与多元风貌,是佛像所折射出来的前人的精神世界,是佛像所映照出的众生心相。
有意思的是,林先生集藏的第一尊佛像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花了几个月的薪酬才得以拥有的。平时,他也将佛像送给友人,唯独此尊佛像坚持不送,这并不在于价格的高低,而是一种情结所在。他所藏佛像,最早的为魏晋时期的作品,是从香港摩罗街的一位朋友手上用其他藏品换来的。收藏最丰富时,佛像竟有3400尊之多,大大小小,高低不等,放在橱里,像博物馆里的陈列物。后来一位朋友要筹办博物馆,请林先生支持。林先生二话不说,居然送出了一半多,条件是博物馆必须作展览用——供观众参观、鉴赏。林先生送出去的,不光是佛像,还有古钱币,美国某大学艺术史某教授曾到港向林先生讨教钱币学之事,走时,林先生让他从存放古币的袋子里抓一把,抓得的钱币就算纪念品了。客人访后告辞,主人居然以“钱”相奉,以作“盘缠”,这也是第一回听到的饯别趣事。
旧时文人对于文房四宝常有偏爱,而砚尤为历代藏家之好尚。林先生收藏的砚台也有不少,他首次接触砚台是在曾荣光先生家中,后来曾先生归道山后,除汉砖砚送予师弟外,其余的,师母都送予他收藏。第二次接触砚,是“砚巢”王石舟先生在香港大会堂所举办的藏砚展,那时他在曾先生的带领下去参观,这也是他见到名砚最多的一次。而真正将林先生引入砚石这个领域的,是80年代初期香港的一场展销会,他一次性买下数十方砚石。后来举办展销会的公司又请书店代卖,老板任林先生挑选。林先生在货仓中挑选了整整三天,挑出了3000余方砚石收藏。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对于癖好,有的人用来消遣、解闷,于是缓缓做下来,可以得见那种精微的风雅。而林先生穷尽所能一心致力于印谱集藏,其中的苦乐远非常人能想象,深情在这里不再是对美好物件的爱慕,而是再苦再累也甘愿的缕缕情愫、涓滴意念、一腔热血。印象里,林先生颇像一位下盲棋的世外高人,即便闭起眼睛,心中也自有丘壑。屋子里一盒盒各种材质的精致小印、一尊尊传神逼肖的佛像,一沓沓整齐有秩的印谱,上面插着索书签,井然有序。哪种印谱在这个房间所藏何处、有多少种版本、各种版本的先后顺序、版本间有怎样的区别、其优劣和特别之处,林先生都熟谙通解,了然于心。
对于普通藏家而言,收藏印谱也许更为注重的是各家流派、印文布局,而对于该印谱的版本便不会有过深的考究,因为常人很难再有林先生这么大的心力整合如此多的资料。林先生对印谱的感情不是据为己有,而是将其编目、著录、整理、归纳,最后为人所用。满室的印谱,经过林先生的精心编排为人瞩目和珍视,也是人与物的缘分,印谱或许可以随时光常存,而人则世世代代,来来去去,于是,欣于所遇,暂得于己。过手时珍重恭敬,解读一方石印上深浅纹路里蕴藏的故事,继而将这物件一脉相承,便是林先生的简单愿景了。
林先生对印谱的珍重不同于一些藏书楼、图书馆。很多收藏机构对于稀有资源的保护重心是隔绝外界的打扰,比如过去天一阁藏书,并不是谁都能进楼翻看的,那个为求读书而嫁给范家的姑娘,在第二天登楼时,看到了“女不上楼,书不出阁,外姓人不准上楼看书”的禁令,此后日日绣芸草为念,因芸草是给书籍除虫的植物,名为钱绣芸。古人将书与世隔绝,也许隔绝了一点日常的磨损,却辜负了那个守望天一阁一生的女性,也少不了遭遇像薛继渭等大盗窃贼的窥视。至于如今的公家图书馆,读者阅览都有一套规矩,除了证件之外,有的馆规定每次看书,还要收阅书费,扫描、拍照是要前去打点的。林先生则不同,他的收藏重心在于把印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每本印谱不仅自己考察得博贯会通,透彻明了,还乐意别人从中受益。博客上有陌生人求某套印谱资料,留下邮箱后,先生看了,亲自扫描发送给对方,也是常有的事。他不会对收集的印谱视若无睹,束之高阁,如有朋友慕名而来,他都会将各种珍贵印谱从书橱里取出来,一一摆在客人面前,没一点架子。林先生笑着说:“书要亲近人,有人气,虫子也不生。”
愚公曾说:“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有人问林先生,整理这些不经见之印人资料为何,他回答说,为了让他人参考用。又问,看者几人?他答:今天一人,明天可能会更多,存点资料予后人所用,何乐而不为。愚公的山不加增,林先生的收藏与录入却是越积越多,任务越来越繁重,先生的执着也超过了愚公。
林先生之伟大,也在于他的平凡。林先生的书斋名为“松荫轩”,因为先生和太太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松”字。“荫”,当指树荫。《荀子·劝学》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句,引申为遮蔽。林先生的用意是能为这批鲜兹暇日、含辛茹苦而蒐集来的印谱寻一保护之场所。在香港这座繁华又高速运转的城市里,还有林先生这样一位隐于浮世的大德之人,在日复一日地为千百年前那些不知名的印人著书立传、为印谱收藏添砖加瓦,但行所爱,不求他知,但行耕耘,不求闻达,心中藏着造福于后人的愿望,忍着病痛,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蹒跚前行。
(作者沈津为版本目录学家、哈佛学者、美国亚洲艺术院资深院士,董天舒为中山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