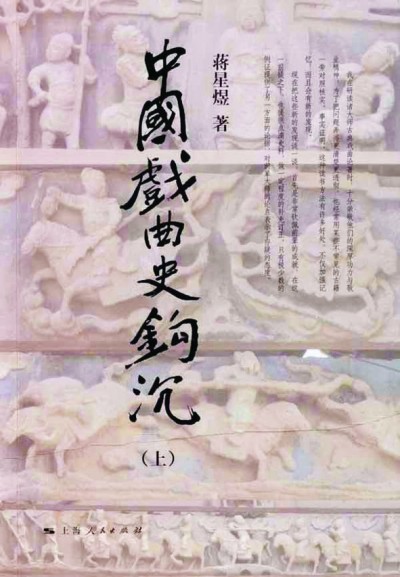陈先行
蒋星煜先生从1979年开始,连绵不断发表《西厢记》版本研究论文,并先后结集多部专著。他对《西厢记》的版本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考证基础之上,又能与戏剧文学和表演艺术紧密联系,故常能思人所未思,发人所未发。
2015年12月20日上午,我尚沉浸在前夜从美东迎回翁万戈先生捐赠《翁同龢日记》手稿的喜悦之中,周巩平兄来电告知,蒋星煜先生已于18日驾鹤仙去,心头顿时如被大石压迫一般,难受得透不过气来。近四十载的忘年交情,一朝山颓木坏,呜呼痛哉。
之前不数日,我还去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探望过他。人虽消瘦了些,精神尚可,也能吃些平素喜欢的食物。不过言谈间突然问起顾廷龙、潘景郑二老之享年,答曰顾九十五,潘九十七,他说“我已九十六”;又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但与侬几十年从未红过面孔,也属难得”。之后久久不语,略显不祥之兆。告别时我说“等美国出差回来再来看侬”,他说了声“保重”,孰料竟成永诀。
星煜丈是1977年秋初到上海图书馆“暂栖生”的,那年他58岁,虽已从“牛棚”解脱出来,但“文革”余波尚存。好在分配工作时“对口”安排在古籍组(即后来的古籍部),前后共待了九月余。对他而言,不啻老鼠跌进米缸里,因祸得福,其于《西厢记》版本研究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记得他刚来上班时,穿着笔挺的深褐色中山装,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皮鞋擦得锃亮,戴一副秀郎架眼镜,眼神深邃,举手投足,一派绅士风度。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我们都叫他“老蒋”,连“先生”两字都不带的。后来熟稔了,不仅习惯,更因该称呼包含着那段特殊的历史而倍觉亲切,我甚至一直到自己变老了都未改口,若叫他“蒋老”,反而觉得扭捏了。而他也从不以之为忤,平素通电话或写信,每自称“老蒋”,实在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
他很快发觉其一本正经的着装与我们勿大协调,于是就勿讲究了,我们旋即与他热络起来。有人暗示,他是个特殊的“临时工”,要与他保持距离。我那时虽也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但很同情他“文革”中的遭遇,何况他是位令人敬佩的大学者,故始终勿接上方的“翎子”。
当时每周工作六天,周六下午是我们年轻人业务学习时间,部门领导曾安排他给我们讲戏曲史常识,至今记忆犹新。地点就在夹层古籍组办公室,在靠南墙一排张元济先生曩昔使用过的书橱前,挂上一块小黑板,他站着演讲,我们围坐聆听。第一讲从“优孟衣冠”故事,一直讲到南戏、北曲、元杂剧、明清传奇。他以浓重溧阳口音的官话,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都被他迷住了。按照现在流行语,成了他的“粉丝”。那是我进古籍组工作的第五个年头,印象中办公室里还从未出现过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可惜后来没有第二讲,原因大家心照不宣。
星煜丈在上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适值启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他与我们一样每天做古籍原书与卡片著录的校核工作。刚开始是按分类校核,他自然选择戏曲类,于是看到许多从未寓目的《西厢记》版本,尤其是颇为稀见的明刻本,如何璧本、徐士范本、汪氏环翠堂本、李廷谟本等,无比享受。不过,他只能匆匆浏览,做一些笔记,尚不能在上班时间从容撰写论文,因为领导表面上没有规定工作量,但每天下班时必须将当日校核的数量填写于墙上表格,对每个工作人员多少形成压力,他当然也不例外。后来因善本书库非分类排架,而是按入藏先后以流水号排架,若分类提书,东抽西取,上下架容易生乱,遂改为按流水号依次取书。这样一来,错架是避免了,但同一种书之不同版本因不能同案校核,版本鉴定著录难免有误,而星煜丈也不可能专事戏曲类包括《西厢记》版本的校核了。为此,我除了遇上相关版本会临时转呈其观览外,有时还会在每周业务学习的半天里,特地以向他请教的理由申请提调他欲看之书,这样多少弥补其未能随心所欲看书的缺憾。
先生离开上图之后,虽然不用每天坐班,可以一门心思做研究了,但有得便有失,看书不方便成了犯难之事。现在说来人们或许不信,上图直至1995年淮海路新馆落成前,没有一套完整的古籍目录可供读者检索,而善本与一小部分普通古籍藏在南京路总馆,大部分普通古籍则藏在长乐路书库,即原来的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读者事先难以了解想看之书藏在哪里,不得不两边奔波;最要命的是,因读者所需之书或由不熟悉业务的出纳人员代查内部目录,提供之书往往不是读者想要看的版本,故白跑一趟的事情经常发生,为此星煜丈叫苦不迭。于是我便成了他的“后勤部长”,专门为他查书借书。起先,我利用内部人员可以应个人业务学习之需外借普通古籍的便利,直接送书上门。后来他怕耽误我的工作,便跑到上图来取,总是等在大门口传达室,我送书下去,颇有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味道。再后来设法为他办理了颁发范围很小的专家外借卡(仅限于普通古籍),他可自己借书回家,但查书及从长乐路书库提书仍需事先为其办理妥当。为尽可能节省其宝贵时间,每次他还书之前,先将其欲借之书准备好,然后一还一借,不使空手而返。但也有我力所不能及者,他要看善本或复制数据,便要看别人脸色了。如1983年7月13日来信有云:“关于善本书影,决定不去向他们交涉了,太费精神。遇见方(行)局长时,我会和他直接商谈的。”直到1985年,我在顾老的提携下担任了古籍组副组长,分管工作除编目外,还包括读者服务,由此星煜丈利用上图资料顺利多了,介绍其友朋前来借阅古籍或代办文献复制也成为常事。
从1979年开始,星煜丈连绵不断发表《西厢记》版本研究论文,并先后结集多部专著,名噪中外。他对《西厢记》的版本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考证基础之上,又能与戏剧文学和表演艺术紧密联系,互为发明。因此,宏观上他能厘清众多明清版本的系统归属,微观上对某些版本的真伪,对已亡佚的版本,甚至对批校、注释、刻版发行者的生平爵里等都作了许多鉴别考订与资料发掘工作,故常能思人所未思,发人所未发。过去研究《西厢记》者很少作版本考订研究,而版本学家们又鲜有精通戏剧史、戏剧理论与《西厢记》者,星煜丈能兼而有之,故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引领《西厢记》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本著名汉学家波多野太郎在为星煜丈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所写的序言中说,他“一来以乾嘉之文献学做基础,二来用戏剧家之文艺科学为武器”,“考究新颖,考核精细”。这是对他的研究方法与成就颇为中肯的评价。
从某种角度说,星煜丈对《西厢记》独树一帜的版本研究,于古籍版本学亦具有创新开拓意义。他希望我能以版本学方面的特长,结合某一文史专题作系统研究,并表示以他的人脉关系,能为我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便利条件。可我才疏学浅,何况我所从事的图书馆古籍整理编目工作任务繁重,不可能有时间进行像他那样的深入研究,只能停留于“书皮之学”而已。我说当年叶景葵、张元济等前辈创办合众图书馆,顾廷龙先生应邀南下担任该馆总干事时,曾向叶、张二老表示,“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也可谓不负其平生”。如今能为侬这样的专家服务,也是我的幸运,同样是很有成就感的。于是他不再提起。
事实上,他对我的编目工
作很是关心,而我在工作中若发现他感兴趣的事情也会告诉他。如1987年我写过《〈宋稗类抄〉作者、版本考辨》一文,认为该书的作者是李宗孔而非潘永因,这是他先前研究《西厢记演剧》连带考证李宗孔时未及注意者。又如2003年我应邀赴美撰写《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发现臧懋循删订汤显祖所撰四种传奇的书名应为“玉茗新词四种”,柏克莱藏本尚保留着万历四十六年臧氏雕虫馆刻本的书名叶。之所以称作“新词”,是臧氏强调由于通过自己的改编,方使汤氏《还魂记》等四种案头之曲变为场上之曲。今人不知有此名称,各家书目著录为“玉茗堂四种传奇”者,或据失却书名叶之后印本,或为后来翻刻者的自题书名,不能确切反映臧氏改编面貌。星煜丈于此亦首次听说,便勉励道:“版本目录确实重要,侬能将古籍目录编成这样,也勿容易。”此外,我编撰过的几种书,印象中他都写过介绍文章,而事先我皆一无所知,之后看到殊为感动,一直将这份长者爱护后学之深情厚意视作工作动力。
他曾想和某出版社编辑合作编纂一部《西厢记》的版画集,这是他全面研究《西厢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未悉何因中辍。由于有些图片是我协助采集,他便提出以我的名义编纂。我知道他是为了帮我,至少多一项成果有利于职称评定。可这是他的专门,我岂能染指。我对他说,将来有可能的话,就以上图所藏稀见明刻本《西厢记》版画结集出版,规模虽小,但在可控范围,容易成功。机会终于来了,1999年,上图欲选馆藏精品制作高档礼品书,我便申报了明刻本《西厢记》版画的选题,以上海图书馆编纂的名义,请星煜丈撰写鉴赏文字,线装出版。领导马上同意,并纳入馆属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当年出版计划。星煜丈十分高兴,将此书定名为“西厢俪影集”;书名请龚学平先生题署,我担任责任编辑。该书一函两册,就当时的印制水平,堪称精良,图文双美,大受欢迎,印数无多,转瞬即成稀罕之物。
2012年,我们又有过一次合作,上图要影印乾隆御览之本《江流记》《进瓜记》,出版前言之撰写非星煜丈莫属。5月初我上门相请,他一口答应。保姆悄悄对我说,老人家近来健康欠佳,已有较长日子闭门谢客,电话也不让接听。我闻之惶恐不安,谓可俟康复后再动笔,他连说勿要紧,勿要紧。不数日接到他来稿,曰“文章乃急就,外来应酬,已一概谢绝,精力不济也。阁下嘱托,自当全力以赴,但极其不理想。想你们修正。实在不行,另请高明亦可”。我立即将其手稿整理成电脑文本,并稍作改动,呈其审阅。之后于5月中下旬又三度书信往返,遂成定稿。迨至7月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我想到上图的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尚无星煜丈的墨宝,便将其前言手稿及连同给我的四通相关信札捐给了手稿馆。
他知道后,表示要将一批文化界人士给他的信件捐给上图。2013年5月28日,星煜丈将四十余位文化、戏曲界人士共两百余通信札捐赠上图文化名人手稿馆。之前特地招我到其府上一起挑选,除有涉及写信者的个人隐私不宜捐赠者外,哪怕有对其学问提出不同意见及批评者,皆不作保留,全部捐献。他于不少信件,或对撰写者作了特别的介绍,如称徐朔方先生于“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十二万分坦率。任何事情绝不顾情面,一概秉公处理。两次纠正我的错误。我认为我们的相处在当代学术界是少见的”;或提示信的文献价值不能忽略,如于卢豫冬先生之札,谓“彼此一直联系,到他逝世。信三件,内有左翼剧联重要史料”。其坦荡、认真有如是者。同时他还捐赠了一迭手稿,带有歉意地说:“过去随写随扔,未及处理的稿子被档案馆要去,就剩这点了,以后会给上图留着。”然而,再也没有以后了,惜哉。
星煜丈生前有一个心愿,希望上图所藏清初朱素臣校刻《西厢记演剧》这部孤本能够影印出版,这是他研究《西厢记》的一大发现,惜皆以各种原因无果。我去六院探望时,向他表示会继续想办法出版此书,他说现在没精力写前言了,我说可以用发表过的论文代序。窃以为,书是有魂的,要在识与不识。现在他走了,书魂也被勾走了,留下的,是我对长者无尽的思念。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