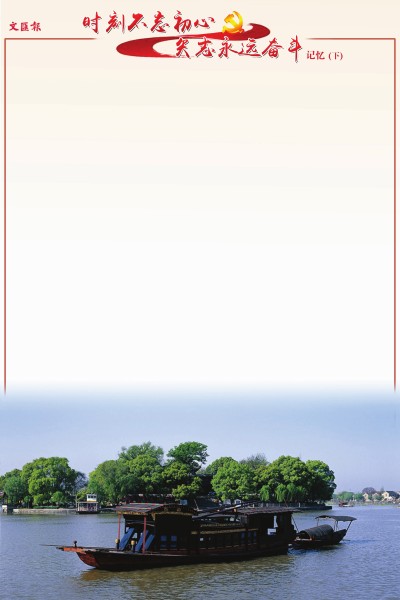回顾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
邵岭
1921年7月,如同一记砸向旧世界的锤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向世界宣告成立。从当年上海望志路石库门建筑里一间18平方米的房间,到浙江嘉兴南湖上的红船,年轻的政党出发,启航,引领了跨世纪的航程。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她手握真理,浴血奋斗,把人民对新中国的憧憬与理想变成现实,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开天辟地,锻造出中华民族驶向复兴彼岸的航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一大到十九大,从一大召开时的全国50多名党员到如今8900多万名党员。信仰始终是我们高扬的旗帜,也如同血脉,融入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肌体。今天,站在新时代的门坎,在走向“两个一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我们回首过去,回顾党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为的是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本报记者 刘力源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中国共产党走过光辉历程。党在上海诞生,这一历史选择看似偶然,但蕴含着一种必然。
兴业路76号,隔壁就是喧嚷的新天地。上海的热闹,这一带最为明显。
而96年前,这里静得很。当时,沿望志路 (今兴业路) 只建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房屋簇新,马路对面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沿马路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
1921年7月23日,平均年龄28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而来,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走入望志路上的106号(今兴业路76号),之后的故事已家喻户晓。
而后,直至1933年转移到江西瑞金,中共中央与上海结缘12年,其间虽有过短暂迁移,最终又回到了上海。这12年,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 (除三大在广州召开),构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整过程、开启了大革命的新高潮。
回到起点,回到这幢保留着上世纪20年代风貌的老宅,一个个问号被点亮———为何是这里?为何是上海?为何是城市?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一历史选择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必然性?
特殊的城市提供特殊环境
无论是政治环境、社会环境还是交通通信,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
“一个会议在某一个地方举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考虑到那时上海城市特殊的政治格局与特定的区域功能,像中共一大这样的会议在上海、在法租界举行,还是有某种必然性的。”学者熊月之认为,无论是政治环境、社会环境还是交通通信,对一个全国性的、国际联系频繁的政党的成立及发展,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
熊月之将当时的上海概括为“一市三治”———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管辖区域、管辖权及司法系统等都是各自独立的———这就跟单一性的城市有所区别:“单一性城市在行政管理上有其有效性,而当时的上海管理边际效益比较低,相对来讲,从事党的工作就有比较大的安全性。再加上制度差异,客观上为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
尽管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但是在当时,仅从政治环境来看,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远不如上海宽松。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气氛压抑,文化环境恶劣。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再是《新青年》编辑部南迁,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这期间很多政治精英、文化精英选择了上海,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是其中一员。
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很多选择居住在法租界。熊月之梳理了1919年至1921年,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参与或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分子的住处:“都在法租界,而且相距不远。中共一大的选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就居住在附近。”选择居住法租界,而非公共租界,是与前者的发展有关。法租界重文化,工商业不如公共租界发达,税收相对较少,建设较慢。1914年对于法租界来说是个发展的界线———之前法租界只有2000多亩,租界中心是金陵东路;1914年法租界向今鲁班路以西的地方扩展,一直延伸到肇嘉浜路以北、徐家汇一带,面积一下增至15000多亩,中共一大会址(房屋建于1920年)所在的区域1914年后才发展起来,属于法租界的边缘地带,相对僻静,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激进人士,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等都在这一带居住,原因在于这一带房子较便宜,房价大概是金陵东路等市中心的五分之一,又临近租界交界处,方便组织活动,而且法租界的集权管理模式相比公共租界效率不高。另一方面,相对集权的管理模式也使得法租界成为上海实行城市规划最好的区域,从道路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法租界的品位与宜居在当时的上海比较突出,这也是很多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选择此处落脚的原因。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面临的危险严重加大,上海临近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南京政府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整个环境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了一个天地,意味着党的活动、工作重心发生变化,由城市转移到农村。1933年,中共中央决定撤出上海,迁至江西瑞金。
全国化的上海有独特优势
城市性格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性格;文化性格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
中共一大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在上海,他们便于隐藏身份,这是很多城市不具备的优势。“上海外国人多,外地人多,这是很要紧的。如果是在一个外地人很少的地方,一大代表的外地口音会被马上听出来,但是在上海这很正常,当时的上海85%的人都是各地而来,可谓‘南腔北调’。”熊月之说,1860年以后,当时的上海可以免受战火波及,相对安全。再加上城市大,容易解决就业问题,因此国内尤其是江南一带一旦发生战争、灾荒,人们会逃向上海。“上海的第一波人口及财富就来自江南,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的富户为上海带来了资金,穷人带来了廉价劳动力。1921年,上海已经有240万人口,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是当时的特大城市。在一个移民城市里,中共一大代表的到来不会显得突兀。”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上海开会,跟共产国际也有关系。“当时整个欧洲严重打压共产主义,马林、魏金斯基 (中文名吴廷康) 等人熟悉欧洲的政治环境,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又不太熟,所以警惕性特别高。中共一大开会期间,闯入了巡捕,马林等人尤其紧张。”而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为马林、魏金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熊月之认为,当时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那么信息发达,可以跟国际上任何大的城市有通信往来,交通上跟欧美、日本及南洋都有轮船航线,面向国内还有内河航线。清末铁路的发展,更使上海成为交通和信息通信的枢纽。上海当时又有全国最多的报纸、电台等媒体,甚至连弄堂里都有电台———世界上出了什么消息,第二天上海就知道了。
上海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还表现在,许多新发明、新产品如电话、电灯、汽车在上海的使用跟西方大城市几乎同步,这与侨居在此的西方人有一定关系,当时在上海安家置业的西方人少则三四万,多的时候有八九万,其中很多人都自称“上海人”,他们使用一些新式物品对中国人的示范效应非常强,而上海对这些先进的东西接受得也非常快。
有学者认为,城市性格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性格,上海对西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于全国其他城市。当现代科技大潮席卷而来时,西方的现代元素传至国内,上海是一个最好的载体。作为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打破了社会原有的等级差别、文化差别———西方的观念、文化与本地文化交融,形成“平台文化”,这种文化性格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同时,上海的商业程度高,成熟的商业社会,法治程度往往也很高,两者作用下还能够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工厂集聚。“当时的上海可谓机会遍地、出版业也非常发达,人人都看报纸从中寻找机会。这种生活方式与留学生留学的国家极为相似,因此很多人留学归国后就往这里聚集。他们把外国的方式拿来中国实行,尽管方式可能不同。”
红色基因组成的全新政党
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
“生产力和文化的地域先进地位,赋予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学者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座城市是一个最适宜先进政党诞生的地方———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城市的近代化与政党的先进性相统一,体现着上海地缘政治的机理。
中国共产党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先进文化,工人阶级则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胚胎里的红色基因。
“如果不具有新的品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多添了一点水滴,没有实质性意义。而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国内当时其他政党的根本特质。”齐卫平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已经出现过好几百个。民国初年各种政党蜂拥而立,但停留于权力争夺的政治乱象,使政党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相脱离,因此,民主共和的新型国家形态落于徒有虚名的空壳。
“可见,当时的中国正在寻找一种先进力量和先进文化的结合,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结合。”齐卫平认为,是上海以近代城市的先进含量,为中国共产党画上了组织基因的红色符号,“上海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能量和工人运动水平,在中国共产党筹建的整个过程中具有典型性;同时,作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无疑也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意义。可以说,当时的上海是培养中国共产党先进品性的最佳土壤。”
历史的确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发展,在这片土地上,1920年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等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商议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就表现出了另起炉灶的建党志向。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重镇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
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这样描述工人运动的深远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这一条十分重要。没有它,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战争,而且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太平天国的事实所证明了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上海诞生,正是基于这里有着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力量。
关于工人阶级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学者金冲及进一步作了阐释:与农民不同,工人阶级跟现代化大生产结合在一起,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马克思主义则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个现代工业大城市,是十分自然的。”
上海工商业最为发达,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期间,还是在甲午战争后以及辛亥革命前后,具有规模的大型企业几乎都选择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
上海适合开展工人运动还有一个原因是,上海工人的组织程度比较高。齐卫平领衔著成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里有这样一段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外资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上海虹口———杨树浦、浦东陆家嘴、沪西曹家渡等工业区的形成。这些工业区均临靠黄浦江或苏州河,航运便捷、地价不高,从而使近代工业在兴办和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自然集中的趋向。“大规模集中工业区的形成促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成长,使得这里的工人运动开展组织水平比较高,政治上的成熟也相对领先于全国。五四运动后,上海工人罢工斗争显示的强大威力更是突出表现了质量水平上的政治觉悟。”
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从根本上看是中国革命力量主体力量向工人阶级位移的历史象征。之后中共中央长期设在上海,也与此有关。1923年7月15日,在广州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称:“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往上海,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1927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后来经过多次讨论,还是决定迁回上海,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在上海出版
“1899年,第一次有中国刊物提到 《共产党宣言》 里的内容,就是在上海。”学者忻平告诉记者,他学生时期曾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到过当年的 《万国公报》 相关材料:“那也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被中文刊物介绍。”
作为对外交流中心和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中心,上海在传播先进文化、集聚知识分子方面优势明显。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日本思潮影响较深,许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著作通过日文出版物被大量翻译进国内,上海集聚的大批日本留学生在其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金冲及回忆道:“解放初,我曾问过陈望道,当初为什么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说是在日本受到的影响。”《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在上海出版。
齐卫平指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共有9人留学日本,占据全部成员的一半以上。他们在日本各大学学习法律、教育、新闻、理工等知识,并在此期间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的还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日本共产党员山川均、堺利彦等有接触。“而其他各地早期党组织成员,大多在国内高校或中等师范学校接受教育。”
再来看出版业的助力。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中国出版中心,全国出版业的80%以上集中在这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从著书、编书到印刷、发行,都相当齐备。“出版业发达说明这个地方相对安全,且输入西学的东西多、容易传播。”熊月之说,“从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开始,到戊戌变法提倡制度变革,到辛亥革命,新文化相关内容的出版,主要是在上海。”
提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就不能不提到《新青年》,这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分量的杂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成为党的机关报。熊月之说,从陈独秀经营《新青年》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对于陈独秀的事业有实际意义。“即使陈独秀到北大任职、《新青年》编辑部移京以后,其排字、印刷、发行地点仍是上海。”1920年5月,从北京搬回上海的《新青年》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这期专号被视作《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其筹备时间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时间重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很大一部分成员与《新青年》、《觉悟》副刊、《星期评论》社等有着重要的关系。他们或是其中的骨干成员,或是重要的撰稿人。可以窥见,上海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时起到的作用。
而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工业重镇的上海,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优质土壤,而知识分子就是两者之间的黏合剂。金冲及在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里评论过京沪两个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对马克思的研究比陈独秀深。而陈独秀有着烈火样的性格,往往更急于行动。这时他的目光已更多地转向工人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已经意识到光靠学生运动难以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上海让他看到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此时的陈独秀明显表现出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动向。“一些活动于上海的党的创始人,会自觉到工厂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之中培养运动骨干;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创办《劳动界》《上海伙友》等面向工人的刊物,开展宣传启蒙教育。这些条件在其他城市不是很充分,也因此促进了更多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选择到上海来。”齐卫平说。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正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建党做准备的过程。
重温记忆,是为了更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