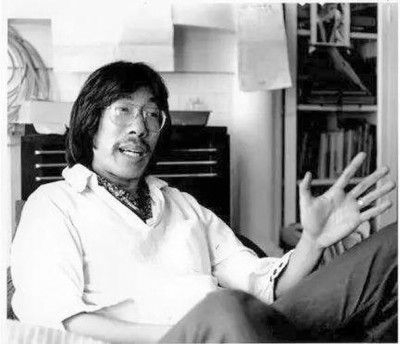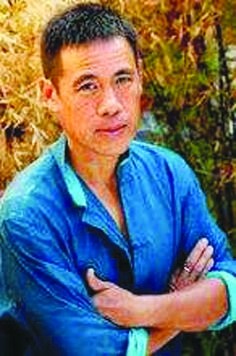苏少伟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场域,即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它有两个显著特征:斗争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人们对此思潮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我们仅从国内的视角来看待一种文学思潮,眼光是否太过狭隘?于是,我想考察一下华裔美国文学对左翼文学资源的借鉴,从较广的视野来看待左翼文学。不少华裔作家正是在左翼文学精神的旗帜下,创作了迄今仍有影响力的作品。
要说左翼文学对华裔作家的影响,就不能不提到赵健秀(Frank Chin)。熟悉华裔美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他的地位不下于汤亭亭、谭恩美等人。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他的开创性拓展,华美文学才有了更宽广的格局。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赵健秀受过左翼文学精神的影响,但他的战斗精神至今让人感怀。
赵健秀的文学观点很特殊,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史中独树一帜。他认为文学是斗争场域,文学家需要争夺话语权。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战斗,一切皆需战斗!他的小说正是这种文学观念的产物。《甘加丁之路》要与陈查理(白人想象出来的)的虚伪形象斗争,《唐老亚》要与华人男子“女性化”的刻板社会印象斗争……他经常借用关公、李逵的形象,在突出他们英雄气概的同时,又渲染他们的战斗精神,这与左翼文学的精神内核有相通之处。赵健秀的文学思想、写作风格、作品内容等,确实展示出了强烈的现实批判与斗争精神。
还有一些华裔美国作家,他们受左翼文学影响的源头很清楚。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志英(Russell Leong)和朱丽爱(Nellie Wong)。
梁志英是华美诗歌界、小说界的“两栖”作家,又是一位学术评论家。他的作品《凤眼及其他故事》曾获得2001年美国图书奖。关于亚裔/华裔美国人,梁志英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兼具诗人、政治家和战士气质的人”。这样的看法比较特殊,值得关注。
梁志英信奉“生活即是战斗”的信念。在这种文学观念的主导下,他的创作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为人生”的倾向。而追根溯源,梁志英的文学实践正是受左翼文学精神的影响。他曾经说过:
关于我们的文学艺术,甚至华裔美国文学艺术,我喜欢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看待。他说过,革命文艺应当从真实生活中塑造各色各样的人物,帮助人民群众推进历史前进。我不认为历史总是向前而没有曲折和倒退,但我坚信,我们在内心必须坚持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人民的理想,坚持真正的社会改革。
这里,梁志英清楚地说到了自己的理念来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影响并不是浅表的,它已经深入到梁志英的精神世界中。他的一首名为《恒河》(Ganges)的诗作很具代表性:
竹篙/从混合着黄泥沙的/河里掏出/牲口、船只、死尸。/那里的喧闹声,不是乔治·哈里逊/1971年刺耳的歌的切分音,/是1991年滚滚奔腾的洪水。(张子清译)
1971年的歌,指的是1970年代某些西方青年对孟加拉国进行的“艺术想象”,构造出孟加拉“黄金社会”的“虚伪形象”。事实上,这样的虚构对孟加拉国及其人民来说,并非现实。恒河的大水、人民的横死、万物的遭殃、财产的损失,这才是现实,才是文学要关注的现实批判问题,因此,必须向“假升平文学”开战。左翼文学精神的两个维度:现实批判与斗争性,在此可见一斑。梁志英也由此展开自己的思考。
朱丽爱是华裔美国文学中最富个性的作家之一。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其作品涉及种族、性别、阶级等尖锐问题,充满了愤怒、反抗精神:
“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这句话来源于丁玲《三八节有感》,它被朱丽爱放在诗集《长气婆之死》(The Death of Long Steam Lady)的前言里。这种斗争精神是朱丽爱的写照,也照耀着她的文学之路。
在朱丽爱文学生涯之初,一位白人男性大学教师就反对朱丽爱的“愤怒诗篇”,从根本上说,这就是在否定朱丽爱的文学创作。这种不公正的遭遇,造就了朱丽爱反抗一切的精神韧性。她反抗社会、种族、性别、阶级等的不公平。在《长气婆之死》中,朱丽爱写道:
当我成长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很脏。我以为上帝使/白人干净,不管我如何洗澡,/我改变不了,在白色的水里/我搓不掉我的肤色。(《当我成长的时候》,张子清译)
甚至,她也反抗文学本身。《长气婆之死》这本集子总共三十一篇作品,其中有二十九篇是诗歌,然而特别之处在于其他两篇:小说《长气婆之死》和《走进镜中》。我们很难看到哪位诗人在其诗集里混进小说。但朱丽爱就是如此“不服从”,从一定意义上说,她达到了一种反抗的极致。
其实,不只是华裔作家,很多亚裔作家或多或少也受到过左翼文学精神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受此影响呢?反抗现实,反对不公正,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赵健秀等人的时代(甚至目前),华裔的形象在现实中、在文学想象中、在历史记述中不外乎几种:第一,东方主义式的想象——男性像女人,女性又很乖顺;第二,难以摆脱的“噤声”现象,长久以来无法在主流社会中说出自己的心声;第三,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边缘地位。概而言之,社会现实给华裔作家们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不平等的现象一直存在,这是需要打破的“铁屋”,需要做一番“破坏”,需要战斗,于是很自然的,他们就转向了具有斗争精神的左翼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