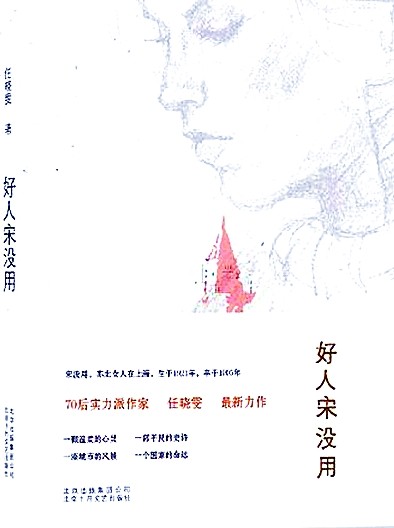■项静
“宋没用,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这是《好人宋没用》后记中任晓雯的第一句话,也是这部小说的全部精简得当的人生事例和形式。一个普通女人在业已成型完整有序的历史时空中被断层一样发掘出来,一个人搅动一潭深水。
小说聚焦1921到1995年间上海的生活空间——曾经出现在各种文学意识和装置中,现代文学以降,众多作家曾以各种方式塑造过它的形象,再现这个空间中的人物和生活,形成各种固定形象和命名,聚集和构造处理这一时空纪实和虚构的方式、修辞和意象。这是任何处理这一时空的文学所必须面对的潜在对话者,任何想要有所作为的叙事者都无法视而不见的。
任晓雯把一个在上海生活的普通女人和她的人生节点赋予了长篇小说的形式,以语言的重新锻造,从“她们”回到“她”的写作理念的反拨和回撤,以扎实细致的针脚去映衬一个普通人庸常漫散的一生。与当下写作中遍地的雄心以及并不对称的呈现效果相比,任晓雯收束和用力的每一步都在恰切的点上。她从细微之处扬尘,去撬动更多的写作对应物,看似简单的故事和精炼的形式所开启的,是精微而复杂的文学空间和需要重新衡量的文学标准。
据悉,在路遥文学奖研究中心举行的2017上半年度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评审会上,经评委反复讨论、共同投票表决,《好人宋没用》成为两部入围作品之一。
菲茨杰拉德说:“小说来自于历史的缺陷。”小说这一文类的合法性,有时就是建立在对宏大历史的插入和拯救上。它拯救那些被历史遗忘的私密时刻,被各种叙事所无能为力的细部和褶皱之处,潜藏着世俗的事例和事件,当然又绝不会也不应该止步于此。任晓雯的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以及“浮生”系列短篇小说,在面对众生的现世时,都是一首安魂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叙事者以朴实健康的肌理去建设每一个平凡人的一生,仿佛是在模仿创世的动作。“浮生”取其字面意思,或者避免社会学深度阐释模式,是这部小说或者任晓雯近期创作中所发明和描摹的一种人生存在形式。一个普通人如宋没用,又或者张忠心、袁跟弟、周彩凤、许志芳们,都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浮在潮起潮落的人间,浮在时代的热流中,没有办法建立起牢固的主体性,但他们都在完成自然的人生。人的一生是各种事件的集合,其中某一个事件或者最后一件事可能改变集合的意义。确立了时间的尽头(叙事的时间)以后,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加以描述就变得顺理成章,并且生出自然人生并不具备的意味和仪式感。
福楼拜曾向屠格涅夫讲述《布瓦尔与佩库歇》的创作计划,屠格涅夫强烈建议他从简、从短处理这一题材。这是来自一位年长者和成功前辈大师的完美意见。因为一个故事只有在很短的叙述形式下,才可能保持它的喜剧性效果;长度会使它单调而令人厌倦,甚至完全荒谬。但福楼拜坚持己见,他向屠格涅夫解释:“假如我简短地、以简洁而轻盈的方式去处理(这一题材),那就会是一个或多或少具有些精神性的奇异故事,但没有意义,没有逼真性;而假如我赋予它许多细节,加以发挥,我就会给人一种感觉,看上去相信这个故事,就可以做成一件严肃甚至可怕的东西。”
任晓雯以长篇的方式去结构《好人宋没用》,应该是预设了对逼真性和严肃性的追求。在克制了大历史和地方叙事的诱惑之后,把一个“没用”之人所经历的人生足迹和内在风景呈现出来,它所带来的是生存的严肃性和密度之美。密度之美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在这种时间跨度较大的日常生活史诗中,推动故事进展、保留悬念的必要性要求一种情节的高密度,而小说家要保持生活非诗性一面的所有逼真性,则必须对抗高密度的戏剧化。但漫长历史场景中的事件那么丰富,那么多的巧合和内在的勾连,遵从文学和历史的惯性,必然会失去它逼真性的一面。
另一个问题,任晓雯在小说的附注中说,本书所有历史细节都已经过本人考证,亦即表明所有细节都是公共的细节,所依据和参考的历史著述和口述历史,保证了生活的真实性和它的公共性。大众化的历史故事背后对于革命的历史,也采取了浮泛的形式,“叙事者”跟宋没用几乎采用了同一视线,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期待太容易消散在这个漫长、曲折摇荡的人生长河里,变成一份精心绘制的历史流水清单。将不同的历史时代放置在同一个严整有序的小说形式中,等同于抹平很多差异。艺术的可怕之处在于,一旦它获得某种形式,就再也不去寻找从未说过的东西,而是乖乖地为集体生活服务,它会使重复变得美丽,帮助个体祥和地、快乐地混入生命的一致性中。
“浮生”是任晓雯系列短篇小说的名字,浮生又是一个形式,拒绝跟历史任意随便轻简的调情,以一种有距离的语言和眼光再现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具体处境。“浮生”又是任晓雯借以深入历史处境的灵魂的知识,一种抓住这一历史处境的人性内容的知识。作家在对具体人生的严肃观察和历史故事的重新排列组合中,萃取了新的艺术上的差异性。明清小说的古典意蕴,半文半白、陌生化的词语和名称,减缩的最少的抒情语言,触目即是所见所得所闻。叙事者最大的存在感就是语言上的独特性和统一性,在上海话、苏北话、普通话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杂糅,以简短的句子、有古典意韵的词句、古朴的口语,制造了一段与现在的距离,它封锁和深化了已被过分历史形象化的生活。
任晓雯《好人宋没用》是一部质实的小说,铸就了坚实的写作底线,并把语言从陈述和描写上升为形式本身。只有用一连串的字句和意象,才能对读者和小说艺术作出适当的提示。《好人宋没用》是一个混合体的芳香,普通劳动者借由深度描写所折射出来的神性的光彩,大历史宏阔前行途中遗漏的私密时刻,熟悉的历史事实侵入虚构后被精致的语言蓬松出来的新质地,以及抵御一种艺术观点离开之后尚存的余温,旧有轮廓若即若离的光晕,是存在本身的偶然与艺术必然的遭遇。这就是亨利·詹姆斯在批评托尔斯泰时所主张的另一种长篇小说的样子,“绝对精巧构思的艺术”,又像一首卑微而有尊严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