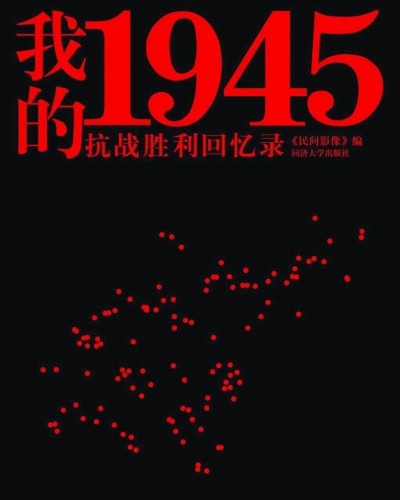该书汇集全国各地近八十位亲历者回忆1945年抗战胜利以及接管、接收、复员、团圆的动人场景,首度披露部分珍稀史料和珍贵影像,包括当事人日记等。全景式记录抗战胜利前后的巨变及其对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全面呈现抗战胜利带给中国人民的快乐,见证中华民族屈辱的终结,填补民族记忆的重要空白。
到达《新民报》当晚,就编发毛泽东应蒋介石电邀前来进行国共和谈的新闻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喜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四川自贡市贡井那个小镇上。西安报界的朋友赵荫华电告,重庆《新民报》正招兵买马,延揽人才,准备战后到南京、北京、上海三地发展,如我愿去《新民报》工作,他可以推荐。赵兄是山东人,抗战初期原是《新民报》老编辑;后因叔父赵自强在济南出《华北新闻》(日报)内迁西安,他奉叔父之命辞去《新民报》职务,主持自家报纸编务。而我也曾是他在《华北新闻》十分相得的同事。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此以后,我的命运发生转折。我运气不错,到重庆那天,竟是吉日良辰。原来同时到达的是应蒋介石三次电邀前来进行国共和谈的毛泽东。我到了《新民报》为躲避敌人轰炸的临时办公地——重庆郊外大田湾的编辑部时,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暗自说了一声:“他怎么可以到重庆来,多危险啊!”
重庆《新民报》每天出报两次,日报前一天夜间编印,次日早晨出版。晚刊上午编印,下午二三点钟发行。日报总编辑方奈何与我一见如故。他对我说:“赵荫华已写信介绍你了。你是有经验的熟练编辑。放下行李,吃过晚饭就上班吧。大概这一路上你也听到了,今天出了大新闻啊!你编辑本埠新闻,这是我们报纸的一大卖点。”
原来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正是这天下午三点三十七分。
国民党不许各报的中国记者采访。《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是《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暗中邀请同车去机场的。
我当晚开始上班工作,设在通远门外七星岗的采访部已发来第一批新闻稿,主要是浦熙修的现场特写,写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在机场受到欢迎的情况和重庆街头群众自发的欢迎盛况。稿子里还写了毛泽东在临时下榻的张治中公馆宾主交谈细节。我做的新闻标题是“走向和平建国之路,毛泽东为团结而来”。我还没与浦熙修见面,先看到她的稿子。她是《新民报》采访主任。
毛泽东8月28日到渝,遍访故旧。30日在临时下榻的桂园设宴请柳亚子、沈钧儒等人。柳诗兴大发,即席赠新作七律一首,诗云:“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9月2日《新华日报》以《赠毛润之老友》为题,发表此诗。9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拜访柳亚子,柳请毛校订1935年的旧作长征诗,准备收入《民国诗选》一书,同时又向老友索取新作。毛回答新作没有,只有1936年初到陕北时见天降大雪,填的咏雪词《沁园春》,明天当录呈审正。柳得毛词大喜,请画家尹瘦石配画与自己的诗一起在中苏文化协会的一个展览会上展出。限于客观环境的种种不利条件,观众不是很多,只有出席毛泽东招待会的各界代表性人士浏览一过。毛、柳二诗随后送交《新华日报》发表,但《新华日报》只在11月11日刊出柳诗,未刊毛诗。
陈德铭的朋友王昆仑在柳公馆见到了这一阕新词,十分倾倒,抄录了一份给黄苗子,黄又给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编辑吴祖光。他们常在一起玩,是至交,两人一商量,立刻发稿、见报。《沁园春》后面的按语或短跋,也是两人合作。
14日见报后反响之热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日《新民报》晚刊被抢购一空,连次日的日刊也供不应求。其他报纸纷纷连篇累牍地刊发步原韵与毛词唱和之作,也有人批评毛词流露帝王思想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奉命鼓噪,指桑骂槐,直至骂“草寇称王”“封建割据”成不了大事。
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方面加强钳制舆论,严密检查新闻。共产党为加强宣传工作领导,派陈翰伯、孙大光等参加《新民报》编辑部工作,由陈铭德的朋友王昆仑出面推荐陈任副总编辑,负责晚刊工作。陈出身燕京大学新闻系,“一二九”运动中,他是民先队领导人,曾陪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陈又介绍孙做编辑部主任。
陈铭德不想得罪共产党,致使手下大批进步记者灰心泄气,也怕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局责怪“你们报纸办得很像《新华日报》了”,弄得他瞻前顾后,十分为难,很想有个能领会“居中偏左,遇礁即避”这一精神的人加入晚刊编辑部班子。
我进报社不久,就发现方奈何是一个正直的老报人,但思想较保守,编辑方针重在“遇礁即避”。他处理版面不出岔子,深得老板信任。但也常删改、压下采访部一些能“出彩”的新闻和言论。尤其是浦熙修为首的进步记者对他素无好感,双方时有龃龉。我编辑本埠新闻后,编记矛盾很快缓解。方奈何则因我是他聘用的,也深得人心。他有意要提拔我,让我当编辑部主任,进而晋升主笔之类,以巩固其总编辑地位。
接周恩来指示,编发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遭国民党士兵枪击新闻
政协会议期间,政治形势变化很大。国共双方的矛盾与斗争之外,社会上许多矛盾不断暴露、激化,一条消息、一个版面的处理,一篇言论的措辞和语气,事事牵涉到报社的立场观点。我到重庆《新民报》上班后,以同行晚辈、同乡人的身份径直去民生路《新华日报》采访部找石西民。1938年我们在浦江就相识,也知道彼此情况。所以相见后以家乡方言交谈。“南蛮舌”这种土话只有本乡百里方圆听得懂,所以畅所欲言。我详细说了自己从抗战开始参加民先运动,又如何去西安的经历。特别是羁留西安那四年的各种遭遇,认识交结的各色人等,也坦陈自己得失感知与觉悟。
过了些日子,我去找石西民,要求从《新民报》转到《新华日报》工作。我觉得《新民报》虽好但不是久恋之地,既已立志投身革命就要干“新华”这样的报纸。石西民批评我好高骛远。他以为我在《新民报》更合适,要准备长期干下去。“《新民报》那些人许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党尚且要派人帮助他们办报,宣传抗战,你怎么反而要出来?”这一句话,让我在《新民报》蹲了七八十年,这是后话。
《新民报》作为党报的友报,《新华日报》不便发表的稿子过去都由石西民交浦熙修等转发《新民报》,但老板胆小怕事,方奈何思想保守,对国共双方均无好感,尤其是较激烈的稿子都要压下。他认为我是他的人,能体谅他,拥护他,感激他的恩德,仰仗他保全一二。开始时对我很放心,后来发现“看错了人”。因为我对新闻稿的取向与他大有差异,而且一些明显站在共产党立场的讲话也见了报。有一次,国共和谈中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关键问题上唇枪舌剑争持不下,重庆郊外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秘书李少石(廖仲恺何香凝之女公子廖梦醒的丈夫)在进城公路上突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中弹殒命。周恩来正在会谈的座间,听到消息不敢惊动毛蒋二人,不动声色赶赴医院,探视回来已是晚间。他同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邓颖超等研究后认为:此事如果公开,一定会闹大,势必影响和谈大局。但如果不公开,又怕进退失据,将来被动。消息最好由《新民报》这样的民间报纸来发表为是(后来查明,是蒋军一个士兵在公路边解溲,被车后扬尘眯了眼,开枪泄愤酿成奇祸。凶犯被军法处置,事乃平息)。石西民当场写好新闻稿,经周恩来过目后送到七星岗《新民报》采访部,由浦熙修发往大田湾编辑部。这时石西民已打电话给我:“此稿务必设法明天见报。”稿子发排前须过方奈何一关,他一见就皱眉头:“这种稿子只能在新华社登!”我耐着性子向他解释半天,他总算给了个面子,板着的面孔有些缓过来,勉强放行:“删短些,登小点。”结果看大样时发现版面很大,很不高兴,但又不便当众发作,因为我毕竟是他引入的人,是他藩篱的一部分,平日里他总是在人前人后夸我的。
自此以后,我在他眼里成了忘恩负义之徒,我也自觉为难,向老板推说失眠症严重,神经衰弱,要求做日班,调到陈翰伯手下编辑晚报。晚报编本市新闻缺乏好手,陈翰伯、浦熙修表示欢迎。
9月3日是“胜利日”,日本投降,中国胜利,国共和谈,凯歌声声,重庆市的庆祝活动达到最高潮,可以说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全民狂欢节。
在这沸反盈天的热闹中,毛泽东在重庆访问故旧,拜会新交,广泛开展统战活动和社会调查工作。别的不说,单是新闻界他就约了许多人谈话。《新民报》受邀的是张恨水、赵超构两位。张恨水是妇孺皆知的通俗小说家,“名满天下”,共产党很重视其社会影响。《新华日报》曾在不久前以专刊为他五十岁生日祝寿。他有爱国心,同情弱者,对政治淡漠,与毛泽东谈话不多。赵超构不同,他曾在1944年夏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写了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在国统区产生很大影响。赵超构曾因一偶然机会,与毛泽东并肩坐在一起,一同观摩延安平剧团演出的《打渔杀家》等京戏。
赵超构小毛泽东十七岁。两人以“先生”相称,俨然忘年交和布衣交。这次胜利后在重庆相见,两人从朝至暮整整谈了一天,次日赵超构到报社来,与毛泽东长谈的事一字不提,过了许多年也拒绝话及此事。我和他最相与的几个朋友常常上小馆子吃酒,只在酒兴高时禁不住大家追根问底“敲打”,他才吐露片言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