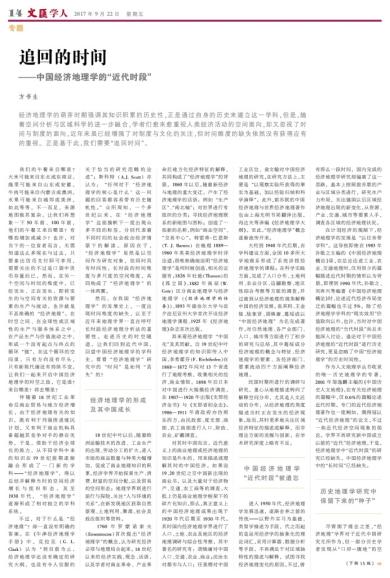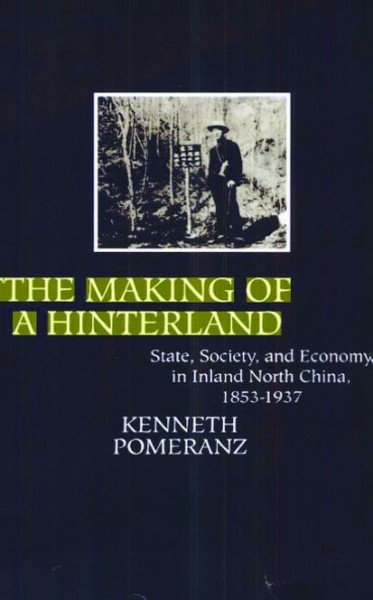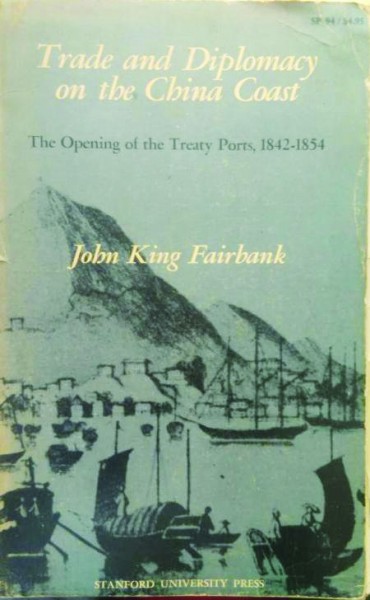方书生
经济地理学的萌芽时期强调其知识积累的历史性,正是通过自身的历史来建立这一学科,但是,随着空间分析与区域科学的进一步融合,学者们愈来愈重视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面向,却又忽视了时间与制度的面向,近年来虽已经增强了对制度与文化的关注,但时间维度的缺失依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正是基于此,我们需要“追回时间”。
我们的午餐来自哪里?大米可能来自东北或东南亚,蔬菜可能来自山东或安徽,牛肉可能来自内蒙古或澳洲,水果可能来自城郊或美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来源地图极其复杂。让我们再想象一下50年前、100年前,他们的午餐又来自哪里?有哪些增加或减少?也许,对当下的一位食者而言,无需知道这么多现在与过去,只要拿出货币支付即可享用,需要关注的不过是口袋中货币存量而已,然而,在另一个空间与时间的维度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与空间有关的资源与要素的生产与流动,也许就是不甚准确的“经济地理”。在时空之间、在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生产与服务体系之中、在产品生产与价值流动之中,形成一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循环“链”,在这个循环的空间里,只有方向没有尽头,只有新陈代谢没有持续不变。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时空之旅,它是谁?来自哪里?将去哪里?
伴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后商业贸易与地方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地理有关的知识,既有利于列强推进殖民计划,又有利于商业机构具备超越其竞争对手的潜在优势,于是,借助于经济全球化的推力,从不同学科中来的知识在19世纪前期逐渐融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地理学”,得以总结并解释当时的空间经济增长与组织形态,及至1930年代,“经济地理学”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系统。
不过,对于什么是“经济地理”?却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在《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中,克拉克(G. L. Clark)认为“到目前为止,经济地理学还没有确定的研究大纲,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关于恰当的研究范畴的论述”;斯科特(A.J. Scott)亦认为:“任何对于‘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都容易带有历史随机性。”众所周知,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经济地理学”这面旗帜下一度出现众多不同的标签,分别代表着不同时间的社会政治经济情景下的解读。原因在于,“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以空间作为研究对象,但同时具有时间性,长时段的时间维度与多尺度的空间维度,共同构成了“经济地理学”的一体两翼。
然而,在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史上,一度出现时间维度的缺失,以至于近年来地理学界一直在呼吁长时段经济地理分析法的重要性。走进历史的时空隧道,让我们回到近代中国,回望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史,看看“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时间”是如何“丢失”的?
经济地理学的形成及其中国成长
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欧洲运输技术的改进、工业生产的出现、劳动分工的扩大,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种类大幅增加,促成了商业地理知识的积累。经济学界开始探索生产、消费、财富的空间分配,以及贸易的空间形态;地理学界则进行旅行与探险,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在新发现地区获取自然景观、土地利用、聚落、社会及政治组织等资料。
1760年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首次提出“经济地理学”的概念,认为研究经济必须与地理结合起来。18世纪以来的经济实践、观念、话语,以及学者对商业革命、产业革命后地方化经济特征的解释,共同构成了“经济地理学”的背景。1860年以后,随着新经济与地理的重大变迁,产生了经济地理学的话语:例如“生产区”、“南北轴”;对世界进行有组织的分类;寻找经济地理联系的新地图与图标;创造了一些新的名称,例如“商业空间”、“交易中心”。特雷弗·巴恩斯(T. J. Barnes)在梳理1889—1960年英美经济地理学时评论道:很难准确地说明“经济地理学”是何时被创造,相关的证据有:1826年杜能(Thunen)的《孤立国》、1882年高兹(W. Gotz)区分商业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的任务》)、1893年康奈尔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首次开设经济地理学课程、1925年《经济地理》杂志首次出版。
再来看经济地理学“中国化”及其贡献。自19世纪中叶经济地理学的知识即传入中国,李希霍芬(F. Richthofen)在1868—1872年间对13个省进行了地理考察,收集相关的经济、商业情报。1898年后日本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调查,在1907—1920年出版《支那经济全书》与《支那省别全志》。1906—1911年清政府亦仿照东西方,由民政部、度支部、商部、农工商部进行人口、财政、农业、矿藏调查。
对其时中国而言,近代意义上的商业地理或经济地理的知识是外生的,用来描述或理解其时的中国经济。如果说19、20世纪之交中国新出现的商业书,以及大量对于经济物产、交通、农工商等的调查,大抵上仍是商业地理学框架下的碎片化知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地理成果出现于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其时国内经济地理学界进行了人口、土地、农业及地区的经济地理调研与综合性考察,其中著名的研究有:胡焕庸对中国人口、交通、农业、商业;沈汝生对都市与人口;任美锷对中国工业区位、翁文翰对中国经济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观察实验所获得的事实为基础,加以经验归纳和科学演绎”。此外,前苏联的中国经济地理与世界经济地理著作也由上海光明书局翻译出版,冯达夫等译编《经济地理学大纲》。至此,“经济地理学”概念逐渐流传开来。
大约到1940年代后期,在学科建设方面,全国10多所大学地理系形成了系统讲授经济地理学的课程;在科学实践方面,完成了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边疆勘察、地区性综合考察等方面的调查,并过渡到从经济地理的视角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张其昀、王金绂、陆象贤、胡焕庸、葛绥成以“中国经济地理”为名完成著作,对自然地理、各产业部门、人口、城市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总结,其中葛绥成分经济地理的概念与特征、经济地理学的要素、各经济部门、要素流动四个方面阐释经济地理。
民国时期所进行的调研与研究,重心从地理描述转向了解释空间分布,尤其是人文活动的分布,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描述当时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故而,其时更多地关注区域经济特征的描述或解释,而非理论方面的发掘与创新,在学术研究深度上略有不足。
中国经济地理学“近代时段”被遗忘
进入1950年代,经济地理学发展迅速,逐渐舍弃之前的传统——以野外实习为基础、类型学描述为手段,代之而起的是运用经济学的抽象化的理论词汇,采用计算器、数据分析等手段,不再满足于对区域独特性的描述与解释,试图寻找经济地理变化的原因。不过,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国内完成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却偏离了这一思路,基本上按照前苏联的产业与区域分类进行,研究生产力布局,关注建国以后区域经济地理出现的新变化,从资源、产业、交通、城市等要素入手,调查各区域的经济地理状况。
在计划经济的规制下,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是“以任务带学科”。这导致即使在1983年孙敬之主编的《中国经济地理概论》里,在总论论述工业、农业、交通地理时,仅用很少的篇幅描述近代时期的情形以为背景。即便到1990年代,孙敬之、刘再兴等编著《中国经济地理概论》时,论述近代经济布局变迁的篇幅也不过5%。除了经济地理学学科的“现实效用”价值取向以外,也许,当时对中国经济地理的“当代时段”尚且未能深入讨论,遑论对于中国经济地理的“近代时段”进行历史研究,更是忽略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历史时间性。
作为人文地理学丛书收录的唯一历史地理学的专著,2001年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在有关经济地理的篇幅中,仅0.6%的篇幅论述近代时期。专门的近代经济地理著作也一度阙如,偶得冠以“近代经济地理”的论文,不过一些近代经济空间现象的简论。学界不再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近代”经济地理,于是,经济地理学中“近代时段”的研究已经缺失,中国经济地理学中的“长时间”已经缺失。
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保留下来的“种子”
尽管囿于理念之差,“经济地理”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研究无所作为,但一部分历史学者发现从“口岸—腹地”的空
间视角,能够理解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随着更多具有地理知识背景的学者加入,新的力量在边缘地带逐渐生长。
1、观察中国:口岸之于腹地与中国的涵义(1950’s—1960’s)。
1953年墨菲(Rhoads Murphey)的《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出版,表明口岸城市成为透析近代中国的一个窗口。1956年费正清(J. K. Fairbank)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中,从沿海条约口岸的外力冲击角度理解近代中国初期的适应。1960年代后,“费正清模式”与“冲击—反应”概念的政治性思维取向受到了质疑。侯继明对外国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述,德恩伯格(Robert F. Dernberger)对于外资与口岸的解释,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从近代以来经济的全局,探讨口岸城市与内陆之间的关系。
2、识别中国:从口岸解释近代区域经济变迁(1970’s—1990’s)。
1960—1970年代,随着历史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在刘翠溶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不再是把口岸城市简单地作为透视的窗口,首次对贸易进程、商品流通、市场结构、贸易影响诸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1973—1983年间,台湾学者对口岸贸易的研究一时蔚然成风,对相关口岸的贸易、贸易效用、腹地经济变迁等进行了新的研究。至此,已经大大超越了墨菲、侯继明、德恩伯格等一般的经验性认识。
因为中国的地方性变异幅度很大,1984年柯文提出需要提升中国研究的“精度”,即将中国“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县、城市。其时,在“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的框架下,台湾“中研院”多位学者分别研究闽浙台、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安徽、广西等地区,试图探讨1860—1930年代中国各地在西方冲击后发生的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变迁的过程,及其成败的原因。这一系列研究表明,学界已经超越了口岸与区域的一般性讨论,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对口岸贸易、区域变迁、传统商业关系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及至1990年代,大陆学者在近代口岸贸易和区域经济成长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尤其在相关的水运与港口史、城市史方面,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大约在同时,台湾学界对近代口岸贸易、大区域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也进行了拓展。
20世纪下半叶的口岸贸易与近代中国研究,从空间与地理的角度切入,对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多维考察。但在同时,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历史经济或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讨论近代经济变革,暂时未能形成学科史上的突破,故而一度陷入困境。
成长中的中国经济地理学“近代时段”
大约在1990—2010年代,现代经济地理学的知识、理念、方法工具被引入近代口岸与区域研究,具有历史、经济与地理知识背景的学者,将时间与空间分析相结合,开启了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的研究。
1、从口岸贸易转向经济地理(1990’s—2006)。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1993)讨论了晚清以来国家转型与国家对不同地区服务的重新配置,及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的影响,从核心、边缘等区域视角,观察了近代不同“区域”的塑造过程。戴鞍钢(1998)从上海港口建设历程、城市崛起、港口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变迁的影响、上海和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建构方面,关注港口、城市、腹地这三个密切相关的要素。大约同期,吴松弟(2004)认为近代“港口—腹地”格局及其引发的各区域现代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趋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在《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中,吴松弟(2006)等从经济地理的视角讨论了中国现代经济的空间展开过程,总结了近代以来港口城市与腹地的空间演变。
就在地理学界对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的研究搁置之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从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开启了“港口—腹地”及其空间形态的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港口—腹地的双向经济联系、互动作用及其动力机制,从而将口岸贸易研究逐渐扩展到经济地理研究。
2、中国经济地理学的“近代时段”(20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深度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的空间形态也迅速发生了巨变,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大国经济及其属性越来越令各界瞩目,学界在研究这一现象的同时,不由地询问其长期演化的起源、路径与趋势。最近十多年来,学界相关的研究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梯式的进程。
第一,有关口岸、腹地与区域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吴松弟、樊如森、王列辉、武强等人的著作,形成了一些相对规范的学术路径,对近代口岸的研究已超越了港口贸易本身和区域影响的一般分析,开始将历史、地理和其他研究思路进行整合,以构建融合时间、空间诸要素的分析框架,更多地触及到经济地理学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第二,有关劳动地域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新产业空间的研究,以及网络经济、区域集聚与集群、干预与管制、文化与经济关联方面的研究,同样正在被有效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的研究之中。例如,有王哲、吴松弟、Keller W、Li B、Shiue C H、王茂军及笔者等对近代贸易网络与结构、空间组织、空间经济增长的研究,采用近代中国旧海关等面板数据,尝试分析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一些高频问题,验证了相关议题在近代时期的特征与表现,类似于格雷戈(Derek Gregory)对约克郡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地理的研究。
第三,随着相关的文献、工具、方法积累的初步完成,学界开始探索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地理的格局、特征与内涵,最终形成了九卷本“近代中国经济地理”(1840—1949年)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017年),分为绪论与全国概况卷、江浙沪卷、华中卷、 西南卷、华南卷、闽台卷、华北与蒙古高原卷、西北卷、东北卷。其中第一卷以全国为整体获取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线索,并纵向分析各部门经济地理,其余8卷分别以一个大区域为对象,探索各大区域近代经济地理的特征与差异性,“1+8”形成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的总论与分论系列。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史上看,该丛书第一次对中国历史经济地理进行完整全面的分析,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探索,弥补了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近代时段”学术研究空白,将成为中国经济地理学“近代时段”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起点。
学科史上的意义与期待
我们知道,在经济地理学的萌芽时期强调其知识积累的历史性,正是通过自身的历史来建立这一学科,但是,随着空间分析与区域科学的进一步融合,学者们愈来愈重视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面向,却又忽视了时间与制度的面向,近年来虽已经增强了对制度与文化的关注,但时间维度的缺失依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史并非是范式的演替,而是一个核心经验的发展,即以不同的尺度来解释空间经济,使得人们对于其时的环境、生活以及不同类型现象之间的联系与关系有更深层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思里夫特(N. J. Thrift)、奥尔兹(K. Olds)倡导从社会的多元性方面,从真实世界的角度重塑“经济地理学”的边界,实为睿智之见。陆玉麒从人文地理学科学化的总体目标与实现路径角度,提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历史过程的长时段分析方法。李小建也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同一阶段不同类型的经济地理研究。从樊杰等梳理的近30年来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演化来看,已经逐渐遵从学科发展的内在脉络,回归追溯“经济地理学”发展史的谱系。
当前是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时代,它能够解释我们面临的问题。例如,可以测度与分析我国第二次融入全球化时代很多具有经济地理特征的集聚与扩散现象的效用及其成因。如果说这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新领地,那么在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经济地理学的旧领地又在哪里?从上述的学术维新史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目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界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其基本研究方法和路径,也完全可以运用于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的研究,也完全可以移植到近代时期来进行验证,比如,近代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测度、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及机制等。随着近些年大量近代中国城市地图、大比例尺地图(尤其是日军和美军军用地图)的发现、整理和出版,进行小尺度的城市内部经济地理或城市地理研究的条件也越发具备,有助于从长时段的角度厘清我国城市化与城市地理的演化路径。中国经济地理“近代时段”研究的复兴,将能提供一系列更为清晰、准确、完整的经济地理变迁案例,将能寻找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地理变迁的历史脉络。从“近代时段”的研究中可以探索源自中国历史基因上的特色之处,从时间与演化的维度上丰富并发展中国经济地理学。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