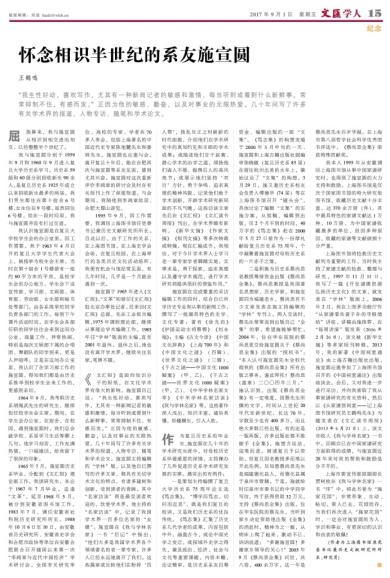王鹤鸣
“我生性好动,喜欢写作,尤其有一种新闻记者的敏感和激情,每当听到或看到什么新鲜事,常常抑制不住,有感而发。”正因为他的敏感、勤奋,以及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几十年间写了许多有关学术界的报道、人物专访、随笔和学术论文。
屈指算来,我与施宣圆从相识到相交进而知交,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
我与施宣圆分别于1959年9月和1960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历史系59级和60级分别招收新生90余人,是复旦历史系1925年成立以来招收新生最多的两届。我们男生都住在第十宿舍6号楼,女生住在9号楼。虽然同住6号楼,但在一段时间里,我与施宣圆并没有打过交道。
我认识施宣圆是在复旦大学校学生会的办公室里。因工作需要,我于1963年4月召开的复旦大学学生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校生会主席。当时在第十宿舍1号楼前有一座约60平方米的平房,是校学生会的办公地方。学生会下设宣传部、学习部、文娱部、体育部、劳动部、女生部和秘书处等部门,由各系推举的同学负责各部门的工作。每到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在学生会各部任职的同学往往会来到这间办公室,商量工作,异常热闹,特别是每次文娱部下属的合唱团、舞蹈队的同学到来,更是人声喧哗。正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我认识了在学习部工作的施宣圆,得知我们都是由历史系推举到校学生会来工作的,更感到亲切。
1964年9月,我考取历史系胡绳武先生的研究生,继续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期间,在学生会办公室,在宿舍,在校园,遇到施宣圆时,我们总会就学校、系里学习生活等聊上几句。他学习刻苦,工作充满热情,一口福建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5年7月,施宣圆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文汇报》理论部工作。我读研究生,本应于1967年7月毕业,适逢“文革”,延至1968年5月,被分到安徽省图书馆工作。1983年7月,调任安徽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88年10月6日至10日,由安徽省历史研究所、安徽省史学会和合肥市政协等单位在安徽合肥联合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研讨会,全国有关研究单位、高校的专家、学者共70多人参会,包括上海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生和姜铎先生。施宣圆也应邀与会。离开复旦十年后,能在合肥再次与施宣圆等系友见面,感到尤其兴奋。施宣圆对这次重新评价李鸿章的研讨会及时在有关报刊上作了深度报道。与会期间,我陪他到李鸿章故居、合肥大蜀山游览。
1995年9月,因工作需要,我调回上海图书馆任党委书记兼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自此以后,由于工作的关系,在上海图书馆,在上海史学会会场,在复旦校园,在上海举行的各类历史文化活动场所,我便有机会与他经常见面,有几年时间,几乎是一个月就会遇到一次。
施宣圆于1965年进入《文汇报》,“文革”初曾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后来回《文汇报》总部,先在工业组当编辑,1975年调到理论部,继续从事理论学术编辑工作。1985年任“学林”版面的主编,直至2001年退休。退休之后,他也没有离开学术界,继续关注名家,笔耕不辍。
文汇报》是面向知识分子的报纸,在文化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施宣圆自己说:“我生性好动,喜欢写作,尤其有一种新闻记者的敏感和激情,每当听到或看到什么新鲜事,常常抑制不住,有感而发。”正因为他的敏感、勤奋,以及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几十年间写了许多有关学术界的报道、人物专访、随笔和学术论文。施宣圆主持编辑的“学林”版,以及他自已撰写的许多文章,都具有关切学术文化的特点,有诸多建树和创新,受到读者的青睐。其中“名家访谈”则是最受读者欢迎的,饮誉学术界。他主持的“名家访谈”中,记录了我国学术界一百多位名家的“业绩”。施宣圆在《我与学林名家》一书“后记”中指出:“他们大多是我国学术界各个领域著名的老一辈专家,许多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些篇章或反映他们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时崭新的时代面貌,介绍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的真知灼见和丰硕的学术成果;或描述他们甘于寂寞、潜心学术的治学之道,颂扬他们诲人不倦、提携后人的高风亮节;或展示他们坚持‘双百’方针,勇于争鸣、追求真理的精神风貌,记录他们敢于学术创新,开辟学术研究新局面的不凡气魄。这些访谈文章先后在《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刊出,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新华文摘》《作家文摘》《报刊文摘》等多次转载或转摘。现在汇编成书,我相信,对于今日学术界人士学习老一辈专家学者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以及遵守学术规范,进行学术研究将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
施宣圆在完成繁重的采访编辑工作的同时,结合自已所学历史专业和从事的新闻工作,撰写了一批颇具特色的史学、文化专著:著有《徐光启》《护国运动主将蔡锷》《刘永福》;主编《古文今译》《中国文化辞典》《上海700年》和《中国文化之谜》(四辑)、《世界文化之谜》(三辑)、《千古之谜——中国文化1000疑案》(甲、乙)、《千古之谜——世界文化1000疑案》(甲、乙)、《中华学林名家文萃》《中华学林名家访谈》《我与学林名家》等。这些著作深入浅出,知识丰富,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作为复旦历史系的毕业生,施宣圆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对母校历史系怀着感恩的深情,主持操办了几件促进历史系学术研究发展的实事。最突出的有两件:
一是策划主持编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75周年论文选《笃志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既是我们复旦的校训,又是我们历史系的优良传统。《笃志集》汇集了历史系几代学者的成果,内容包括中外,涵盖古今,或论中国史学之变迁,或探域外史学之得失,兼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重要课题,内容丰赡,论证精审,是历史系系友自筹资金、编辑出版的一部“文集”。《笃志集》的构想发端于2000年3月中旬的一天,施宣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张晓敏(复旦历史系85届)在前往杭州出差的火车上,肇始议论了“文集”的构想,3月29日,施又邀历史系校友会负责人傅德华(74届)等在上海图书馆召开“碰头会”,具体讨论了编辑“文集”的实施方案,从组稿、编辑到出版,仅2个月不到的时间,40万字的《笃志集》赶在2000年5月27日前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复旦历史系75周年,个中凝聚着施宣圆对母校历史系的一片赤子之情。
二是积极为历史系蔡尚思老教授筹措资金出版《蔡尚思全集》。蔡尚思教授是我国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施宣圆同为福建老乡,蔡尚思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施主持编辑的“学林”专刊上。两人交谈时,蔡先生常常说到出版自己“全集”的事,希望施能够帮忙。2004年,住在华东医院的蔡尚思更交给施宣圆关于《蔡尚思全集》出版的“授权书”:“本人认可施宣圆先生全权代理我的《蔡尚思全集》所有出版之事务。谨此拜托!蔡尚思(盖章)二四年三月。” 施认识到,出版《蔡尚思全集》有一定难度,因蔡先生所撰的文字,时间从上世纪20年代至新世纪,长达70年,字数至少也有400多万,而且绝大多数已经出版,有的还是一版再版,许多出版社都不敢接手《全集》。施想方设法,迎难而进。曾请复旦予以资助,但复旦因老教授多而难以开此先例。后知悉蔡尚思先生是福建德化县人,而德化县属于泉州市管辖。于是,施就给时任泉州市委书记的中学同学写信,终于获得资助32万元,支持《蔡尚思全集》出版。住在华东医院的蔡先生,当听到家乡决定资助他出版《全集》的消息时,精神为之一振,从病床上爬了起来,激动不已,讷讷说道:“多谢施宣圆!多谢家乡领导的关心!”2005年9月《蔡尚思全集》问世,共八卷,400余万字。这一年是蔡尚思先生百岁华诞。在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评选中,《蔡尚思全集》荣获特殊贡献奖。
我本人1995年从安徽调回上海图书馆从事中国家谱研究时,也得到了施宣圆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上海图书馆是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的特大研究型图书馆,收藏历史文献十分丰富,达370余万册(件),其中最具特色的家谱文献达1万种,10万册,为中国家谱收藏最多的单位,但因多种原因,收藏的家谱等文献破损十分严重。
上海图书馆将抢救历史文献列为重要的工作,当时我主持了家谱文献的抢救、整理与研究。1997年11月11日,我写了一篇《开发谱牒资源 弘扬历史文化》的文章,就发表在“学林”版面上。2006年2月,我在上图多功能厅作“从家谱看炎黄子孙的寻根情结”讲座,讲稿由施推荐,在“每周讲演”版发表(2006年2月26日),该文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2013年,我的新著《中国祠堂通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施宣圆应邀参加了上海图书馆召开的《中国祠堂通论》出版座谈会。会后,又对我进一步进行采访,并向我索取了我从事家谱研究的有关资料,然后以《从家谱到祠堂——记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先生》为题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6月21日)上,该文亦收入《我与学林名家》一书中。回顾自已在中国家谱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与施宣圆近20年来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贾树枚在《我与学林名家》一书“序”中,将此书誉为“施家花园”,非常形象、生动、贴切。斯人已去,花园犹存。当我们再次进入“施家花园”时,一定会对施宣圆的为人、学识和事业,有更深切的认识和由衷的敬佩!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兼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