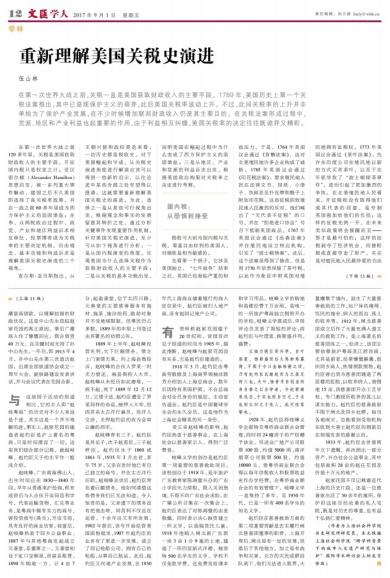宋钻友
赵家花园曾是海上著名公共空间。它是南下北上的政府高官钟爱的下榻之处,还为各方沟通交流提供了合适的场所。1911年至1913年,孙中山先生曾三次莅临赵家花园。其建造者粤商赵灼臣,热衷于慈善救助,兴办了不少社会公益事业。
上海开埠后,不少华商经商致富,热衷辟土造园,享受饶有野趣的林下生活,张园、愚园、徐园、甘园、周园、叶园即其中声名较著者,但这些当年颇为知名的宅院大多已被时间的尘埃湮没,赵家花园(即虹口扆虹园)留存至今,堪称沧海遗珠,令人欣喜。保护好这座晚清著名的私人宅院,不仅是当地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也是文史工作者的责任。当务之急,是尽快厘清该园的历史,为其修复提供学术基础。
赵家花园的历史见于著述的不多,但也流韵可寻。徐珂的《清稗类钞》列有专条,一叙其详:“扆虹园以地为上海公共租界志虹口,故名,即靶子路也,俗呼‘赵家花园’,为粤人赵某所建筑,颇似西式园林,达官贵人恒借座以宴客。陈设器物以舶来品为多。”徐珂虽为知名著述家,但这一记载有误,扆虹园之名与建在虹口无关,当时沪上另有一座扆虹园,由南京辛姓富商建于新闸王家厍,叠石为山,疏泉为沼,风格类明清江南园林。孙玉声的《沪壖话旧录》中《南北园林变迁》一节历数晚清北市的私家宅院,对扆虹园作了介绍,指出新闸扆虹园“俗呼辛家花园”。故清末民初,上海的媒体报道扆虹园,必在前置限定词,以“虹口扆虹园”指赵家花园,以俗称径指新闸扆虹园为“辛家花园”。
赵家花园位于苏州河北部的老靶子路111号(今武进路453—455号),时属美租界,据报道当年赵园的周围住的多为洋人。整个建筑呈狭长型,第一进为两层的门楼,门楼后为长方形天井,两旁莳有花草,天井后为三层的楼房,楼房后为厅堂。厅堂外辟有花园。赵家花园的园子并无特色,但厅堂空间很大,装潢精致奢华,反映出当时上海著名富商的品味和消费水准。1935年赵家花园举行一次拆除前的家具拍卖,受托拍卖行在媒体上列出了拍卖品,我们因此有机会见识当年赵园之内部装饰:
广东红木镶石台椅、柚木洋式各种台椅、酒架,福州漆器、台椅,精刻云石镶屏风,云石及玻璃罩座钟、紫檀圆台大钟,康熙、雍正五彩青花,建窑纷蓝洋瓷大小花瓶、盆子,金鱼缸石山、花园登、古铜瓶、宣炉、镶瓷挂屏,名人字画、绣画、洋画,飞兽人物摆件,洋瓷火炉浴缸、电灯、火炉器具。
人们不难从这份拍卖清单中感受到主人对传统风格的喜爱,也可从西洋玩意的点缀中感受到主人兼容并包的品味。正是极度的奢华、宽敞的空间,且位于租界,环境安全,交通方便,使这家私人宅院成为海上著名的公共空间。
赵家花园不是一般的仕商行台,却是南下北上的政府高官钟爱的下榻之处。在这里能借得一眠的大都系名公显宦,其中不乏出洋大使、政府各部门的首长(晚清的尚书、侍郎)等,尤其是广东籍京官。赵家花园还为各方沟通交流、联络情谊提供了合适的场所,不少中外联谊活动曾在此举行。1906年清政府外务部邮传部农工商部派员到上海接待美国来华商业代表团,该团乘高丽丸到上海,外务部代表亲自到吴淞迎接,中方官员先把美国代表团一行40余人送往汇中旅馆,当日“下午3时在赵园举行茶会欢迎代表团,14晚在张园筵宴,16日下午乘小轮赴杭”。味莼园(即张园)和赵园成为官方接待美国代表团的两个公共场所。中国的地方官员多次在赵家花园会见各国驻沪领事官,把酒言欢。1905年江苏巡抚陆某来沪巡视,下榻斜桥洋务局,当日下午4点上海商务局董事在张园宴请陆某,次日上午陆某拜访驻沪各国领事,随后在赵家花园与各国领事叙筵。
正是在频繁的社交活动中,赵家花园不经意间成了小说家石黑一雄笔下的中国的达林顿勋爵府邸,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连接起来。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在中国许多城市展开,上海的抗议活动尤其激烈,一度发生罢市。这场运动的激烈程度超出了美方的估计,也超出了上海绅商的想象。为使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上海绅商代表唐露园等人曾与美国新任驻沪领事在赵家花园进行磋商、谈判。这是赵园介入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个记载。
赵家花园最值得写入历史的是,孙中山先生三次莅临赵家花园。1911年12月30日,上海广东社团在赵家花园设宴招待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欢迎孙中山先生,从苏州河桥堍到老靶子路赵园的马路张灯结彩,营造出浓浓的气氛。第二天,上海的广东香山县同乡绅商设宴,孙中山先生再次到赵园与同乡欢叙。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此时两次造访赵家花园,偶然中隐藏着必然。开埠后,大批粤民北上,至1910年代,上海的广东人口已升至苏浙两省之后的第三位,经济势力颇强。孙中山在革命中素来重视向华侨和同乡寻求支持,临时政府成立后,经济奇窘,孙中山有意通过临时政府的官员伍廷芳、温钦甫以上海广肇公所董事的身份向上海广
潮富商借款,以缓解拮据的财政状况。这是中山先生莅临赵家花园的真正原因。事后广潮商人作了慷慨回应,联合借资40万元,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孙中山先生。一年后,即1913年4月,孙中山先生第三次造访赵园,出席全国铁道协会成立一周年大会,就铁路建设发表讲话,并与会议代表在花园合影。
与这座园子活动的报道相比,它的主人即“赵姓粤商”的历史对不少人来说是个迷,其实这是一个并不难解的迷。事实上,赵家花园的建造者赵灼臣是沪上著名的粤商,只是时间湮没了一切。这里我们综合部分记载,就赵岐峰、赵灼臣父子的生平作一粗浅介绍。
赵岐峰,广东南海佛山人,出生时间应在1830—1840年间。早年从香港来沪经商,积有成资后与人合伙开设同昌利字号,代客运输货物、汇兑等业务,是粤商中颇有实力的商号,曾投资质号(典当),开设书局,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致富后,赵岐峰热衷于同乡公益事业,1887年与其他粤商发起成立元善堂,系董事之一。元善堂初设于虹口宝顺里,房屋系租赁,1890年购地一方,计4亩7分,起造善堂,位于北四川路。元善堂的主要慈善服务有施材、施茶、施诊给药,救助对象并不受地域限制,但粤民仍占多数。1889年的申报上刊登过由其署名的劝捐公告。
1889年上半年,赵岐峰经营失利,欠下巨额债务,债主上门索债无果,向上海县衙投诉,赵岐峰的合伙人罗某一时无力偿还,被县衙拘入大牢,赵岐峰从未经历如此磨难,一病不起,死于1889年12月12日。父债子还,赵灼臣遭受了罗某同样的命运,被押入大牢,但因其系太古洋行雇员,经洋人交涉,关押赵灼臣的改为会审公廨的西牢。
赵岐峰育有三子,赵灼臣是其长子,次子赵甫臣,三子赵梓臣。赵灼臣生于1860或1861年,1935年3月去世,享年75岁。父亲在世时他已有自己独立的商号,并在太古洋行任职。赵岐峰去世后,赵灼臣背负着巨额债务,他如何清偿这些债务我们已无法知道。令人惊奇的是,父亲遗下的债务没有把他击垮,同昌利不仅还在运营,十余年后又有所发展。1902年前后,该号开始经营美国面粉批发,1907年赵灼臣的业务有了更进一步发展,成立了同记轮船公司,拥有自己的轮船,从事沿江航运。此后,赵灼臣又向地产业发展,在193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商人征信录中,赵灼臣被归入地产商,设有赵同记地产公司。
有资料称赵家花园建于20世纪初,该园首次见于报道的时间为1905年,据此推断,赵岐峰与赵家花园没有关系,它是赵灼臣建造的。
1918年3月,赵灼臣由粤商劳敬修及上海商界领袖沈联芳介绍加入上海总商会,数年后因持有英国护照,不合总商会对会员身份的规定,主动宣告退会。赵灼臣是中国寰球学生会的永久会员,这是他作为上海社会精英的另一身份。
受父亲赵岐峰的影响,赵灼臣热衷于慈善事业,在上海社会以慈善家示人,得到广泛赞誉。
岐峰义学的创办是赵灼臣第一项重要的慈善救助项目。该校创办于1918年,是年旅沪广东教育家陈鸿璧兴办的广东小学因无力续租,限入关闭绝境,不得不向广东社会求助。在广肇公所召集在一次集会上,赵灼臣表达了对陈鸿璧的由衷敬佩,同时表示决心独资建立一所义学,以造福贫民儿童。1918年他购入闸北新广东街一块3亩1分9毫的土地,建造了一所四层新式洋楼,能容纳500名学生的义学,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免费发给课本和学习用品。岐峰义学的购地和造楼经费7万余两,是唯一的一所旅沪粤商独立捐资开办的学校。岐峰义学落成后,申报评论员发表了简短的评论,将赵灼臣与叶澄衷、杨斯盛并列,盛赞:
以独力捐巨资兴学,自叶澄衷、杨斯盛而后久焉渺焉寡俦。不图于今日金融枯窘之顷,乃有赵灼臣氏继起而与之鼎足而三也。夫叶、杨皆手自创业而身自誉之以办学者,今赵君继承先志,于实也则自任之,于名也则以归之于先人,此天性笃挚也。
1928年,赵灼臣将岐峰义学全部转交粤侨商业联合会管理,同时将24幢房子的产权赠予该会,另送业广地产公司股票100股,约值5000两,南洋烟草公司股票500股,约值10000元,使粤侨商业联合会得以每年房租收入和股票收益充作办学经费。在粤侨商业联合会的有效管理下,岐峰义学一直维持了多年,至1930年代,已是一所有400名学生的知名义学。
赵灼臣在慈善救助方面的第二项重要贡献是忠实履行闸北慈善团董事的职责。上海开埠后,闸北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落后于其他地方。加之每有战争和灾害,北方的灾民成群结队南下,他们无法进入租界,大量麇集于境内,滋生了大量慈善救助的工作,如尸体的掩埋、饥民的施舍、病人的医治、孤儿的收养等。1912年,闸北慈善团成立后作了大量充满人道主义的救助工作,是上海著名的慈善团体之一。经济上,该团主要依靠旅沪粤商及江浙丝商,尤其是前者,经常慷慨解囊,组织同乡商人,热情捐款捐物。赵灼臣曾出资为慈善团建造了两层楼的医院,以收养病人。曾捐地15亩,供慈善团开办工艺学校,专门教授所收养的孤儿以谋生能力。赵灼臣的慈善救助不限于闸北及同乡社群,每当各地闹灾,总能看到受助机构在收到大善士赵灼臣的捐款后在报端发表的感谢公启。
1933年,赵灼臣去世前两年立下遗嘱,再次捐出一部分资产,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其中包括面积28亩的赵庄花园及价值十万元的地产。
赵家花园不仅记载着近代上海的历史片段,还是一位慈善家生活了30余年的寓所。保护好这座历经沧桑的私人宅院,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有益于弘扬仁爱精神。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跨学科背景下的城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