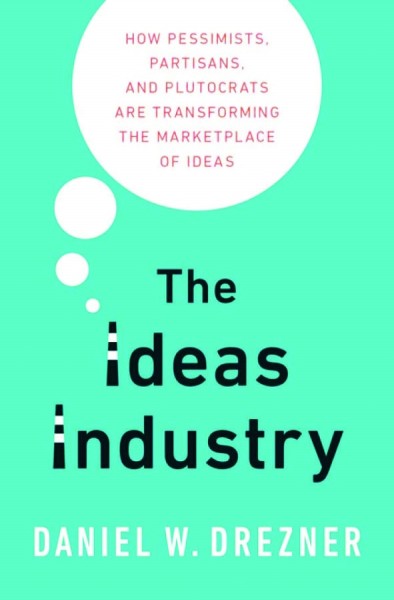编译/郭大路
崛起的巨富阶层,对新型“思想”满怀热忱。巨富阶层当然没有选择老派的“知识分子”,而是一手扶植了新型知识分子代表。今天的公众,相比复杂的思想,也更愿意接受漂亮的“大思考”。那些既受大众也受巨富阶层欢迎的想法被变现,新型知识分子由此跻身昔日只属于名流的财富圈。
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德莱茨纳(Daniel W. Drezner)新著《思想产业》(The Ideas Industry)日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知识界局内人观察“思想”产业链及陈述其弊端之书。《新共和》杂志近日(2017年6月28日)刊发了关于此书的长篇书评《巨富阶层如何制造新型知识分子》(The Rise of the Thought Leader)。
书评作者大卫·塞森斯(David Sessions,波士顿学院现代欧洲史专业博士生)重提193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葛兰西认为,相对于教师、教士、行政官员那些地位稳定的“传统知识分子”,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等新兴知识分子将走向历史舞台,把大众处于无意识水平的“常识”提高到自觉的水平。而现在,近九十年之后的美国,相对“有机知识分子”走向历史舞台,时髦的话题早已变成“知识分子的撤退”:高校日益与世隔绝,学术思考日益精致狭窄,加上条条框框的博士生培养制度,都导致知识分子对公共话题的失语。
正是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德莱茨纳教授分析了思想从结构到表达的运行机制,在他看来,今天的公共空间就像个市场,三大要素决定了美国知识分子的财富水平:公众失去了对研究机构的信任、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和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巨富阶层(superrich)的崛起——该阶层对新型“思想”满怀热忱。
巨富阶层当然没有选择老派的“知识分子”,而是一手扶植了一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他们的代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这些知识分子,充满怀疑和分析精神,其旨趣在批判,在展示事物的复杂性;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桑伯格(Sheryl Sandberg)“用他们自己的视角去解释世界,然后把这种世界观向全世界散播”,其冲动则在于“改变世界”。而今天的很多读者,相比复杂的思想,更愿意接受漂亮的“大思考”,“值得注意,市场对新想法以及思考世界的有趣想法,有着强烈的需求”。
近的例子,是上周末刚刚在上海举办的《人类简史》作者演讲大会,那更像一场时尚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远的例子,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想在全球经济中胜出,需要与众不同,需要一个像迈克尔·乔丹那样不同凡响的品牌”——该观点看着更像营销法则而不是哲学洞见,“但商界崇拜弗里德曼的写作,认为他道出了技术和全球化如何改变了全球经济”,他的信息强化了这些人既定的世界观。这些知识分子将他们这些既受大众也受巨富阶层欢迎的想法变现,跻身昔日只属于名流的财富圈。
凭借《西方的衰落》走红的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德莱茨纳所谓思想产业链中的典型案例。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弗格森直率地表示,自己从牛津学者转型写这类著作,“都是为了钱”。一边是学界的看法,一边是一小时7.5万美元的演讲费,换你是弗格森,会如何选择?三十年前,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更愿意在学院或科研机构谋职,稳定收入和生活的吸引力很大。三十年后,情况不同了。
作为注脚的信息是,成名之后的弗格森拼命给思想变现,为电视系列剧写书、大价钱卖演说、在各种刊物写文章,疲惫中的他最终像其他思想领袖一样被抓现行:2012年他在《新闻周刊》发表的关于奥巴马的封面故事,错误和误导信息被一一曝光。但在这个品牌远比内容重要的思想领袖产业里,类似这样的错误并不影响思想领袖们继续赚钱。弗格森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思想产业通过真人秀、高额演说费用和可观的图书预付版税,轮番引诱学者们,他们在重压之下往往不得不稀释专业性以追逐金钱,甚至兜售虚假的思想商品。
不妨再多举一个意见明星成为品牌后“大而不倒”的例子。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提出“破坏性创新”,他把用新科技和新商业模式改变行业图景的公司称为“破坏者”。这个概念在硅谷太受欢迎了,它妥帖地迎合了巨富阶层的世界观:成功偏爱敢于承受风险的勇敢者。这个概念红了几十年,出了八本系列著作、在哈佛创立了增长与创新论坛、开了自己的咨询公司的克里斯坦森,在2014年才被雄辩地反驳(Jill Lepore, “The Disruption Machine”,New Yorker):克里斯坦森断言被“破坏者”吃掉的西捷技术,在他做完研究的第二年,业绩就翻倍,倒是被寄予厚望的破坏型公司已经销声匿迹。当然,批评克里斯坦森理论的论调在硅谷并不受欢迎。
巨富阶层花钱制造思想代表者的后果,可不止制造夸夸其谈的思想者:那些曾经是知识分子从事有意义研究的后盾的研究机构,也已被其新赞助人激进地重塑。过去几十年来,来自政府机构和慈善组织的资金几乎耗尽,智库需要从公司、外国政府、政界精英那里开源。这些人对做研究当然没有兴趣,他们在乎的是为自己赞成的观点提供政治上的支持。或者更赤裸地说,他们想要投资获得回报。结果是,智库变得越来越偏狭。德莱茨纳举例说,美国前参议员吉姆·德名(Jim DeMint)在2012年被任命为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主席后,就将重心从科研转向了政治,以满足捐助者的需求。
在高校工作也不免受到类似的影响。随着校董会里出现越来越多的银行家、投行人、不动产投资者,长久以来的学术研究不受工业影响的原则被搁置一边。即便名校也向工业界开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被英国石油公司(BP)资助的研究发表了广为人知的结论——深水地平线的石油污染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严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接受了数百万美元的赞助,以提供一项关于“政府面临的财政挑战”的高中课程,名为“我们为什么要削减政府津贴”——要知道与此同时,金融服务公司BB&T为几十个高校捐资,推广“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以及安·兰德的思想。
如巨富阶层所愿,今日美国的思想领袖共享着同一个核心世界观:巨富和巨富阶层获得财富的渠道不单合法,并且是英雄主义的,即巨富阶层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巨富“破坏性创新者”雄心勃勃地想要向世界证明自己合理,最不掩饰的例子是彼得·蒂尔,他设立的10万美元奖学金,专供那些“跳过大学或辍学”的大学生。另一个例子,是TED这样的演讲平台,通过各种付费演讲传递硅谷崇尚的历史观:科技正在让我们越来越好。
最后,让我们回到比葛兰西更久远的时代回溯“思想产业”。《美国保守派》杂志资深编辑诺亚·米尔曼(Noah Millman)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撰文分析说,“idea”一词源自希腊文里的“看见”,在其原始语境中,思想是一种形式,当你看见后得以理解现象背后本质的形式。“industry”一词则源自希腊文中的“勤奋”,意为生产特定产品的经济部分。当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原本应该是一个可信赖的、生产能有助于理解事物真实本质且对文明有所增益的事物,但在德莱茨纳的今日美国的语境里,则意味着某些学者和智库的智囊们如何用知识资本迎合政策制定者,如何仅仅通过一代人,就用进击的思想领袖,将思想从“市场”转变为产业:曾经,在市场上,参与者带着不同需求交换货物,现在,在产业里,生产是为了满足顾客的特定需要。
不过,或许这也不是坏事。从很多层面来讲,世界史上还没有哪个时刻像今天一样充满各种思想,好的、坏的,来自这些“品牌知识分子”的、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只不过知识分子的思想赚的钱少得多而已。“而且我们总倾向于用过去时代最好的思想和今天的平均思想比较,因为时间已经过滤掉那些坏思想。”
《金融时报》书评在对这本书大加赞赏之余追问,“一定要对这本书提出什么批评,那就是他的应对方案颇为无力。他呼吁高校和智库从投资方那里独立出来。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他们怎么负担得起独立成本?”就像另一个颇具讽刺的事实是,作者一直在这本书里批判这类知识分子,但这本书涉足的也不是作者专长的国际政治领域,并且,他依然使用弗里德曼们的方式结构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