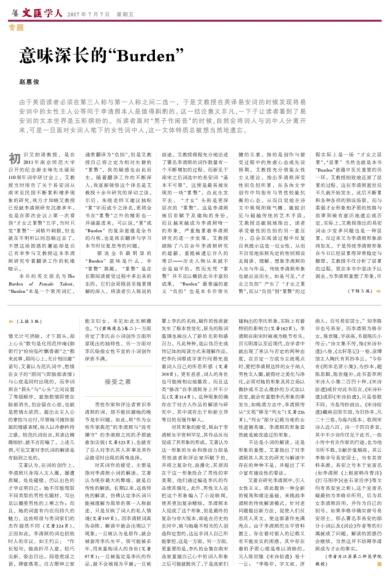赵惠俊
由于英语读者必须在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之间二选一,于是艾教授在英译易安词的时候发现将易安词中的女性主人公等同于李清照本人是值得斟酌的。这一结论意义非凡,一下子让读者看到了易安词的文本世界是五彩缤纷的。当读者面对“男子作闺音”的时候,自然会将词人与词中人分离开来,可是一旦面对女词人笔下的女性词中人,这一文体特质总被想当然地遗忘。
初识艾朗诺教授,是在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纪念唐圭璋先生诞辰110周年词学研讨会上,艾教授当时报告了关于易安词从南宋至民国不断累积增多现象的研究,我方才知晓艾教授已经就李清照研究沉潜多年。也是在那次会议上第一次看到“才女之累赘”五字,当时只觉“累赘”一词格外刺眼,但也就在不明所以间忽略过去了,不想这场困惑的邂逅却是自己有幸参与艾教授这本李清照研究专著翻译工作的机缘暗示。
本书的英文原名为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Burden”本是一个常用词汇,通常翻译为“负担”,但是艾教授自己将之定为相对生僻的“累赘”,我的疑惑也由此而生。随着翻译工作的不断深入,我逐渐领悟这个译名是艾教授十余年研究的深切之谈。尔后,朱刚老师又建议独标“累”字而成今之译名,更将全书在“累赘”之外的精彩也一并涵盖进来。可以说,“累”或“Burden”的复杂意蕴是全书的内核,也是我在翻译与学习本书时反复思考的问题。
要说全书最明显的“Burden”意味是什么,非“累赘”莫属。“累赘”是在长期阅读接受过程中多出来的东西,它们会局限甚至拖累理解的深入,将读者引入陈说的歧途。艾教授理据充分地论述了署名李清照的词作数量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而新见于南宋之后词选中的易安词“基本不可靠”,这便是最易被发现的一块“累赘”。由此生发开去,“才女”头衔是更深层次的“累赘”,这是李清照被后世赋予及建构的身份,而且越来越成为李清照唯一的形象,严重拖累着李清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艾教授破除了八百余年李清照研究的遮蔽,重提被遗忘许久的常识——历史人物从来就不会是扁平的。然而光凭“累赘”并不足以概括此书丰富的成果,“Burden”最普遍的意义“负担”也是本书非常关键的元素,指的是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的焦虑心态或先设预期。艾教授充分借鉴女性主义理论,指出李清照深受性别负担所累,在各体文学创作中均抱有与男性较量抗衡的心态,从而自觉地在诗文中展现阳刚气概、敏锐识见与超越传统的艺术手段。艾教授还敏锐地指出,读者承受着性别负担的另一重压力,总会在阅读过程中反复自我提示这是一位女性,从而不自觉地依照先定的性别预设去阅读、理解、想象李清照的人生与作品,传统李清照形象也就应运而生。如是可见,“才女之负担”产生了“才女之累赘”,而从“负担”到“累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场“才女之层累”,“层累”当然也就是本书“Burden”意蕴中至关重要的另一环。艾教授细致地还原了层累的过程,这在李清照逝世后不久就开始发生,此后不断累积各种各样的预设场景,而与柔弱才女形象相矛盾的性格与故事则被有意识地遗忘或否定。实际上,艾教授指出的易安词由少变多问题也是一种层累,反过来又为李清照形象添砖加瓦,于是传统李清照形象在今日已经层累得异常稳定与醇厚。艾教授不仅分析了层累的过程,更在本书中坚决予以剥去,为李清照重塑了形象,尽
管他笔下的李清照与传统形象差别很大。
综上可见,“累”字至少包容了三种内涵,而无论是李清照还是历代读者,抑或是艾教授,面对性别导致的负担、累赘与层累,无疑都会感受到各自不同的疲惫。故而,读者看到本书译名的时候,若产生“才女很累”的第一反应,其实也不失为这本精彩纷呈的李清照研究的一种正确打开方式。
为了剥离层累,艾教授充分调动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材料,但无论再怎么努力,新材料也很难再被发现,研究工作还是只能围绕着那几篇核心文献展开。材料匮乏是仅以词名者的通例,也是词学研究不得不面临的焦虑或负担。宇文所安曾以“纸牌屋”比喻这种负担:由一张张纸牌搭起的屋子本身就不牢固,更何况只要抽去一张纸牌,整幢房屋就会轰然倒塌。艾教授的研究很好地应对了这种负担,思路主要有二:一、细读现有文献以发现新的理解可能。这突出体现在艾教授对《词论》的解读上。艾教授从开篇“李八郎”故事切入,认为故事中的李八郎就是李清照的象征,他以男歌手身份闯入了属于女性的歌唱圈好比李清照闯入原本属于男性的词体文学世界一样,李八郎最终获得了听众的认可与接受,李清照也期待着男词人能接受她的这次“擅闯”。这种理解角度前人已有尝试,但是艾教授的结论却是前所未闻。或许这个观点臆测成分较大,但无论认可与否,学者都能够获得突破陈规的启示,思考词论与李清照形象其他的可能,这便是有效的研究,比讲来讲去还是在重复证明李清照重视音律声乐要有趣得多。二、将文本置回到鲜活的历史场景去。由于“词别是一家”的传统,词人的作品在解读的时候总会被孤立,似乎游离于作者的生活状态与其他作品之外。但是任何文本都产生于鲜活的环境,文本自身也同样是鲜活的,传统上将词体文本悬置出来的读法容易使文本的阅读弹性部分流失。一旦将文本放归到鲜活环境中,不同的理解可能就会随之出现,文本的美感魅力也会更加夺目。历史书写说到底就是提供一种可能性,今人都是通过前人的记载尝试回到历史真实中,但是任何的记载都是片面的观察,总会带上记叙者个人的立场与情感褒贬,历史真相终究无法完全到达,只能在种种可能中尽量获得全面的认识。这便是艾教授重塑的李清照形象如此鲜活合理的深层原因。
艾教授为李清照取出的最沉重的累赘是对易安词的自传式阅读。由于英语读者必须在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之间二选一,于是艾教授在英译易安词的时候发现将易安词中的女性主人公等同于李清照本人是值得斟酌的。这一结论意义非凡,一下子让读者看到了易安词的文本世界是五彩缤纷的。词人与词中人关系是永恒的词学命题,是词之所以别是一家的关键,二者的分离是词体尤为重要的文体特征,是词体能将人生类型化情感表达得极为狭深绵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读者面对“男子作闺音”的时候,自然会将词人与词中人分离开来,可是一旦面对女词人笔下的女性词中人,这一文体特质总被想当然地遗忘。艾教授敏锐地指出这种阅读方式有违词体文学的写作传统,是一块对女词人来说极度不公平的累赘。其实这块累赘也深深拖累着绝大部分词人,明清以降的读者总会不经意间对词进行自传式解读,可是男词人笔下的男性词中人就一定是词人自己么?类型化情感直至北宋中叶依然是词体表达的绝对主流,即席应歌之曲为何不能吟唱男性对于类型化情绪的理解与表达?难道只有女性才会产生爱情的孤独寂寞与惆怅么?实际上,代言式男性抒情主体的引入是词体容量扩大的第一步,歌词由此被允许走进男性的情感与生活世界。柳永笔下的天涯游子、羁旅秋客更应该承担着这一层词史意义,而非只供爬梳考据柳永的生平履历或妻妾身份。对于后世专业词人来说,这种特征同样强烈,他们应歌制曲的写作场合依然很多,如周邦彦、吴文英者更将填词融汇成一种自我生命方式,从而词中人脱离于词人的文本这种手法始终大量存在。不过柳永以来的专业词人基本上资料匮乏,影像模糊,词作是他们最主要的传世资料,若要钩沉他们的生平,也只能从中下手,这种累赘的产生机制,与艾教授为李清照打抱的不平,是完全一致的。
不仅如此,随着词体雅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词人熟练于用词体记叙自己的生活,表达自我个人情绪,许多词作也就有了明确的本事,词家也越来越喜好为每一阕词作寻找本事。然而是否每一首词就非得具备特定的本事?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大量传统的男女情爱歌词也出现在士大夫词人笔下,这些类型化作品本应没有明确的人事指向,但是探究本事的趣味使得读者总会觉得名公巨儒的艳词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或是早年情事,或是不期艳遇,或是隐秘勾当,这就与伟岸高大的社会形象产生巨大反差,世人对之喜闻乐见,于是围绕这类词作产生的风流韵事就被好言八卦的宋人津津乐道。其实只要仔细琢磨一下就可发现,宋人笔记中那些香艳本事大多不甚可靠,如苏轼应酬张先的《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被说成西湖之上遇白衣美女;初贬黄州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被传言是有怀王氏女子;叶梦得《贺新郎》(睡起流莺语)被认作思念初恋情人仪真;辛弃疾《祝英台近》(宝钗分)与吕婆之女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本事与附着在李清照身上的赵李爱情故事一样,遮蔽了词人与词中人分离的歌词传统,使得士大夫词人也患上了累赘。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便是这种观念的深化,尽管不失为一种文本可能,南宋词人也确实有不少于艳事中寄托个人身世的实践,但过分的索隐会使得词情词意被本事限制,别是一家的情感表达与艺术魅力也就大为削弱,读者需要时刻清醒,词人与词中人分离的传统始终存在。
本书在英语学界的反响甚是热烈,北美汉学界的孙康宜教授和宇文所安教授均撰写书评盛赞本书成就,皆认为本书可能很难被超越。不过宇文所安还是有所指瑕,认为艾教授的研究依然存在性别的负担,艾教授始终不愿放弃李清照身为女性的特殊。宇文所安认为并不能断言李清照在创作时候,特别是在填词的时候,真的就有来自性别上的负担,他甚至希望把累赘全部拔去,仅仅将李清照作为词人而非女词人置身于词苑之中,以此考察易安词中有什么优秀的异质。这种方法论层面的意见似乎很难实现,就是在女权运动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对于杰出女性仍然会有充满敌意乃至抹黑式的议论,女性依然深受性别负担之苦,更别说帝制时代了。于是,阅读易安词,认识李清照,艾教授承受的“性别负担”应该是必须的,也会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尽管宇文所安的建议稍显苛责,但某些意义上也确实点出艾教授最后讨论易安词的两章较之前文有些逊色的原因。艾教授在寻找易安词的词体独创性以及与男词人差异时微微执著,从而淡化了将文本放归鲜活历史空间中的精神,忽视了社会环境与词人生平在其间的影响。李清照毕竟是生活在南北宋之交的词人,她再怎么受性别负担拖累,也不可能不被百年词史经验与时代思潮影响,因此易安词中的特征哪些是基于性别负担的焦虑心态,哪些是填词传统与时代大势的体现,是需要先做辨析的问题,不然就可能会被性别意识所累。艾教授分析的某些易安词特质以及女性形象新变实际上是徽宗朝正在形成与巩固的雅词传统,朝野其他词人为之也有所贡献。比如“改写成句”并不是李清照用来展示自己严肃填词态度的个人性手段,化用唐诗早在晏欧时代就已经是普及的词法,徽宗朝更为大兴,而且花样不断翻新。贺铸与周邦彦以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而奔命不暇闻名,就足以说明严肃的填词心态已经非常普遍,亦表明对晚唐诗的喜好与改造也非李清照性别负担下的专属。只是晚唐诗有秾丽与清艳之分,贺周偏重秾丽,李清照则更好清艳,但在她之前仍有晏幾道导夫先路。而且晏幾道就已爱用与其生平有所关联的人事细节入词,以一时所游兴发应歌式的类型化情绪,即其在《乐府补亡自序》中所谓“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于是将自我影像揉进词体文本形象的塑造,也非李清照独具的匠心,只能是性别意识下的词法选择。此外通过重复一首词的首句对其词进行改写是非常传统的词体唱和方式,李清照《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与《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两阕实际上就是用传统方式唱和自己颇为喜欢的名作,将其视作与男词人的较量当然可以,但是其间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形象却不是李清照本自性别的独创,前代词人在使用这种形式进行词体唱和时,往往就会对女性形象作与传统有别的改变。尽管这些问题丝毫不足以掩盖艾教授对易安词女性特质充满真知灼见的揭示,但也确实表明艾教授在剥离李清照身上的性别累赘时,不经意间也为其所累。
艾教授之累其实也与李清照密切相关,女性主义之外,“词别是一家”是艾教授用来剥离层累的另一种重要理念,该命题最早就是李清照提出的,深刻影响了传统词学基本范式的确立。词体特质与相对独立的词学史使得读词必然要从“词别是一家”入,但是艾教授借此揭示层累形成与剥去累赘以及再次被拖累说明其也会成为词学的负担,并为之增添累赘,词学研究还要从“词别是一家”出,这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是,本书的“Burden”就格外意味深长,其不仅是对八百余年李清照研究的总结与感慨,更触及了超越李清照的词学焦虑,每一位习词者其实都是如此地负重前行。
(作者为《才女之累》中文版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