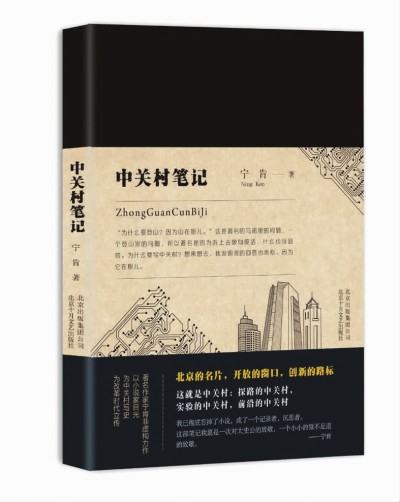宁肯
烈日下曾光着膀子挥汗如雨从三轮车上搬微机的柳传志
联想的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二十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烈日下的柳传志、李勤,这两个日后中关村叱咤风云的人物干脆光了膀子,跟天桥的板爷儿一模一样。那是联想的“爬雪山过草地时期”。
1985年,或1986年,柳传志第一次到长城饭店参加IBM代理会。那时的联想不过是一个刚刚成立两年不到的民营企业,拿到代理资格已非常自豪。柳传志记得自己那时连像样的衣服也没有,穿上了父亲的呢子大衣,先是坐公共汽车,快到长城饭店了下来,打了个出租车,表示是坐车到的。以为有人在门口迎接,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柳传志后悔打了车。到了会议厅,柳传志脱了大衣,里面穿的也是父亲早年的咖啡色西装,包括领带。一切好像不是1980年代而是1930年代,像上海滩。会间有茶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第一次看到点心可以随便吃,柳传志就忍不住了,大吃起来。多少年后回忆起来,柳传志都觉得那点心好吃,不少是没见过的点心。那时完全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收购I BM,更别说做IBM那样世界级的企业的领袖。柳传志记得那时IBM虽有中文环境,但非常不好使,不适应中国的办公环境,那次会上他向 IBM高管推荐联想汉卡,对方极其傲慢,你为他好,你是在帮助他,看上去你倒是在求他。
大公司就是大公司,高山仰止,你能傍上做一个小小的代理就不错了。但柳传志这点好,承认对方的实力,尊重甚至崇敬对方的实力,没二话,但同时也把自 己做好。每一次感到对方的傲慢,柳传志都在心里增加一分决心,一种意志,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
柳传志是一个能够把握大势的人,时代的关口到了什么地方,他会义无反顾且又极审慎地做出抉择。
1983年,出于两个原因,他从中科院计算所调到干部局。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原因,他看到所里的问题,研究出的东西总是束之高阁,于实际毫无用处,事实上非常荒谬,而他又不是一个能改变课题的人。一方面是干部局的原因,上面看他是个人才,有人望,有辩才,准备在仕途上重用。这两种原因柳传志都非常清楚。但更加或越来越清楚的是:仕途不是他的路,时代在发生变化,大势已清晰可见:那就是陈春先走出了科学院,“两通两海”已打破体制,表现出一种活力,且这种底下的活力与上边的活力是一致的,这是大势,虽然充满风险,但是是大势。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也真是太穷,太窘迫了,物质匮乏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人没有尊严,能看到一点转变的机会都会抓住。以住房为例,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在普通市井人心目中是高级人物,但即便像这样的人那时竟然住在自行车棚里,连普通的筒子楼都住不上。自行车棚靠计算所的东墙根儿,房子高仅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被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作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不久这片自行车棚改造的区域已有相当规模,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被进驻这里的人戏称中关村的“东交民巷”。
所以,当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来找他,希望他能回到所里办公司时,两人一拍即合。到1984年底,竟纠集了所里的十几个人,曾茂朝大笔一挥给了二十万元开办费,公司正式开张。所谓开张,没有锣鼓,没搞任何仪式,就是公司可以免费使用计算所的传达室,一间小平房。多少年后———即使是在北京五洲大酒店收购I BM那天,面对全世界的闪光灯,柳传志也没忘记那间幻觉般的小平房。回忆起来像幻觉,当年可不是幻觉,不再是传达室的小平房腾空后,空空荡荡,满是灰尘。公司在灰尘中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而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搬运桌椅,打扫卫生。一通暴土扬尘的忙活之后,大家在三个长条凳上坐下来。
会议第二个议程是公司干什么。既是科技公司,当然要做科技,但这只是方向,二十万元的开办费不可能马上用到科技开发,当务之急是赚钱,如果不赶快挣钱,人吃马喂二十万元很快就会花光,到时散摊子,大家真要再回所里不是件容易事。
大家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虽然具体干什么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知道的,那就是干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先赚了钱再说,有了资本再说。倒卖钢材吧,这样能挣大钱,谁有路子? 还是小商品吧,这样稳妥,占用资金不大。电子表怎么样?对了,旱冰鞋现在很新潮,哎,听说运动裤衩好卖,得了,冰箱彩电现在最缺了,谁有路子?大家议论纷纷,全是这个。柳传志也是如此。他派出精干人员四下打探,寻找商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周密侦察,终于发现,在遥远的江西省的妇联工作的一个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根据柳传志办事稳健缜密、万事都要留一手的一贯做事原则,必须反复叮嘱办事人员,一定要先验货,再给钱。于是属下带着领导的嘱咐,很快来到了江西,惊喜地看到了那批彩电。没错,眼睛看得真真的,赶快汇钱,晚了就让别人抢先了。钱一汇过去彩电却神奇地失踪了。江西妇联的那位大姐原来是个职业骗子,那批展示的彩电是个障眼法,就像“二战”盟军让好莱坞弄了许多假坦克让希特勒在加莱看走眼。二十万元的开办费一下折了十四万元,还剩六万元。这迎头一闷棍太狠了。因为太狠了,也激起了柳传志内心一种莫名的东西,一种很硬的东西。而这东西过去是柳传志缺乏的。柳传志发热的脑袋一下清醒下来,意识到自己的经验是办公室的经验,甚至是科学院的经验,关起门来自己算老到的,出了门差远了。
二十万变六万还给了柳传志一种东西,那就是彻底,既然已输得差不多只剩下条裤衩,那就也没什么再输的,为把窟窿堵上,柳传志亲率员工摇身一变成了卖小商品的二道贩子:带领员工在计算所门口摆摊卖电子表、运动衫。这当然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在外面赔了钱,跑到家门口讨饭,脸往哪儿搁?但柳传志就这样黑着脸干了,是的,我输到家了,但我还在干,这就是彻底。卖电子表挣不了几个钱,但就像一种宣言。从现在起没什么可输的了,那就只有赢了,一点一滴的赢。而且说到底也是堂堂正正,劳动所得,汗水所得,不丢人。
这就是那种很硬的东西,硬中有邪,说到底又邪得非常正。
那时“两通两海”———四通的万润南,信通的金燕静,京海的王洪德,科海的陈庆振都已是中关村的风云人物,产值做到上千万,而柳传志在卖电子表。那时没人知道柳传志,知道一点的也是听说他做赔了,在卖电子表。
公司11个人中有六个人抽烟,工资都不高,抽不起好烟,公司来了客人连根好烟都掏不出,羞于出手。公款买烟招待客人既不恰当,也不自然,比如特具体的是怎么往外掏烟呢?现从抽屉拿吧,不合敬烟的规矩,因为本来敬烟是很私人的,不分你我,拉近关系,你从抽屉里拿算怎么回事,那不就成了公事公办? 要不公款买了,每人口袋里装两包,一包自己的,一包公家的?公司的三个领导商量来商量去———别小看这个细节,很日常的。
戒烟吧,柳传志说,打今儿起我不抽了,说到做到。
柳传志丢掉烟头,踩灭了。从此再没抽。王树和与张祖祥犹豫了一会儿,也灭掉了烟。他们把烟扔到窗外。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连烟都能戒了,还有什么干不了?
曾茂朝没有追究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的责任,这样布下的一支精兵出师不利,让人痛心,但曾茂朝仍认为这是一支精兵。他们卖电子表,就让他们先卖吧,这是一种砥砺,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种子不死,一旦生出来就会强大。
他们卖电子表说明他们不死。
不死就是生———终于,这支精兵迎来了一次机会。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准备配给各家研究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柳传志和后来也是大名鼎鼎的李勤离开菜摊直扑科学院设备司,他们的确不是卖菜的,就像一支军队不是种田的,他们对电脑比对菜敏感得多,有一种天生的敏锐与兴奋,如同将军听到了战争的消息。他们天天跑去游说,争取,磨破嘴皮子,韧劲十足,志在必得。一支能卖菜的精兵还有什么能阻挡他们? 他们拿下了这500台 IBM电脑。
确切地说,是把这500台 IBM 电脑的验收、培训、维修业务揽到手中,也就是说从设备司得到1%的硬件备份,给各个研究所讲课,讲完课后把机器交付给对方,机器以后有了什么问题他们来维修。500台电脑堆满了两间房,场地狭小不能把电脑一字儿排开验机,只能腾出一间房子验机,其余人马搬到另一间办公。一批电脑检验完毕,装箱后搬走,送到各所,再验下一批。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身先士卒,蹬着装满电脑的三轮车吃力地前行,女员工在后面推,挥汗如雨,一趟一趟,是联想的“爬雪山过草地时期”。
多年后计算所的胡锡兰还忘不了那一天往办公室窗下一瞥的情景:联想的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二十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将近2000个包装箱浩浩荡荡,人拉肩扛,烈日下的柳传志、李勤,这两个日后中关村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挥汗如雨,衣服都湿透了,后来干脆光了膀子,跟天桥的板爷儿一模一样。胡锡兰是曾茂朝的妻子,也是计算所的研究员,可贵的是尽管看到了这“感人”的天桥式的场面,不久胡锡兰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柳传志的队伍中。
他们最终也收获了超过他们预期的服务费。项目结束的时候,尽管扣除3%的成本,他们的所剩不超过500台I BM总价的1%,但他们的努力特别是他们的劳动赢得了尊重,他们不光能卖菜,也能像老北京三轮车工人一样卖力气,更能安装电脑、培训技术,维修调试———如果这不是一支精兵还有什么是?由于服务干得出色,科学院最终把原订的服务费1%上涨到7%,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的前身,在1985年赚到了70万元。这是联想的第一桶金,它结束了他们卖菜的决绝的精神练兵时期,“电视机骗局”所密布的阴霾一扫而空,他们终于可以运用知识与名副其实的技术赢得利润了。他们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历史也在此时展现出方向。
完成第一台中文的电脑输入与输出系统的王缉志
那时一代语言学大师王力神志竟还清醒,他握着远方归来的王缉志的手。出国前,王缉志曾经给父亲讲解过文字处理机的工作原理,父亲始终不解。如今父亲已到生命最后时候。讲了半天原理,父亲依然不解,但露出了微笑。带着微笑,父亲走了,如同文明的微笑。
王缉志是北京大学教授、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的四子。虽家学甚深,王缉志却没有子承父业,在十六岁的时候,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是当时班里最小的学生。
既然父亲已是一座高山,那就成为另一种事物。
特别有趣的是,另一种事物,最终,绕了一大圈仍与父亲有关,与语言文字有关,王缉志偶然也是必然地宿命地在另一座山上呼应了父亲。
相对一代语言学大师的父亲,这山不高,却足够特殊。
1979年,当王缉志成为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计算机应用研究室中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时,正值国家刚开始进口微机,王缉志所在的小组也考虑购买一台微机。经同事介绍,王缉志认识了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邝振琨在澳洲有一家叫 DATAMAX的公司,DATAMAX机问世时,IBM PC还没出来。当时邝振琨介绍给王缉志的机器是DATAMAX8000,这台带有文字处理软件WordStar和Mai l Merge(邮件合并)功能的微机,让王缉志大开眼界。
不久,王缉志用DATAMAX8000主机和Tel eVi deo终端,加上一台伊藤忠的打印机,凑成了一套价格相对便宜的微机系统。因为是自己攒的系统,需要自己去做有关的驱动软件,王缉志便开始认真阅读打印机的说明书,突然发现这个打印机的打印头由八根针组成,通过软件指令来控制每一根针的动作,属于由点阵组成图形的打印机。国内当时所用的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而显然,这种针式打印机在操作上要灵活得多,因为从理论上讲这种打印机可以打出用点阵组合成的任意图案或者文字。
王缉志激动异常,血液沸腾,连夜按“可以打出用点阵组合成的任意图案或者文字”,编了一小段程序,然后在打印纸上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这是破天荒的,汉语的天荒,从来没有过!
这个成功让王缉志兴奋不已:能打印七个汉字,就意味着原则上可以打印所有的汉字。也就是说,让电脑处理汉字不再是遥远的事了。
当然,能打印七个汉字,只是解决了原理问题,要让这套微机系统能用汉字处理各种应用,则要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首先,要有汉字字库才能使打印机真正打印汉字。但是,到哪里去找汉字字库呢? 只能自己动手做。
王缉志在用与父亲不同的方式研究文字。
而相同也并非王力期待的。
王缉志从家里拿来了一副围棋,把塑料棋盘布往桌上一铺,动员全小组的人都一起来做,一个人用棋子摆放汉字点阵,另一个人把该字形用16进制数来编码,再有一个人把该数据录入电脑。用这样一种原始的方式进行数字化处理,就像某个阶段你必须用马车拉着火车头,人多势众,哼唷嗨唷。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16点阵字库。
有了汉字字库还不够,如何把汉字文章输入电脑又成为关键。需要汉字输入法,当时国标一级汉字是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放的,如果从工作量来考虑,研制拼音输入法是最容易实现的,王缉志又开始研制拼音输入法。不久一个简单实用的拼音输入法大功告成。但是汉字有许多同音字,用拼音输入法就要解决选字问题,这就需要能够看到拼音输入的汉字。能看到,这非常的关键!这就需要终端,需要屏幕,而这已是准电脑,准PC。
可当时的终端即屏都是英文字符,根本显示不了汉字,而且一般只能显示80×24个英文字符。王缉志有一天终于又想出一个办法:把一个字符M当一个点来用,用屏幕上的16×16个M来组成一个汉字,这样一来,虽然一屏只能显示4个大大的汉字,但总算以一种最原始的落后方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后,王缉志已经完成了第一台中文的电脑输入与输出系统。而他实际应用的第一案例是自动化所里财务科的报表,他把中文财务数据录入电脑,用 dBASEⅡ处理,并打印出第一份整齐的中文报表!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意味着太多东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聂鲁达20世纪70年代来到中国,面对长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许多文明都消失了/你依然存在。但如果不能将汉字数字化,如果最终只能拼音化,拉丁化,这个文明将会真的出现巨大的鸿沟,而鸿沟的另一端意味着什么?
正当王缉志解决数字化中文输入输出系统研发时,时代的变化发生在了他的四周。中关村出现了陈春先创办的华夏硅谷研究所,王洪德的京海公司成立也颇引人注目,四通也即将成立,一批人走到了时代的海边没有停留,义无反顾地脱离陆地,走向远方。有了中文输入输出系统,王缉志忽然发现自己也到了海边,也有脱离传统陆地的可能,但有些犹豫。下海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习惯了陆地,即使站在海边也觉得陆地强大无比,而海洋则充满不确定性,充满危险。
正当这时候,四通公司向他静静地打开了一扇门,时间王缉志记得清清楚楚———1984年5月16日。四通公司在中关村注册成立,同年9月门市开始营业,这一年的六七月份,王缉志进入了 四通公司,任总工程师,成为四通初创时期的主要成员之一。
11月,王缉志正式向冶金部自动化所辞职。
那时无论多小一个单位都是国家的,单位意味着国家,人也是国家的人,辞职意味着真正的“断奶”,王缉志虽然毅然决然,但“心理”上仍然不好受,而且不知道家人怎么看自己,比如母亲,特别是父亲! 没想到父亲不但不反对,还非常开明,挥毫给王缉志写了一首《七律》,如同送给他的“成年礼”:
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这是王缉志没想到的境界,父亲看得更远,不仅向前,也是向后。王缉志把父亲的墨宝拿到琉璃厂荣宝斋裱好,挂在家里的墙上,从此这首充满历史感的诗成了王缉志的座右铭。
1985年初,四通从日本伊藤忠公司引进了1570型彩色打印机。为了公司的生存,王缉志把还没完成的汉字终端的开发暂时放在了一边,带领一个开发小组,为伊藤忠公司的1570型打印机做汉卡。比起汉字终端开发工作,这个工作容易得多,很快就完成了,而就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四通发现大多数购买电脑的单位都是拿电脑配上一台打印机,来打印合同和报告之类的公文。当时购买一套这样的电脑系统要花费近5万元,利润空间可观。鉴于当时的市场情况,如果四通能够开发出一款价格在万元以下的能完成打字和编辑任务的机器,不仅将提升市场上此类产品国有品牌的竞争力,也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
时机成熟,四通公司决定借助日本企业的帮助,重新开发一种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中文文字处理机,打印机芯采用击打式的打印头,这与王缉志的中文输入研究完全一致。
四通的产品开发小组由四个人组成,总体设计的是王缉志,同时王缉志还负责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王缉志的设想是:既然能在WordStar上实现英文编辑功能,那么也一定能在此基础上实现中文编辑功能。那时国内绝大多数人还不习惯什么文字处理,为了市场宣传方便,消除多数人对电脑的天生恐惧心理,王缉志决定给该产品起名叫中文电子打字机,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 MS -2400”:M代表三 井(Mi tsui ),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为了要全方位贴近中国市场的需求,王缉志还拒绝了四通公司有些人提出的在机壳上标外文或者设计一个洋商标的主张。
1986年的3月份,王缉志携开发小组到 日本横滨ALPS公司去进行最后调试工作,计划在日本工作三周,每周七天、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为的就是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快地将机器调试成功。三周很快过去了,但机器仍未调好。
就在这个时候,王缉志接到电话:父亲王力病危。
王缉志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将自己是否回国的决定权交给了母亲,如果母亲让他回国,他会立刻动身。电话无比沉重地通了,王缉志心怦怦跳,祈祷上天保佑父亲,保佑了父亲他也可以在这儿完成重要的工作。母亲接的,上帝保佑父亲还在住院……王缉志先长出了一口气……说实话他已想到葬礼……王缉志突然有个预感,他不用回国了……当然,父亲的病非常重,发病时起先是发烧,大家都以为是感冒,谁知住进医院之后才发现情况严重,是白血病,病情恶化很快。
“我知道你在日本的工作很重要,如果那里的工作离不开你,你就不必回来了,北京有你的弟弟和妹妹在。”母亲说。
王缉志可以暂时不回来了,留在日本把开发工作做完。
以工作事业为重,是王家的传统,从小王缉志就记得父亲和母亲不会轻易因身体不适而请假,一般小病都会坚持上班,而王缉志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不管是肚子痛还是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母亲都是要求尽量要坚持上学。根据这一残酷的原则,王缉志留在日本继续做开发,是必然也是自然的选择。就这样,王缉志带着对父亲强烈的挂念,与全组人员昼夜奋战,终于调试成功。
4月12日,四通MS-2400中文电子打字机诞生了,打印机飞快地打出了一页页清晰的中文样张,机头发出的嗡嗡的蜂鸣声像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王缉志作为研制了中国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的专家,一夜成名。在四通的发展史上,MS系列文字处理机是举足轻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产品,它同时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办公自动化设备领域最早的民族品牌之一。这个产品从推出之日起,一直销售了10余年。截至1996年底,四通MS系列中英文文字处理机累计销售近30万台,销售收入突破30亿元人民币,让中国的 IT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了自己的名牌。
当同事沉浸在欢乐之中,王缉志回到北京,直接从机场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父亲住在那里。那时一代语言学大师王力神志竟还清醒,他握着远方归来的王缉志的手。出国前,王缉志曾经给父亲讲解过文字处理机的工作原理,父亲始终不解,想象不出,王缉志本来想搬一台电脑到父亲面前边演示边讲解,一来开发工作太忙,二来想到反正很快就会有产品出来,等产品问世后拿着产品再讲岂不更好,谁知道此时产品真的开发完成的时候,父亲已到生命最后时候。讲了半天原理,父亲依然不解,但露出了微笑。
带着微笑,父亲走了,如同文明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