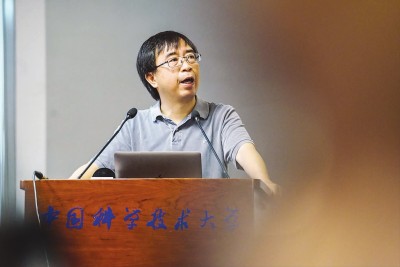■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去年8月16日,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腾空而起;十个月后,“墨子号”首次实现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的成果,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审稿人认为该成果是“兼具潜在实际现实应用和基础科学研究重要性的重大技术突破”,断言“将在学术界和广大社会公众中产生非常巨大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实验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96年,留学奥地利的潘建伟第一次见到导师蔡林格教授时就说:“我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实验室。”此后,他在这条梦想之路上,一步步踏实前进。
2001年,31岁的潘建伟回国组建实验室。2002年,他萌生了把卫星送上天,利用天地之间的链路做量子科学实验的想法,“当时听起来像一个天方夜谭,欧洲、美国都没有类似的项目”。就在许多专家还心存疑惑时,中科院支持了他这个近似疯狂的想法。
潘建伟常说,创新不能总跟在别人后面,要敢做没人做过的事情。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完成前期科学铺垫后,从2011年开始,潘建伟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微小卫星中心、上海光机所、成都光电院等单位,迅速立项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星地量子通信这一领域,我国从一开始起跑,就站在了欧洲和美国的前面。
然而,“墨子号”研制过程中,一路碰到了许多坎坷。就在去年6月底卫星进场前,一个信标光激光器突然被发现能量下降,光机所、中科大、技物所的科研人员和大家一起讨论,最终联合解决了问题。“墨子号”刚进入轨道,外太空的环境比预计恶劣,对卫星的光学系统很快产生了影响。眼看实验要做不成了,整个团队又在一起调整卫星参数,把卫星“救”了回来——最后,卫星数据的各项参数比原来好了10倍,原本准备两年完成的实验只用两个月就完成了。相关论文投稿到《科学》杂志,仅十几天就接受,并且以封面文章发表———这是前所未有的。
成果发表后,不少外媒评论,中国真正走到了量子通信的国际领导地位。而在“墨子号”发射之后,加拿大也为量子卫星立项,欧洲、日本、印度等地的项目也相继启动。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体记者,潘建伟难掩内心的激动:“这次,中国真正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到来。”
不过,潘建伟深知,这种优势要保持起来并非易事。当年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一开始也只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几十个人,后来短时间内就从全国汇聚起了上万人参与。现在,量子科技碰到的情况十分类似。一开始做前沿研究,只需一两百人就能做起来;做卫星可能上千人就好;但今后再发展,就需要更多资源和人才的汇入。
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量子科技是一棵竹子,过去一直在泥土中酝酿破土,现在则到了破土而出的时候。人们常说“雨后春笋”,它将很快进入拔节猛长的阶段。如果它被栽在花盆里,最多长成一个盆景,如果长在山林中,则可能发展成一片竹林。
眼下,国家正酝酿实施量子信息领域的重大科技项目,并将筹建国家实验室。在上海,量子科学作为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各方也在联合推进。潘建伟希望,未来可以探索一种更好的机制,举全国之力,更有效地协同创新——造出中国的量子计算机,发展中国的量子通信产业,让我国真正成为未来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