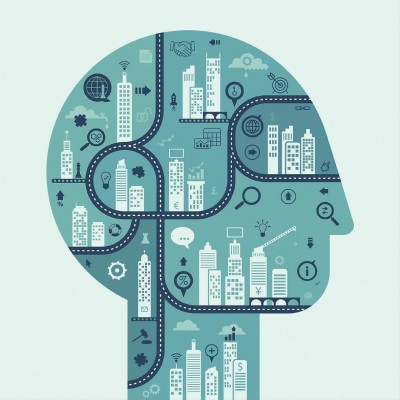■本报记者 徐晶卉
《哈佛商业评论》 杂志的一年订阅权,目前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全年电子版,收费150元;第二个选项是全年电子版加印刷版套餐,售价320元。你会选择购买哪个?
70%以上参与测试的消费者会选择150元的电子版。
如果此时又多出一个选项:印刷版全年售价320元,在三个选项当中,你又会购买哪一个? 测试结果显示,选择购买全年电子版加印刷版套餐的消费者,原来是20%左右,如今上升到接近60%。
换句话说,有接近40%的消费者改变了主意——本来打算只花150元的人,最后心甘情愿花了320元,还窃喜自己捡到了便宜。
大多数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我们在做购买决策时,我们相信自己是在根据自己所能掌握的信息,作出最正确的决策。但在 《哈佛商业评论》 的这个例子中,很少有消费者会进一步追问:商家为什么会给你“印刷版全年售价320元”这第三个选择? 它看上去根本没有吸引力。
本期论坛,我们邀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金立印教授和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和大家一起聊聊营销中的“读心术”。
人不是想像中那么理性
记者:商家在营销过程中充分利用心理学原理进行营销,这在商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在研究层面,经济学或营销学与心理学的结合,有哪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孙时进:营销背后是人的行为决策,行为决策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出色的营销,是把这些理论融会运用到商业实践中去。
上世纪7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司马贺 (Herbert A.Simon),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学家,在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的结合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学术上影响很大。
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卡尼曼 (Kahneman) 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带给人们一个新的理论——前景理论。瑞典皇家科学院称,卡尼曼的获奖原因是“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中国,奚恺元教授有一本书叫做《别做正常的傻瓜》,融合了诺贝尔奖得主及其他学者数十年的研究成果,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帮助人们发现决策中的误区。人们发现,经济学看起来是理性的决策,其实不然,人不是想像中那么理性,同一件事的不同问法,会对行为决策产生不同的作用。
从心理学角度看,如果要改变人们对价值的认知,就可以通过改变信息刺激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认知。其实,很多时候人们不仅仅是对事物的“价值本身的强度”做出反应,而是对“事物价值”与其所处环境的相对差异做出反应。从这个角度理解,在市场当中要想改变消费者对某个产品的态度,除了努力改进产品品质之外,另一条路径,就是改变与产品相关联的信息环境,通过对照来彰显产品价值。
金立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
记者:能否谈谈您印象比较深的营销学与心理学结合的企业案例?
金立印:前几年有个创业公司利用互联网概念,推出了一款体检产品。这个产品的潜在用户,是那些具有感染某种病毒风险的特殊人群。从健康角度出发,这些感染高危人群非常有必要做定期的检查,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人群又不太愿意去医院及时做检查。创业公司推出的产品,不需要用户自己跑去医院,只要客户在网上下订单,24小时内就会收到产品,产品包装内有一根消毒棒和采血针,将血采集到带有二维码的采血盒里,然后通知客服来取,24小时内就可以在网站上查询结果和基本治疗建议。相比去医院做检查,要方便不知多少。
但问题是,这款产品此前在中国市场从未推出过,如何定价才能吸引这一群体购买? 一番决策后,定价出来了,公司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成本定价的方法,而是先定出了一个1799元的“专家版”,上市不久,公司又针对价格相对敏感的消费者,推出一款1299元的“增强版”。这两款产品在功能上完全一样,差别仅仅是购买增强版 (少支付500元) 的顾客,需要等待48小时才能查询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销售,效果很理想。
试想一下,如果这家公司一开始先推出1299元的“增强版”,然后再推出24小时得到检测结果的“专家版”,这款产品的营销效果还会好吗? 很可能不会。推出两款产品的顺序不同、价格不同,“高开低走”,导致消费者的心理感受有很大差异。
记者:这里面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
金立印: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信息输入不同,引起不同的心理感受差异。就像同一个逻辑的事实,我们用不同的“信息表述”去呈现这个事实,会带来信息接收者的不同反应。
消费决策取决于信息输入
记者: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研究一代人的心理学,是否有一些影响消费行为决策的共性特征?
孙时进:我最近有一个基础研究课题,叫 《不同成长年代个体的心理贫穷感与策略、风险偏好的关系》,我认为,除了人类共同的特征,人有个体差异和年代差异,比如对于金钱的拥有,并非所有的人都一样。童年对于人的一生影响重大,童年的生活状态,可以预测未来的决策行为和消费行为。
从更大的层面上,要预测一个国家消费行为的发展趋势,与这个国家的过去有关,研究者必须读懂整整几代人的群体生活状态。如果一个人从小很贫穷,长大之后虽然可能会拥有很多金钱,但行为决策还是会受童年影响,省吃俭用,严重影响消费行为。如果一个人从小很富足,长大之后对于金钱,就可能不会那么看重。在电视剧中,有贪官豪宅中冰箱、墙和床上铺了满满的钱,让人瞠目结舌,有人会问,这些人那么有钱了,他为什么不舍得花? 如果从心理学视角来分析,当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这个人对于钱的贪婪欲望,往往不是理性所能解释的,更不是理智所能控制的,这就是所谓“心理贫穷”。如果不透过深层心理治疗,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
极度贪婪是一种病态现象,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极度挥霍,在我们这里,表现为一些人对奢侈品的狂热消费。中国消费者在国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金额令人咋舌,从消费心理学角度出发,这一现象该怎么解释? 在我看来,童年的不安全感、经济的匮乏,都会给一个人此后的决策行为带来深刻的影响。奢侈品,包包、手表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些人买东西“只求最贵不求最好”,因为买到最贵的,意味着可以换来人们对自己的尊重,而尊严是无价的。这样看,这些人“暴买”奢侈品也就能够理解了。
再比如“快决策”。一种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童年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在这种不可控的环境下长大后,这个人在决策时,会忽视长期价值的要素,而偏向于做出短期内“尽快变现”的决定。所以,现在有不少商家在经营上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并不完全是道德问题,也有一定的心理问题。
记者:能不能举个例子,商家在营销过程中,因为输出信息的细微调整,会对消费者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
金立印:举个例子,如果你正在节食瘦身,有一块肉摆在你面前,一种说法是“这块肉有80%是瘦肉”,另外一种说法是“这块肉有20%是肥肉”,虽然这两种说法说的是同一个事实,但哪种情况下你更可能吃这块肉? 一定是第一种。
再举个例子。你准备接受一个手术,一个医生告诉你:“做这台手术有90%的存活率”,另外一个医生告诉你: “这台手术有10%的死亡率”,哪种描述下你更可能选择去做这个手术? 一定是前者,但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消费决策,看似是理性思维、谨慎权衡的结果,但其实不然,包括很多重要的决策,比如买车、买房子、选基金,诸如此类,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毫不相关的外部信息的影响,也会受到信息表述的影响。有些时候,越是重要的决策,这种“毫不相关外部信息”的影响会被放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决策,其实也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困难,只要我们尝试基于某些被科学证实了的行为决策理论来改变决策任务的信息输入,就可以影响到人们最后的选择。
记者:也就是说,通过改变信息输入,其实也可以起到改变消费者对价值的认知的作用?
金立印:是的。庄子秋水篇里面有一段话:“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意思就是,按照物与物之间的差别来看,顺着各种物体大的一面去观察,便会认为物体是大的,那么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是大的;顺着各种物体小的一面去观察,便会认为物体是小的,那么万物没有什么不是小的。这后面还有两句话,大致意思是,我们拿世间万物和天地相比,世间万物都像小米粒;拿世间万物和毫毛末端相比,世间万物都像山岳那样大。这种观点认为,大小、好坏、优劣都是相对的概念。同样道理,价值也是相对的。
由于价值是相对概念,所以从心理学角度看,如果要改变人们对价值的认知,就可以通过改变信息刺激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认知。其实,很多时候人们不仅仅是对事物的“价值本身的强度”做出反应,而是对“事物价值”与其所处环境的相对差异做出反应。从这个角度理解,在市场当中要想改变消费者对某个产品的态度,除了努力改进产品品质之外,另一条路径,就是改变与产品相关联的信息环境,通过对照来彰显产品价值。
记者:如何有效设计信息环境,从而实现对人们行为的有益干预?
金立印:著名的心理学家库特莱文 (Kurt Lewin) 说过:“我们不能改变一个人,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人的环境,来改变这个人的行为”。对此我的理解是,改变环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改变信息环境。
有家欧洲的创业公司开发出一款提醒人们节约用电的节能灯,它有个名字叫“花瓣灯”。灯上装有传感器,传感器能自动监测家里面所有电器的实时用电量——如果用电高过某个设定的峰值,灯的“花瓣”就会“枯萎”,人们就会意识到家里现在用电太高了,就会及时把不必要的灯或其他电器关掉。当用电量降到峰值以下,“花瓣”就会重新开放……从心理学角度来谈,“花瓣灯”的设计者应该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他精心设置了一个人为的信息环境,成功地从心理层面干预了人们的行为。它的热销,就是一个证明。
如果说,按照企业所期望的方向去改变消费者行为是营销的核心工作之一的话,那么,营销管理者就需要对人们认知信息以及作出反应的内在心理机制有深刻理解。
不能把心理学变成操纵手段
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与一代人的心理完整、健康、尊严、自在等有关,所谓自在,就是宠辱不惊,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这样的消费市场,利用人们的心理因素设局、投机这类行为,才会逐步减少。
孙时进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记者:您刚才提到一点,人们在做决策时可能受到毫不相关的信息影响?
金立印:这种例子非常多。1997年6月,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美国超市里面有一个叫做MARS的品牌巧克力卖断货了,持续了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它既没有做促销打折,也没有因竞争对手而退出市场。后来发现,在那期间有一条与巧克力毫不相关的热点新闻——火星探测计划成功,“MARS”成为媒体上的热点词汇。人们看到火星的新闻之后,MARS 这个词占据了他们的心智,以至于他们去超市购物时,会下意识地购买MARS品牌的巧克力。当一段时间过后,这条新闻降温、不再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时,MARS巧克力的销量就恢复了正常。这个案例要证明的是,市场上有些现象虽说并不能用“理性”来解释,但仔细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看似不理性的背后,其实也有“理性”规则可以遵循。
孙时进:在营销心理学上,这个叫做催眠销售,简单来说是指“无意识的东西也会影响你”。通过反复地推送、放大一些信息来影响人的购买决策。比如在电影里植入广告,其实就是希望观众产生一些无意识的联想,从而影响到消费决策。在商业上,这种营销手段,本质上就是利用心理学来操控人,卖一些对方并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果正常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就会不知不觉受它的影响,做出一些看起来理性、其实愚蠢的决策。这是不可取的。
记者:许多时候,人的决策行为也会受到情感的驱动,对此营销心理学如何解释?
金立印:曾经有机构做过这样一个测试:某慈善组织搞了一个保护大熊猫的捐赠活动,用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募捐信息。第一个版本上,主办方只是用文字询问人们为了保护1、2、3、4只大熊猫,愿意分别捐多少钱;第二个版本上,分别呈现了1、2、3、4只熊猫的图片,然后问人们分别愿意捐多少钱。
最终结果你大概也能猜到,看到图片后人们愿意捐更多的钱。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在做决定时候,有两个决策系统,一个可以称作“感性决策之路”,另一个可以叫作“理性决策之路”。当给人们看熊猫图片时,启动了他们大脑中的感性决策路径,这时候人们对具体的数字就不那么敏感了,感觉熊猫很可爱,那么就多捐点。
在营销实践中,这也可以解释市场中很多品牌经常会做情感类型广告的一个原因。消费者看到某个品牌的时候,如果总是基于“感性决策之路”来认知和评价品牌,感觉很好的话,就可能对价格没那么敏感了。
记者:商业通过一些心理学的方式来操控人的决策,有时候这看起来不太道德?
孙时进:有些人学心理学,是为了操纵商业。刚才说的心理催眠学,号称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把任何东西推荐给任何人,这种缺德的事情是挺麻烦的,类似于“麻醉抢劫”。
但从营销学与心理学的结合趋势来说,如今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变化:个性化,尊重为上,而不是操纵、恐吓、诱导,营销会回到越来越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我认为,随着时代进步,把心理学变成一种操纵手段,这种现象会逐渐消失,没有道德的心理学操控,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反过来说,教育对催生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至关重要。我们掌握一门学科,是为了有自我觉察,学完之后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再被别人操控。心理学的作用是拿出来剖析,找到自己的本质,同时找到奸商的本质。
从营销心理学透视下一代人的消费观
记者:在中国,心理学与营销学的融合现状如何?
孙时进:现在很多心理学家会在理论的指导下,将心理学原理应用到商学院的实践中去。而从心理学发展的本身来看,也越来越提倡应用实践。我很赞成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的界限,打破方法与业界的界限来研究问题。
大数据时代,数据可以解释很多人的行为概率和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但现在很多研究数据的人不懂心理学,而很多懂心理学的人在忙着收集数据,所以合作很重要,因为没有思想和理论的数据,本身毫无价值。这时候,研究心理学的视角就特别重要,从心理学视角去指导消费和理解市场,通过大数据的方法,极具意义。
记者:通过心理学研究,您来预测一下,未来一代“00后”、“10后”的消费模式转变。
孙时进:上一代父辈讲财务自由,重点是财务;现在这一代讲财务自由,重点在于自由;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是要的是意义。
现在很多企业在转型的十字路口,很多老板都会认为“90后”、“00后”说跳槽就跳槽,觉得他们没有责任感,反而认为自尊比加薪更加重要。其实,下一代反而能看清上一代看不清的东西,比如上一代员工可能认为,领导找员工陪喝酒是看得起他们,但现在的孩子觉得这是不尊重他们。他们会为自己认为有意思的事情披荆斩棘,却不肯做认为不属于他们职责的任何事。企业领导者若是对这些细微变化缺少认知和理解,未来的管理会越来越困难。
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与一代人的心理完整、健康、尊严、自在等有关,所谓自在,就是宠辱不惊,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这样的消费市场,利用人们的心理因素设局、投机这类行为,才会逐步减少。
就像现在“共享”概念的出现,说明年轻一代对于拥有不再那么敏感。从心理学上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虽然有滞后性,但正常情况,下一代会更加自在,可能会选择不要钱,而去做一些觉得更有意义的事。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未来的消费也会越来越个性化,下一代消费者会去选择真正喜欢的东西。
本版头像 陈韶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