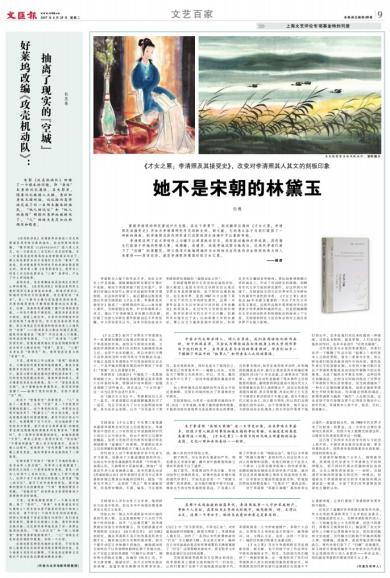杜庆春
电影 《攻壳机动队》 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身体”本身的记忆属性。在电影里,随着记忆被植入大脑,意识和身体无缝对接,记忆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一具陌生躯体的殖民,“他人的记忆”和“他人的感情”都轻而易举地被继承了,“人”的诞生史是如此的偶然和随意。
《攻壳机动队》 的漫画和动画在二次元的领域里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经过好莱坞的改编,“数字朋克 (cyberpunk)”进入真人次元,这一方面是从二次元到三次元的穿越,另一方面则是在好莱坞的全球营销娱乐诉求下,强大的电影资本对日本流行文化的“拿来”和改造。我对漫画原作和押井守的动画电影是陌生的,面对真人版 《攻壳机动队》,我所关心的是三次元的电影回应“二维”美学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虚构未来,首先要解决的是给观众呈现什么样的景观,《攻壳机动队》 的做法是利用大量的现实元素去营造未来感,制造亦真亦幻、跨越时空和次元的混搭感。我们看到的“未来”,是一个摩天大楼与贫民窟并存的世界,实景的建筑被电子数码绘图叠加出未来感,光、幻影、色斑和色晕消解了整个世界的真实感,一切似乎都是不确定的。建筑本身没有东方特征,画面上的汉字、日语字母和韩语字母当然隐喻了地理空间,但只是浅表的符号混搭,真正体现出空间属性和特征的是人工建筑的“密度”———指向东亚大都会的逼仄氛围。建筑的密集性在“现实”中对应着人口规模,然而在这部电影里,“人口”或者说“人群”是消失的,密集的建筑物以及由此构建的城市成为戏中人物活动的“布景”,甚至,“人物”本身也是“景观化”的,被吸收在这庞大的“布景”中。
于是,虚构的工作让渡给“景观”制造技术。大都会的交通系统和地面建筑,都成为高度符号化的空间,酒吧黑市、贫民窟街头、餐厅、高层公寓外墙密集的空调机诸多细节,它们终究仅仅是概念性的,徒有审美的意义。西方想象的东亚未来景观,是一个“密密匝匝的空城”,这个高概念的影像背后,现实其实被消解了———抽离了现实的场景,自然只能是“空”的。
在这个“密集而空”的景观里,“人”也成了一道景观。主角“少佐”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机器人,这个角色的设定,非常安全且保守地沿用了“机器与人”的古老主题,也是此类题材通行的情理逻辑。原作中的少佐名叫素子,电影模糊了这个名字,完全地抹掉了角色的东方背景。影片的女主角斯嘉丽·约翰逊曾 出演过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里的“黑寡妇”,有一张辨识度极高的脸孔,由她来扮演“少佐”,事实上是把一张西方面孔“安全地”“不带违和感地”植入东方的景观中,在这个植入过程中,被戏称为“当代梦露”的约翰逊戴上黑色发套,她的形象本身也就构成了一种景观。
这部电影不纠结于“拥有了灵魂的机器人是否会和人类为敌”,科学和人性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的背景,曾是一对恋人的两个人类的记忆,被植入了两个机器人,这两个有了自我意识的机器人背负着“他人的记忆”,展开了对坏老板的复仇。影片叙事的推动力全然建构在“个体”情感的需求与觉醒,“密集而空”的世界成为忧郁阴暗的个体情感诉求的场域。
于是,这部电影就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除了“意识”,“身体”本身难道没有记忆属性么? 历史的本质不就是时间在个体身上的沉淀、留下印记? 个体作为时间的承载体,两两之间难道不存在匹配与冲突吗?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随着记忆被植入大脑,意识和身体无缝对接,记忆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一具陌生躯体的殖民,“他人的记忆”和“他人的感情”都轻而易举地被继承了,“人”的诞生史是如此的偶然和随意,如同一个幻觉。
这部电影里特别有趣的幻觉是,不同母语的人能使用各自的母语实现无障碍的交流,这个场景与其用科幻解释,不如说是这部跨文化娱乐产品的自我沉醉感的精彩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