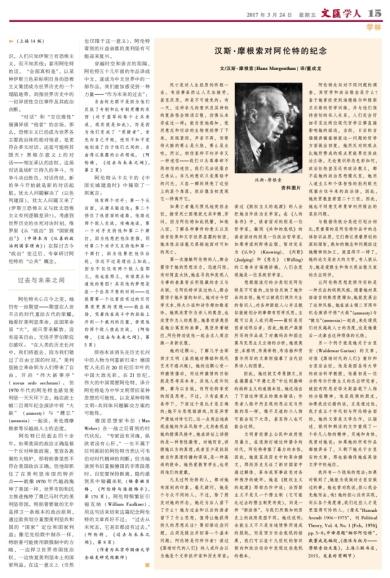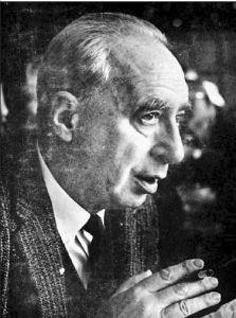文/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译/董成龙
死亡是对人生经历的终极一击。有些事虽然让人无法接受,甚至厌恶,却是不可避免的:有一天,这种非凡的意识及其神秘的复杂性会烟消云散,彷佛从未存在过一样;能自觉地感知、使用意志和行动的生物突然停了下来,双眼紧闭,声音不再,而等待大脑的要么是火烧,要么是虫咬。所以,相信某种不朽并非又一种迷信——我们口头尊奉却不再相信的迷信。我们无法说服自己承认:非凡的意识只是黑暗中的闪光,只在一瞬间照亮了这世上的某个角落,然后像当初发现它一样离开它。
如果亡者毫无预兆地突然去世,接受死亡困境就尤其辛酸、苦闷。因为阿伦特如此机警,知晓人世,了解各种事件的意义以及语言世界和文字世界显露的秘密,她本性应该毫无畏缩地面对可知的死亡。
第一次接触阿伦特的人,都会震惊于她的思想活力,迅速闪烁,有时简直太快,她在寻找和发现人与事的表象背后所隐藏的含义与关联。与阿伦特详谈过的人,都会震惊于她丰富的知识。她对古今哲学文本、伟大小说和诗作都如数家珍。她既欣赏作为诗人的奥登,也欣赏作为人的奥登。她喜欢讲奥登在她公寓里的故事,奥登身着破烂,阿伦特劝说他一起去名人商店换一身新衣服。
她的这颗心,了解几乎全部西方文明(虽然她对舞蹈和现代艺术不感兴趣),她的这颗心受一种激情推动,而这种激情的目标就是思考其本身。其他人或许玩牌、赛马以自娱,而阿伦特享受的则是思考。不过,只有在重大条件下,下面这个类比才是正确的:她不与思想做游戏,而是异常严肃地对待它们。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她的作品风格中,尤其表现在她的授课风格中。她在讲坛上讲授的是一种智性激情,对她而言,讲授她以为的真理,或者至少是批驳被当作真理传播的谬误,是一种高尚的使命。她热爱教育学生,也受到他们的爱戴。
凡见过阿伦特的人,都对她有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不过,除了朋友对她的怀念,她还为后人留下了什么?她为过去和以后的读者留下了什么思想,值得让她获得持久的思想关注?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提出并回答一个基本问题:阿伦特是何种作者?读过《黑暗时代的人们》的人或许会以为她是个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读过《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人会把她当作政治史学家;在《人的条件》中,读者面对的则是一位哲学家。翻阅《共和的危机》的读者面对的则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如果考虑到即将出版、暂时定名为《认知》(Knowing)、《判断》(Judging)和《意志》(Willing)的三卷本吉福德讲稿,人们会发现她是一位系统哲学家。
想根据流行的分类划定阿伦特是不可能的,这恰恰反映了她作品的本性。她可以被我们视作天生的智识人,对各种困扰人心并且貌似能被划分的事都有哲学反思。主题可以是人或问题——最好是用前者说明后者。因此,她就卢森堡所写的作品成了对魏玛共和国左翼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分析。她就奥登、本雅明、布莱希特、布洛赫和贾雷尔所写的文章则描摹了当代世界诗人的图景。
因此,她还就艾希曼撰文,旨在揭露在“平庸之恶”中达到巅峰的纳粹主义的道德本性。她还指出了下面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作恶者人格中所呈现的恶必定与所做的恶一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能会犯下大恶,甚至伟人也可能会这样。
文明曾经禁止公民和政府使用暴力,在逐渐打破这种禁令的时代,阿伦特考察了暴力的本性。因此,她就某段历史中的革命撰文,那段历史见证了新旧国家中通过解体、革命或军事政变对各种秩序的破坏。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那部杰作中说:法西斯主义不是又一个僭主制(它可能比过去的僭主制更有效),而是一种“新政体”,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上的政府类型不同。她还说明:全能主义不只是当地情势所造成的脱轨,而是西方社会危机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智识倾向和政治运动中发现这些危机的根本。
阿伦特走向对不同问题的调查,其哲学和政治缘由是什么?鉴于她曾经受到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哲学训练,并与他们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人们定会仔细寻觅这两位现代哲学巨擘直接影响她的踪迹。当然,日后的吉福德讲稿能够就这一问题的哲学方面做出回复。她所反对的观点比她所赞成的观点更能界定其政治立场。无论意识形态色彩如何,政治狂热甚至还有政治教义,都不在她的政治思想模式里。她用人道主义和个体智性的批判眼光观察古往今来的政治场。因此,她欣赏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因此,她也不同意艾希曼审判所提出的某些问题。
与根据传统分类进行划分相比,更重要的是阿伦特作品中的总体智识品质。它们都记录着原创的深刻理智。熟知的概念和问题经过她精神的加工,就显得不一样了。她的论文是宏大的文学。有人就认为,她是爱默生和伟大英法散文家的杰出同伴。
让阿伦特思想发挥作用的是一种杰出的讽刺风格。随着她对英语语言的熟悉度增加,她就发展出了这种风格。她在波士顿二百周年纪念演讲中将“大赦”(amnesty)与“健忘”(amnesia)一起谈,来处理我们对反越战人士的态度,这是她最后一次拿出这种得体的礼物。
另一个例子就是她关于古里安(Waldemar Gurian)的文章,时值《黑暗时代的人们》重印和古里安去世。他是美国圣母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他最初是一位分析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研究者,被控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分裂精神。他是我俩的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是通过他,我才在五十年代初与阿伦特会面的。她的文章是文学杰作,以描述、锐利和鲜活的文字重现了一个非凡人物的精神、灵魂和身体。我曾对她说:如果她的所有作品都被弄丢了,只剩下她关于古里安的文章,那也能确保她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
我怀有一个隐秘的想法:如果时候到了,她能为我做对古里安做过的事。她也曾对我说,担心我会先她而去。唉!她的担心没有实现,而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些人才是更值得可怜的人。(原文“Hannah Arendt 1906-1975”,刊Political Theory, Vol. 4, No. 1 [Feb., 1976], pp. 5-8;中译原题“缅怀阿伦特”,载董成龙编校,《德性与权力——摩根索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5。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