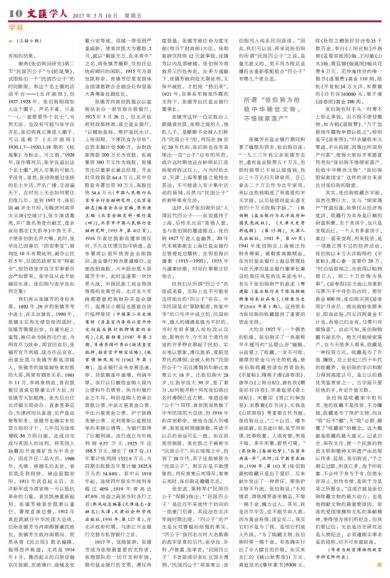章宏伟
我们可以说,张伯驹名列所谓“民国四公子”之说,是毫无意义的,更不用为削足适履而去重新搭配组合“四公子”有哪几个更合适。
出身贵胄门第的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大玩家”,琴棋书画诗词戏曲样样精通,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家、诗家等身份于一身。一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尤其是他从30岁开始爱好收藏,发展到嗜书画成癖,醉心于中国古代字画名迹,一掷千金,买下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等,并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记蓄藏书画名迹117件。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名迹,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捐赠,化私为公,令人肃然起敬。张伯驹的捐献加上故宫博物院购置,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等22件张伯驹收藏过的书画名迹,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收藏(故宫博物院编《捐献大家张伯驹》与故宫博物院、项城市政协编《故宫博物院收藏张伯驹捐献作品中国古代书画作品集》,均只收录了20件书画,还有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卷与元俞和临赵孟頫书《常清静经》轴2件都没有收录)。
随着近年来收藏热的勃然而兴,作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的张伯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张伯驹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现在的研究论说,颇有演绎的成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以非为是,混淆历史真相,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张伯驹的本来面目。
“近代四公子”还是“民国四公子”?
现在几乎所有言说张伯驹者,一开篇总是说:张伯驹“早岁名列‘民国四公子’”。一些工具书,如《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中国艺术家辞典·现代第三分册》《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辞典》《吉林省百科全书·下册》《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历代藏书家辞典》都说张伯驹与张学良、袁寒云、溥侗并称四公子。
乍一听:出身豪门,多才多艺,潇洒风流,具传奇色彩,应该没有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学界对于“民国四公子”之说,没有提出异议,都认可:上个世纪20年代初,“民国四公子”之说在南方出现,并逐渐被京津沪上层社会公认。“在民国上层社会中,素有四公子之说。这些公子皆出身名门,或为军阀政要之子,或为商界名流之后,或为清朝皇族宗室。但究竟所指何人,却说法各异,而这些公子们的事业发展、兴趣爱好与个人命运,也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张晨怡《教科书里没有的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对“民国四公子”都有谁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出至少有四种说法(马勇《民国四公子的政治情怀》,《新江淮文史》2013年第2期):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驹、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马勇认为,“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做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忱。”
王忠和甚至专门编著《民国四公子》一书(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该书《写在前面》说:“末代皇帝溥仪之族兄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均为民国初年京津沪上层社会颇具传奇色彩之豪门子弟,人称‘四大公子’或‘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亦有他本,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三人各本皆榜上有名,卢永祥之子小嘉、张謇之子孝若、张之洞之子张权亦曾列于其中。本书所取是依民国年间社会最为通行之说法。‘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
我这里征引的张晨怡、马勇、王忠和三位的论说只是例举而已,还有不少书籍文章都持类似说法,可知“民国四公子”说的影响之大。大家都把“民国四公子”当成了客观事实,从来没有怀疑过是否真的存在过“民国四公子”,如果真有“民国四公子”之说,又是由何人在何时、何地先说出来,或先用文字记下来,在报刊书籍上刊登出来的?之后都有哪些书报在继续散布?大家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但没有一位学者告诉我们这提法出自何处。
好在近十几年来数据库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民国期刊库、申报库等海量数据为我们搜捡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直到笔者写作本文的时候,我没有查到民国时期关于“民国四公子”的消息。笔者所见最早关于“民国四公子”的文字出自张伯驹手笔,他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所著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说:“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之后,张伯驹在《也算“奇缘”——我与陈毅元帅》中又提及:“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宣传部所属文教部门统被冲击,我的帽子为封建余孽、反动学术权威、四公子之一、康生点名的大右派、陈大炮(造反派称陈毅元帅为陈大炮)的死党,尤以因写《春游琐谈》笔记,称为春游社反党集团,全国皆有组织。”
或许当时确实有“四公子”的说法,但绝不是所谓的“民国四公子”,因为张伯驹自言“人谓近代四公子”,此言“近代”而非“民国”,这不只是两字之差,意义非比寻常。
先来看“四公子”说法产生的时间。学界的认定和张伯驹的自言,显然有着巨大的时间差。
学界认定“‘民国四公子’的提法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固然是为了避开袁克文1931年死于天津,但我们也要分析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无可能形成这种说法。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河南项城阎楼,其生父是张家老六张锦芳。张家老五张镇芳是张家唯一考中进士做官之人,遗憾的是两个子女先后夭折。1905年,7岁的张伯驹被过继给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来到天津。张伯驹自述:“八岁至十四岁住天津,在家中私塾上学,十四岁曾入法政学堂,肄业,十五岁随父去河南开封,十七岁在北京,十八岁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肄业,二十岁毕业,二十一岁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后改任长江巡阅使署咨议(在蚌埠)。后安徽督军倪嗣冲病故,二十三岁去职,二十四岁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参谋,四省经略使署咨议(皆名誉职),二十六岁任陕西省军署参议(在西安),二十八岁去职,二十九至三十七岁任盐业银行经理(在上海、南京)……”(张伯驹潘素文献整理编辑委员会编《回忆张伯驹》,《张伯驹自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7-198页)可以说,直到1927年,张伯驹的生活不说波澜不惊,也是乏善可陈,总之很平淡。张伯驹30岁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逐渐将重心转移到自己钟爱的传统艺术上,他自述:“我三十岁开始学书法,三十岁开始学诗词,三十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三十一岁开始学京剧。”当然,也从这时开始,张伯驹徜徉花街柳巷,得识潘妃(后改名素),惊为天人,才有了后面的美满姻缘。这些都基于张伯驹子继父业,任职盐业银行,有经济后盾、有职
有闲的结果。
谢燕《张伯驹词研究》第二节“民国四公子”与《蛇尾集》,试图给出一个“民国四公子”的时间断限,和这个名士圈的活动平台——《北洋画报》,但1927、1928年,张伯驹刚刚加入这个圈子,声名不著,只是“一心一意想要作个名士”,当然无法、也没有可能与张学良齐名,张伯驹真正算进入圈子,可以连载于《北洋画报》1930.1.7—1930.3.18期的《蛇尾集》为标志,可之前,“1928年,张作霖死后,张学良退出这个名士圈”,两人交集的可能几乎没有。显然,张伯驹能过张扬的名士生活,声名广播,交游遍天下,在时间上无论如何要往后推几年。直到1937年,张伯驹40岁生日时,为赈济河南旱灾义演《空城计》,张主演诸葛亮,并广邀名角登台献艺,连余叔岩都在《失街亭》中饰王平,才使张伯驹名声大噪。此时,张学良已因善后“西安事变”,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5年,后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开始幽居生涯。张伯驹与张学良如何交集?
我们再从张镇芳的身份来看。1892年,29岁的张镇芳考中进士,在北京做官。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时,张镇芳微服出京,在潼关赶上銮驾,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为两宫尽力效命。两宫回京后,张镇芳官升两级,成为四品京官。而袁世凯与张镇芳都是项城人,张镇芳的姐姐嫁给袁世凯的大哥,两家有姻亲关系。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故,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张镇芳大加提携。张先后出任北洋银元局会办、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长芦盐运使等职务。张镇芳也确实有经营方面的才干,几年间为国库增收56万两白银,还成功完成与英国人的谈判,将英国人独霸的开滦煤矿改为中英合办,因此升任二品大员。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去世,袁世凯受到排挤,被迫退隐安阳。1911年武昌起义后,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张镇芳被袁世凯委以重任,署理直隶总督。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命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主政河南期间,贸然杀害《民立报》数名编辑,搞得怨声载道;尤其是1914年1月,豫西起义的白朗穿越京汉铁路,攻破潢川、商城及安徽六安等地,项城一带受到严重威胁,使袁世凯大为震怒,2月,就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之名,将张镇芳撤职,仅担任总统府顾问的闲职。1915年为袁世凯称帝,张镇芳任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
张镇芳向袁世凯提议以盐税结余办一家官商合股银行,1915年3月26日,经北洋政府财政部核准,成立盐业银行,“以辅助盐商,维护盐民生计,上裕国税,下便民食为宗旨”,总资本额计划500万,由财政部拨款200万元为官股,私商集资300万元作为商股。张镇芳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开业时仅收股款64.4万元,其中官股盐务署出资10万元,商股出资54.4万元(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席长庚主编《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四)》,北京市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1993年,第402页)。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举国反对,不久在忧愤交加中病逝。盐务署将以前所拨资金全部抽回,盐业银行转为普通银行,全部改招商股,大半股份落入张镇芳手中。此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难得的发展空间,北洋各大军阀都愿意把钱财存在盐业银行,连溥仪小朝廷也愿意在该行抵押借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清皇室内务府以宫中珍宝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的合同》,《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另请参阅叶秀云《逊清皇室抵押、拍卖宫中财宝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盐业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存、贷款额逐年递增,利润丰厚。该行以巨额资金购入国内公债和外币债券,执当时银行业之牛耳。特别是购入的善后借款公债、中法五厘美金公债、中比六厘美金公债、沪宁铁路英镑公债、克利甫斯以盐税担保的英镑公债等,为银行取得了巨额利润。该行成立当年纯利润9.57万元,1925年达188.5万元,增长了18.7倍,11年累计纯利润1332.9万元,为同期实收股东年累计额3825.8万元的34.84%。其中从1918年起,连续四年股东年纯利率超过40%,1919年曾高达47.6%,效益之高居当时各行之首(郭凤岐总编纂《天津通志·金融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在北洋政府时期,与浙江兴业银行交替为私营银行之首。
1917年,张勋复辟,张镇芳成为张勋最重要的支持者,张勋部队的一切开支和军饷,都用盐业银行的支票,溥仪再度登基,张镇芳被任命为度支部(相当于财政部)大臣。张勋复辟仅持续12天就事败,张镇芳以内乱罪被捕。张伯驹为营救其父四处奔走,在多方通融下,张镇芳被判处无期徒刑,又保外就医,才把他“捞出来”。1921年,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张镇芳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
张镇芳这样一位在政治上跟随袁世凯、张勋之流的人,他的儿子,是断断不会被人们称作“民国公子”的。何况在20世纪20年代初,张伯驹也没有表现出一位“公子”应有的风范,或许这时期他还在蚌埠长江巡阅使府咨议任上,与当时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繁盛之地相去甚远,不可能进入官少集中活动的场域,自然与“民国公子”的称呼难有交涉。
这样,似乎张伯驹所说“人谓近代四公子……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差强人意,也与张伯驹的履迹接近。张伯驹1927年进入金融界,20年代末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在那里得识潘素(1915—1992),1935年与潘素结婚,时间行事都正好相合。
但我们从所谓“四公子”的组成来看,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组合的“四公子”存在。中华民国是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声中成立的,民国初年,旗人的境遇是极为不好的,当时有很多旗人纷纷改从汉姓,影响至今,今天对于清代帝室的许多秽言都起于民初。实在难以想象,溥仪族弟、爱新觉罗氏的溥侗,会被人称作“民国四公子”?而且溥侗的年龄比袁寒云大18岁,比张伯驹大28岁,比张学良大30岁,差了辈分,如何能并称?何况张伯驹出名时溥侗已近古稀,难道还称“公子”?同样,袁世凯虽然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1916年的洪宪称帝,使他为国人所唾弃,袁家是树倒猢狲散,其诸子以后的命运可见一斑。如在洪宪帝制前,袁世凯之子被称为“民国公子”,尚在情理之中,但到了20年代,其子还能被称为“民国公子”,则实在是不敢想象的。何况袁寒云死得早,袁寒云死时,张伯驹还籍籍无名。
张宏武、梁转琴《“民国四公子”探颐》指出:“‘民国四公子’是近百年来流传于坊间的一组豪门后裔,其说法在北洋军阀时期出现。‘四公子’的产生是反对曹锟而结盟的果实。‘四公子’指四名当时大名鼎鼎的政军显贵的后代:张学良、孙科、卢筱嘉、张孝若。‘民国四公子’不含前清宗亲红豆馆主溥侗,‘民国四公子’将袁寒云、张伯驹列入纯系民间误读。”因此,我们可以说,再来说张伯驹的所谓“民国四公子”之说,是毫无意义的,更不用为削足适履而去重新搭配组合“四公子”有哪几个更合适。
所谓“张伯驹为抢收中华稀世文物,不惜倾家荡产”
张镇芳在盐业银行期间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张伯驹自述:“一九三三年我父亲张镇芳去世,遗有盐业股票五十万元,但那时股票已不如以前值钱,我以三十万元归天津家用,自己拿去二十万元作为北平家用。我以这些钱购进了我喜爱的宋元字画,以后陆续向盐业透支到四十万元收购字画。”(张伯驹《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页)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汪伪特务绑架,被勒索高额赎金。在当时盐业银行上海总管理处与在天津的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凤苞的往来函电中,有关于张伯驹财产的叙述(邢建榕《盐业银行关于张伯驹被绑案的来往函电》,《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1期)。这些资本为张伯驹的收藏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大约在1927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张伯驹买了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从而爱上了收藏,一发不可收。雄厚的资金与历史的机遇,使张伯驹收藏到诸如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卷》、宋蔡襄《自书诗》、元钱选《山居图卷》等重要古代书画。张伯驹自云:“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张伯驹:《春游纪梦》,“丛碧书画录·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张伯驹最初收藏只是出于爱好,后来就生发出了一种责任,要保护文物不外流。张伯驹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为了购藏文物,张伯驹时常一掷千金,有些确实付出了令人瞠目的价格,如买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1万元、黄庭坚的《摹怀素书》5000元,收《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5千数百金,李白《上阳台帖》并唐寅《孟蜀官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共花费6万元,范仲淹传世的唯一楷书《道服赞》黄金110两,陆机《平复帖》4万大洋,宋蔡襄的《自书诗》45000元,展子虔《游春图》黄金200两。
张伯驹有时手头一时筹不上那么多钱,而不得不借贷鬻物,如为购《道服赞》,“乃于急景残年鬻物举债以收之”;特别是买《游春图》,“时余屡收宋元霁迹,手头拮据,因售出所居房产付款”,使得大家似乎更愿意用类似“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抢收中华稀世文物”、“张伯驹毁家救国宝”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对张伯驹的敬意。
其实,张伯驹收藏古字画,虽然花费巨大,实与“倾家荡产”背道而驰,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讲,收藏行为本身是巨额的财富积聚。至于卖房子,也只是变现而已。一个人有多套房子,拿出一套来变现,用来投资,是一项最正常不过的经济活动。张伯驹以4万大洋购得的《平复帖》,溥心畬一直要价20万,“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以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游春图》在玉池山房掌柜马霁川手中待价而沽时,要价黄金800两,张伯驹买到《游春图》“月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马霁川亦颇悔恚”。由此可知,张伯驹购藏书画名作,绝无可能倾家荡产。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收藏是一种投资方式,收藏是为了升值、赚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收藏界,张伯驹的学识和眼力得到高度认可,是公认的最优秀鉴赏家之一,古字画只要经他的手,肯定升值无数。
张伯驹是收藏家中的另类,他的收藏不是投资,不为赚钱,收藏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收”而不“藏”,凡“收”必捐,颠覆了“收藏家”的概念。这大概就是收藏的最大意义:记录历史、保存文化,使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由此得以传承、延续。张伯驹说:“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这或许就是张伯驹收藏文物的最大动力,也是他捐献文物的最重要原因。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使得他为我们所纪念。但我们要记住: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人物纪念,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切不可有意拔高。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