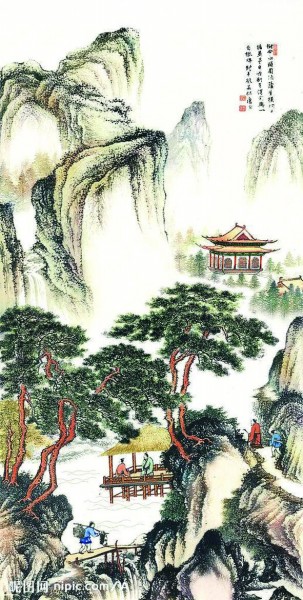■胡中行
本报2月20日在头版、二版刊登了记者采访复旦大学《诗铎》丛刊执行主编、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胡中行先生的特稿《让古典诗词深入国人血脉》。报道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著名作家肖复兴先生看后特意给本报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在充分认同胡先生诸多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并希望与胡先生作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报特邀胡中行先生撰稿,就肖复兴先生提出需要“答疑解惑”的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两位热爱古典诗词、文学功底深厚的作家、学者,坦诚相见,互为唱和,实乃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段佳话也。
——编 者
刚刚看了由《文汇读书周报》记者转来的肖复兴先生的信,非常高兴。肖先生对我关于诗词的基本观点的认同,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查了一下,他长我两岁,我自然得“兄事之”了。
肖兄目光如炬,在信中提到了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那就是“现代新名词和俗语俚语入古典诗词的写作,该如何把握其中的度。”这的确涉及到了今人写古典诗词的一个核心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一味地在古典的意境和名物词汇中打转,显然是一种没出息的表现。在古典诗词教学的实践中,我是比较注意纠正这一倾向的。比如有位学员写了这样一首诗:“雪紧卷帘愁不停,审妆温酒怅无铃。年来常负中庭月,却把心思诉寸屏。”我的评语是:“古意太浓,今意不足。沪上暖冬,何来雪紧?寸屏之说,新而确当。”这位学员辩解说,她写的是一位农民工女性,是代人立言的。我批评说,你写的是早已死去的不知哪个年代的仕女,哪有现代农民工女性的影子!我肯定这首诗的唯一一点,就是“寸屏”两个字。用它来指代手机,倒是有点新意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寸屏”这个词汇与古典诗词意境之间存在的协调性,而我认为这个协调性可能就是“度”之所在。
另有一位学员写了一首题为“南极”的诗:“白雪皑皑留影哉,企鹅户户是双胎。父母月子共同坐,养育婴儿一起来。”看了这样的诗,我真有点生气了,于是批评道:“古诗不同于民歌,还是要尽量雅一些。否则诗词社就变成民歌社了!其实民歌也不好写,打油诗同样如此,但与近体诗有很大差别,不能混在一起的。纵观诗友们的作品,雅多不通,俗多油滑,关键还是基础问题。”
这里提出了一个基础问题,实践经验告诉我,要一个没有古典文学基础的人去写古典诗词,的确是勉为其难的。有感于此,我才会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背诵是根,理解是苗,创作是花,做人是果”的学诗途径。有了雄厚的古典文学基础,那么无论是民歌入诗,还是“打油”入诗,都能做到得心应手,写出上佳的诗词来。就如肖兄在信中举出的那些例子,尽管用的是俗词俚语,但照样格律工整,诗味盎然,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种“玩文字于股掌之间”的功夫,非启功、荒芜、聂绀弩、流沙河诸先生何能及此?尽管如此,他们在写这类作品时,也绝不是信马由缰、轻率随意的,而是十分注意这些词语与总体风格的协调性。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白,这些有点“出格”的作品,都是诸位先生的偶一为之,他们并不总是以此类风格示人的,这里仅举两例来领略他们“正宗”的一面:
启功《金台》
金台闲客漫扶藜,
岁岁莺花费品题。
故苑人稀红寂寞,
平芜春晚绿凄迷。
觚棱委地鸦空噪,
华表干云鹤不栖。
最爱李公桥畔路,
黄尘未到凤城西。
聂绀弩《柬周婆》
龙江打水虎林樵,
龙虎风云一担挑。
邈矣双飞梁上燕,
苍然一树雪中蕉。
大风背草穿荒径,
细雨推车上小桥。
老始风流君莫笑,
好诗端在夕阳锹。
我以为,为了保持古典诗词创作的传承性,保持古典诗词特有的韵致,对现代词语入诗词还是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如果大量使用白话系统的词汇,势必会与本属文言系统的诗词意境发生冲突,从而破坏语词和诗境的协调性。
我曾经写过一首《菩萨蛮》,原稿是这样的:“浅霜薄雾来天地,清风冷月秋无际。径仄桂香浓,篱疏枫影重。 床头听漏滴,床下寒蛩泣。举烛读南华,披衣夜煮茶。”后来有位学生问我,老师您家真有蟋蟀吗?这个问题对我触动很大,既而自问:闹钟能叫漏滴吗?真是举着蜡烛读书吗?但是改成“床头听滴答”、“开灯读南华”行不行呢?于是我把床头床下两句换成“遥听声淅沥,遥看星明洁。”化用了欧阳修《秋声赋》的句子。再把“举烛”改成“坐起”。我觉得,这样的调整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里实际上又牵涉到一个“语典”的问题。所谓“语典”,就是有出处、有来历的词语。如果我们把一首诗比作一座建筑,那么词语便是构成这座建筑的建材。建材的优劣、建材的风格,直接关乎整座建筑的质量。由此可见词语的重要性。
古人写诗,十分注重所用词语的出处,几乎是“无一字无来历”。试以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中的一首诗为例,对杜甫诗歌中的词语作一番例举性的探源。
题张氏隐居二首之一
春山无伴独相求,
伐木丁丁山更幽。
涧道余寒历冰雪,
石门斜日到林丘。
不贪夜识金银气,
远害朝看麋鹿游。
乘兴杳然迷出处,
对君疑是泛虚舟。
第一句,春山,庾信诗:春山百鸟啼;无伴,刘琨诗:独生无伴;相求,《周易》:同气相求。
第二句,伐木丁丁,《诗经》: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山更幽,南朝王籍诗:鸟鸣山更幽。
第三句,涧道,王台卿诗:飞梁通涧道;余寒,朱记室诗:叠夜抱余寒;冰雪,《世说》:范逵投陶侃宿,于时冰雪积日。
第四句,石门,谢灵运诗:披云卧石门。斜日,阴铿诗:翠柳将斜日。林丘,谢惠连诗:落雪洒林丘。
第五句,不贪,《左传》: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金银气,《史记》:败军场,破国之墟,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
第六句,远害,《晏子春秋》:可谓能远害矣;麋鹿游,《史记》:麋鹿游于朝。
第七句,乘兴,《世说》:王徽之曰:我本乘兴而行;杳然,《庄子》:杳然难言之矣;迷出处,沈佺期诗:此中迷出处。
第八句,对君,庾信诗:对君俗人眼;虚舟,《庄子》: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褊心之人不怒。虚舟,谓空无所系。
古人如此讲究,今人又如何呢?我认为,今人写古典诗词,如果完全不用语典,通篇的大白话,即使协韵合律,也是出不了古典诗词的韵味的。要知道,诗词的韵味比格律更为重要,而韵味主要又是通过词语体现出来的。词语的雅俗、文野、高下,直接决定着作品的韵味。所以,我还是不主张在古典诗词的创作中大量使用过于现代、过于白话的词语。
或许有朋友会说,古人写诗,在引经据典的同时,不也间或会用一些当时的新词语吗?事实的确如此,从诗经到乐府,从唐诗到宋词,新词语在诗歌中的出现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有一点必须明白,那些变化都是发生在当时的文言框架之内,“无伤大雅”的;今人写诗,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不加选择地大量使用白话新词,就会与原来的格律诗的语言系统发生矛盾,形成“文白杂糅”,从而破坏诗歌的总体协调性和原有的美感。
或许有朋友会担心,用语典写诗,会不会影响当代诗词的创造性,从而使其失去生命力。我认为这种担心并无必要,因为继承与发展从来就是不矛盾的,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正是脱胎于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而毛泽东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则一字不差地来自于李贺。这些青出于蓝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当然,今人写古典诗词,绝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一味地求古,须知假古董是不值钱的。问题还是在于协调性这个“度”。麻烦的是,这个“度”的把握是因人而异,无法统一的。各人只能讲各人的理解,而绝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我在这里也只能讲讲我自己理解和把握的“度”。我认为,现代词语局部有序地融入古典诗词的创作,是有利于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的。但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体裁上也要有个区别对待。比如五律尚高古,七律尚厚重,我在创作时便比较注重用语典,较少掺入现代词语。例:
谒东坡墓
青史印痕深,文归天下心。
松云围一子,寺塔对三琛。
寻梦孤坟哭,凌风赤壁吟。
焚香埒诸葛,两地柏森森。
而绝句尤其是七绝则比较崇尚轻灵流动,这就成了我尝试新词语和旧诗境之间的协调性的“试验田”。去年和今年的春节写的几首七绝,就是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结果。
年味
行人低首色匆匆,
爆竹无声道路空。
莫谓而今年味少,
无穷年味手机中。
财神
财神昨夜到家来,
瓜果烟糖满烛台。
吓得财神转身走,
财神也怕“喝咖啡”。
丁酉春节
祈福声声声不停,
唯将鞭炮换弦铃。
一条微信千人转,
未见真情见爆屏。
如前所说,我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只是我自己的一得之见,并不成熟,随时准备修正和改变的。期盼肖兄及同道们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