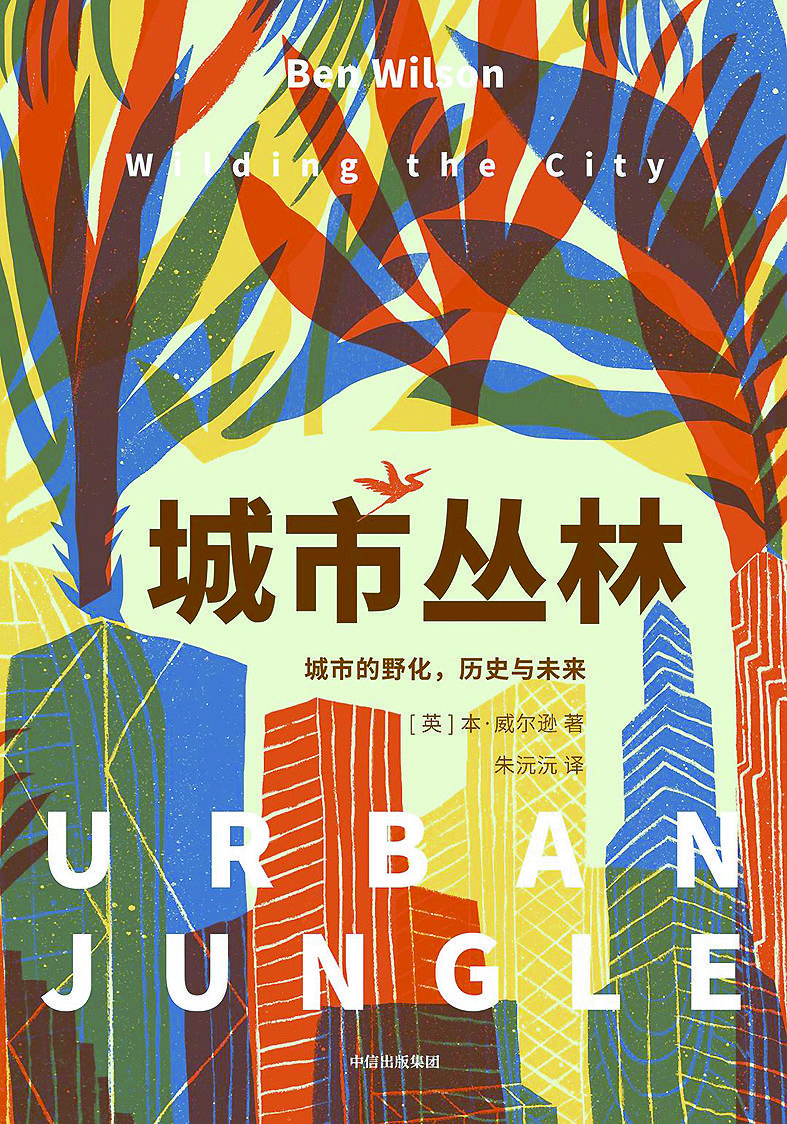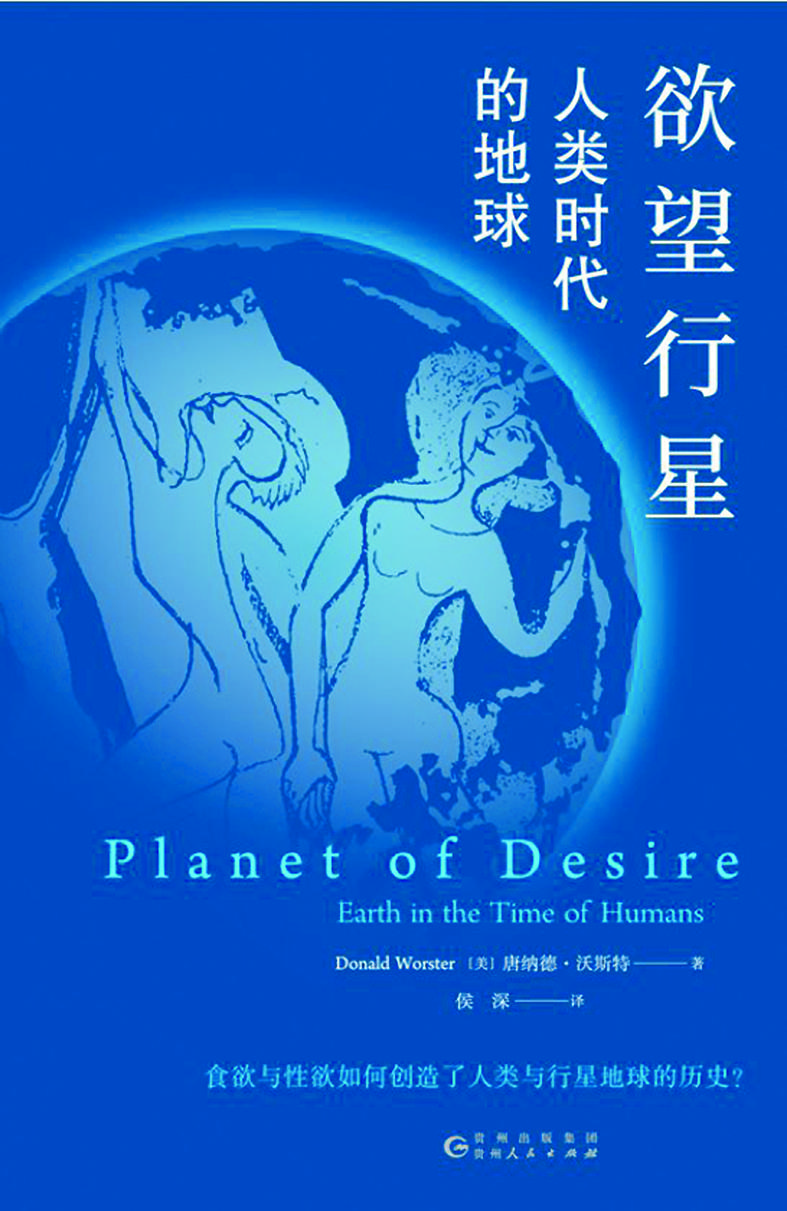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11-03 第28133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让自然与人类一样进入城市,让地球生生不息
《亲生命性》 [美]爱德华·威尔逊 著 张帆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出版
■ 胡明峰人类从自然中演化而来,又与自然渐行渐远,时至今日,坚硬的墙壁和虚幻的数字将人类目光遮蔽,当我们回头张望来处,高更从南太平洋荒岛丛林中发出的质询依然回响在每个尚有决心凝神以思的人耳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亲生命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倾向
1961年3月12日,当爱德华·威尔逊站在苏里南沿海地区一个阿拉瓦克人村庄里眺望远处的沙滩和森林时,他感受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情思。“每一次回忆起这一瞬间,我都会变得越发伤感,直到最后,我的这种情感转变成了理性的推测。”20多年后,威尔逊用“亲生命性”(Biophilia)来总结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感,并用这个希腊语单词作为自己新书(1984年出版)的名字。这是他为回答高更三问提供的线索。
作为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生物学家、科学家,先后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达尔文的继承人”,爱德华·威尔逊认为,亲生命性“即人类与生俱来关注生命及生命过程的倾向”。探索生命,并在生命中寻找归属感,这是人类心智发展过程中一个深刻而又复杂的环节。对于个体来说,对自己身体和其他有机体的好奇,带有一种天然的欢欣;人们喜欢新奇的生命形式,并赞叹于生命的多样性,甚至渴望某天能够遇见地外生命。这种对生命的欣喜和渴望,这种亲近生命的倾向,“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编织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引导我们走过200万年的时空,塑造了今天的人类大脑,因而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亲生命性》中,爱德华·威尔逊认为,人类潜意识中寻求与其他生命的联系、关注自然和其他生命形式并与之联系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有遗传基础。当早期人类(直立人)在非洲稀树草原上开始早期生活时,当时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塑造了人类大脑,并刻入了人类基因:那时他们所处的是面积广阔、零星分布有小树林和孤树的稀树草原,而“双足直立的行走方式和自由摆动的手臂能够让人类的祖先适应开阔的热带稀树草原,让他们更好地利用草原上丰富的果实、根茎和猎物”。这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便利,而且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学标准,促使人类进行艺术创作、景观设计,即使在以后文明更为发达的时候,人类也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生境中形成的这种与自然的依存关系。
然而,城市和城市文明严重割裂了这一纽带。如今,借助机器(技术)的力量,人类的生产、生活更加便捷;同样,借助机器的力量,人类已将荒野(不能被利用或控制的自然)推向无边黑暗,成为恐怖和令人厌恶之地。人类把亲近自然的本性抛诸脑后,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奔向与自然对立的机器。自然作为生存场所和精神家园,本来是无尽富饶的宝藏之地,如今被城市和技术文明撕碎蹂躏,成为“完全是外在的事物,它既没有名字,也没有边界,被视为一股必须与之对抗、必须哄骗、必须设法利用的力量”。这不仅对于自然来说是一种灾难,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大脑在“自然与机器、森林与城市、天然与人造这一系列两极对立的概念之间不断拉扯,迫使我们不懈地寻求答案”。这或许就是高更感到惶惑、连续发问的根源,也是为什么人类总是怀有一种冲破樊笼、复归自然的冲动。
让自然与人类一样进入城市
40年后,另一位威尔逊也在自己的著作《城市丛林》中关心荒野的命运,确切地说,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年轻的新秀历史学家,本·威尔逊的视野较为开阔,思想也更活跃。他不认为城市赶走了自然,他在城市的“边缘”发现了“异常繁茂的自然形态”:“城市中凌乱的地方,比如路面的缝隙、建筑工地、被遗忘的沼泽和破破烂烂的荒地,是大自然能自由支配、肆意生长的地方。”
这40年里,世界相对和平,但地球并不太平。高度发展的全球化和城市化,使人们原先更具地方性和差异性的经济、生活、文化、社会高度趋同,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大潮漫卷,人口爆炸并且主要集中于空间和资源均有限的大城市,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崩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但却看起来与百姓生活并非切身相关。一切都是资本的错,悲观的人们说;一切都有待于技术的进步来解决,乐观的人们说。
然而,本·威尔逊提醒我们,当务之急不仅是要认识到城市中绿色植被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城市居民和环境之间长期而复杂的关系。城市不再是一个封闭和防御的政治、军事堡垒,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们需要不断去发现这种长期而复杂的关联。气候变化是城市问题,因此,它需要城市提供解决方案。本·威尔逊用到了跟爱德华·威尔逊相同的概念来推进问题的解决:“21世纪的挑战是城市第一次成为亲生命的城市,而且城市要积极鼓励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系统的功能。”
如今,城市已经取代稀树草原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场景,城市建设成为时代风貌的重要一章。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以及接踵而来的更大繁荣,城市对物质资源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能源、养分和消费品通过管道、电线和长距离供应链进口,再通过下水道和垃圾填埋场输出,大部分由城市造成的生态破坏被掩盖了,被忽视了。
尽管人们在建筑工程上创造了奇迹,但对城市的设计根本无法应对更高的气温、不可预测的风暴和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工程技术不足以拯救城市居民,相反,焦点已经转移到所谓“绿色基础设施”上。本·威尔逊呼吁人们:“城市迫切需要重新自然化的河流、修复的湿地、恢复的潮汐湿地,以及城市森林的阴凉树冠,来抵御气候危机。如果你想象未来的城市,不要太在意智能技术、飞行汽车和摩天大楼,而要多想想层层叠叠的叶饰、平屋顶上的农场、粗糙的城市草地,以及茂密的森林。”
纵观历史,城市的密集度使之富有生产力,能够营利,并适宜社交。密集度对环境也很有益,当我们停止向外扩张,就给自然留下了更多土地。如果我们更多地步行、骑自行车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会减少燃烧石油。人口稠密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远离自然生活,在地球上,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野生动物融入城市组织。
让自然与人类一样进入城市,重建“城市化的自然”而不仅是“城市中的自然”;让自然在城市环境中促发新的生物多样性,并与人类一道安居乐业,而不只是把生态建设当做一种装点、炫耀和变相的控制自然的企图。这不仅是城市人类的生存之道,也是一种更彻底的“亲生命性”的态度。
这生生不息的行星地球
环境史学的开山鼻祖和领军人物之一唐纳德·沃斯特,同样是在一片海滩上开启了自己新的行星史之思。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奥纳海滩,是太平洋海岸线上一片时而惊涛裂岸、时而安谧可爱的海滩,人迹罕至,但来自海洋与沙滩的浓郁味道,却诉说着那里有机生命的丰裕。与爱德华·威尔逊所感受到的一样,沃斯特说:“当我们人类生命沿此海滨漫步,会生出一种回归感,一种对这个宇宙间我们唯一家园的归属感。”因为地球生命的源头在海洋,而行星史正是要深入过去,探究这个星球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应强大动力,这种动力为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类生命设定条件。
与爱德华·威尔逊倡议回归自然、亲近生命不同,与本·威尔逊试图在城市中悦纳自然、促发生命多样性也不同,沃斯特认为,自然一直就在人类自身之中。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执教期间,研读了中国古籍,从《孟子》中引用的告子所说“食色性也”得到启发,认为人的两种基本欲望就是食欲和色欲。人类以欲望与万物相连、互动,因而也一直身在自然之中——这样一种简捷、直接的物质性史观或许令人难于理解,但却也是一种对于生命的特别见地。在沃斯特看来,是生命的存活和延续,即食、色这两种“内在自然”和“人类自然”的驱动,人类才实现了人类史上两次最伟大的跃迁,即在1.2万年前,从采集到农业的跃迁;在公元1500年前后,从农业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跃迁。
沃斯特在新作《欲望行星》中,专章讨论了中国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作为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核心观念之一,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是一场发展观的深刻革命,更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沃斯特寄希望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西方后现代以来的技术批判相结合,推动一种关于共存的新伦理,并赋予人们去实践这种伦理的新知识,同时提出关于人类生活目的的新问题。如果说地球因为人类而变得像今天这么糟糕(事实并非全然如此),那原因也是对自然的无知,无论是对人类的内在自然还是外在自然。
沃斯特并非认为人类自然中只有食色之欲:“在人类自身中间存在着自然,或者说多种自然的错综生长,内生的仁爱之性与内生的享受安乐、繁衍子孙的欲望形影相随。”其中也包括爱德华·威尔逊的“亲生命性”,还有“某种对抗我们的劫掠以保护地球行星的欲望”。“在人类演化出许多改变环境的方式的同时,我们可能仍然为一种内在自然所指引,去关怀、保护、适应、忍耐,同时寻找解决办法。”沃斯特如是说。
因此还有希望。沃斯特自称《欲望行星》“并不是一部殷切的乐观主义著作,但它是一部充满希望的著作”。希望何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和人口均已接近极限的今天,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可能不再是如何找到新土地或者新资源,而是我们希望保持在什么样的文明水平上。什么样的可持续性是我们想要的?在有限的行星上追求无限的增长是理性的吗?荀子说:欲、物“相持而长”,所以必须用礼加以节制。儒家经典《大学》也说:“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在沃斯特的语境里,“得”就是得到一种人类自然的全新体现。他期待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追求较节制的繁荣、较好的环境保护的生活方式,毕竟“智人物种从来没有停止对新生活方式的发明”。
“变化源自物质条件,在这个人类获取优势地位的时代中,它意味着人口、食物体系和性习惯的改变,意味着以新的方式寻找食物和繁衍后代。”在未来的世纪中,个体伦理将会变化,物质环境将会变化,而我们将会面对一个不那么拥挤的地球,将会拥有一种更为广阔的共同利益的观念,行星地球将会因之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此而言,沃斯特与爱德华·威尔逊等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家不同,他对于人类控制自然的前景抱有预期,这基于他对人性自然的深刻揭示,也是地球行星生生不息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