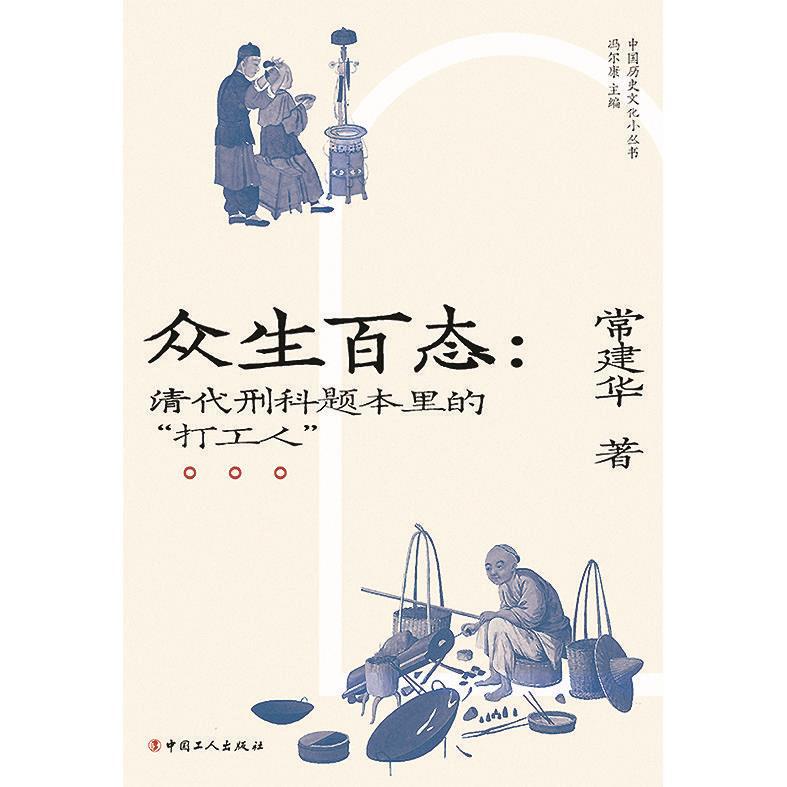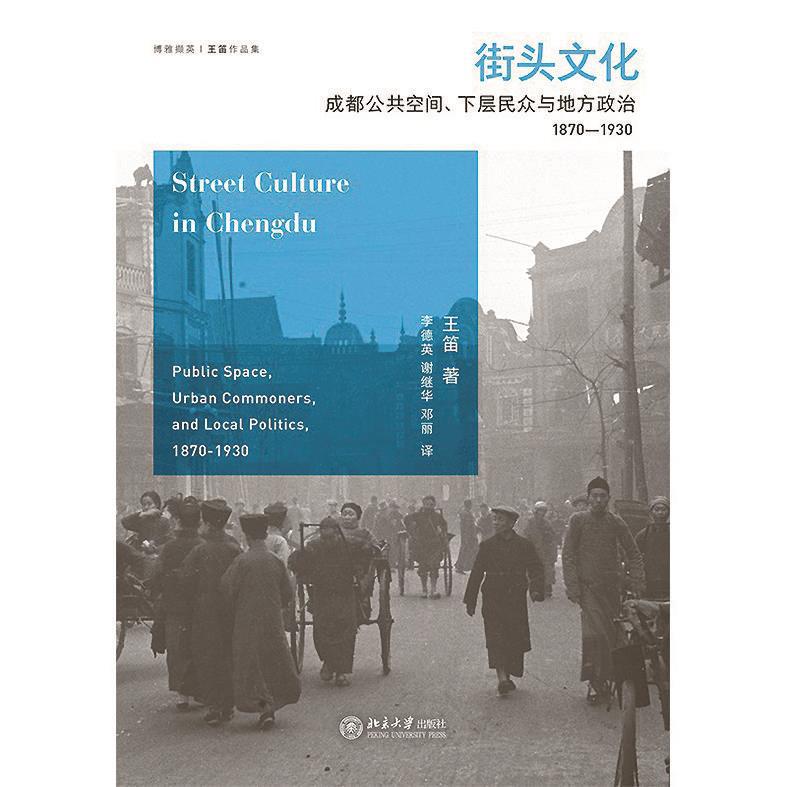日期选择


2024-10-13 第28112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在历史中寻觅普通“打工人”的声音
《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常建华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出版
■ 宋晨希从古至今,人类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记录,但绝大部分都是政治人物的血雨腥风、军事人物的金戈铁马,抑或精英阶层的思想理论。这也难怪梁启超在《新史学》里痛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历史记载都是“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很长一段时间,中外历史学家都不愿意“眼光向下”,瞥一眼普通民众。
但是,没有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喜怒哀乐,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同时代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国家的政策对个人的影响。正如年鉴学派巨擘布罗代尔所说,政治革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了解社会发展,便不能理解人类历史的变革。故而20世纪以来,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等理论接连出现,渴望发现普通人的声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所著《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以下简称《众生百态》)、澳门大学历史人文学院讲席教授王笛所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年)》(以下简称《街头文化》)以及非虚构作家袁凌所著《我的皮村兄妹》,可以说是描述古今“打工人”真实生活的代表作。
《众生百态》:清代档案里的“打工人”
常建华的《众生百态》,让我们看到了清代打工者的境遇。刑科题本是清代的司法文书,凡是涉及死刑的案件,在制度上必须要得到中央(尤其是皇帝)的核准,所以会在中央档案中留下相应的记录。刑科题本数量巨大,其中包含秋审、朝审、命案、盗案、监狱、缉捕等项内容,最早有15万件,后续因战乱兵燹,档案受潮无人看管、遭遇变卖等情况,还剩12万件。这批档案在时间段上涵盖了整个清代,但大部分是自乾隆元年以来的案件。由于数量巨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未完成整理开放工作,目前仅开放了“土地债务类”和“婚姻奸情(家庭类)”两个专题,但已经多达几百万宗案件,中外学者就此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刑科题本里留下了犯罪者翔实的原始口供,保证了历史材料的真实性。
《众生百态》主要围绕剃头匠、木匠、铁匠、篾匠、豆腐铺与酒腐店经营者、挖煤者、茶山经营者、演戏优伶等行业展开,考察“打工者”们的人际关系、经济纠纷、生活矛盾等。
例如,清代的剃头匠年龄多在30岁以上,最大者近60岁,且几乎都在外地谋生,父母亡故者较多,属于孤独之人。清代的剃头服务,主要有为客人梳辫剃头、搅剃耳窍,剃头帮工每月工钱大约四五百文。铜盆剃刀是他们的谋生工具,故而在矛盾出现时,也经常会成为作案工具。
木匠、铁匠、篾匠是清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职业,他们需要租赁店铺经营,故而很多案件都是与房东发生纠纷,也有与雇主之间因工钱产生纠纷。与剃头匠相比,木匠喜欢将斧子别在腰里,铁匠接触用具更多,篾匠常备篾刀,都容易因激动而杀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清代时期,城市里的木匠行业即已有了行规,限制同行竞争,出现了本地保护政策,通过对外地木匠加倍征收行规银来减少竞争。这为我们了解清代城市的商业运行,提供了资料。
通读全书,我们会发现清代权力渗透的有限性。虽然有学者认为,清代主要依靠精英阶层和保甲制度进行社会控制,但是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流动“打工人”,他们几乎靠着传统观念进行社区自治和自我控制,法律和政府处在缺失的状态,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发生口角时,即求之于武力。
《街头文化》:对“打工人”生存空间的管理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观念的渗入,在精英阶层眼中,“打工人”变成了卑下、愚昧、空虚、不诚实的代表。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进行引导,政府则开始关心“打工人”的处境。
王笛的《街头文化》就以成都为例,通过城市公共空间来看近代大众生活的转型。一直以来,王笛都在从事对成都的研究,《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基层权力的社会运作。在这本《街头文化》中,王笛记录了近代中国精英阶层的改良者如何改造“打工人”生存的公共空间,让他们脱离愚昧走向“文明”。
比如,针对普通人拜佛烧香、过年贴门神等迷信行为,精英阶层在报纸上叩问商民为何一年比一年穷,原因是他们坐在屋里什么都不干,专敬鬼神;当他们看到许多店铺因价格问题产生纠纷,店主态度恶劣,就专门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商业经营之道。1909年,四川劝业道甚至发布公告,明令要求店主不能回绝顾客开价,要端茶上烟。在成都,对茶馆的管理是最典型的案例。在此以前,茶馆主要是“聊天”和“讲理”的地方,是民众自我评判是非之地,人们有了口角就会相约到茶铺来争吵,由中间人分辨是非曲直。如果双方都不愿意认输,甚至会上演全武行,扔茶碗,丢板凳,等到见了血,才会报官。近代警察制度出现之后,明令取缔“吃讲茶”,“聊天”则被精英阶层看成是“散布谣言”“制造事端”。
我们不否认,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国家和精英阶层对“打工人”生存空间的管理过于一厢情愿。但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当民众无法表达自我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丧失了与精英阶层和管理者协商、博弈的机会。
《我的皮村兄妹》:“打工人”尝试自己说话
不论是清代刑科题本的记录,还是王笛对成都民众生活的研究,其所依据的历史记载都是精英所写。王笛在一篇采访中曾说,普通民众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态度,但是也需要通过研究“历史的微声”去发现“隐藏的文书”,即对精英留下的文本进行探微式研究,从只言片语中寻找普通民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准则。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碎片化的材料无法进行更多的下探研究。
198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皮瓦克发表《庶民能说话吗》一文,在中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斯皮瓦克认为,庶民是无法自我表达的,因为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已经被消费主义的观念渗透,庶民在其中丧失了自身,很难形成统一意识。此外,学者们在裁剪资料上,使用的是有助于自身研究的内容,其目的是反映国家和社会变革,其背后也是精英意识的体现。的确,在史料中留下记载的底层民众,很多人是以犯罪者的身份出现的,被记载的也多是一些极端经历。而记录者的眼光也会造成一些民众历史形象的失真,如近代成都的茶馆里,显然大多数人是在正常聊天,但外国观察者留下的史料里,记述的多是茶馆民众打架事例,意在说明中国人的愚昧。
当然,底层民众在历史中缺少声音,还有一个原因,即古代普通人识字率低,留下的文本较少,即使有些人留下了记录,如自述、日记等,也不被重视,没有出版的机会。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普通人逐渐有了机会和路径进行表达。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便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趋势的出现。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是很多打工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建立了工友之家,有图书室、博物馆和文学艺术小组,它成为了全国工友心中的梦想地标。皮村此前春节时还曾举办“打工人春晚”,网络点击破万。工友之家门口的两行标语颇能反映普通人对自身诉求的表达:“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与其他描写打工群体的作品不同,袁凌花费了七年时间,与13位打工人深入交往,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录了他们的人生和遭遇。这些打工人都参与了文学小组,心底埋藏着文学梦,有表达自我的诉求。
月嫂史鱼琴身患癌症,还有一个长期患病无法工作的老公,她在养病期间写作小说,真实记录自己的过往。她告诫自己:“赶快写,哪怕死了,写出来就没有遗憾了。”
同心二手商店店员小海,因为所住地方的公厕无人清理,苍蝇横飞,他写下了《尹各庄的苍蝇沦陷了》。虽然他辗转各地打工,报酬微薄,但是对生活充满信心,喜欢读海子,听汪峰的歌曲。他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写下“晚风吹过窗台/梦想依旧澎湃”。
现在皮村已经走出了范雨素、陈年喜这样的知名“打工人”,他们出版的《我是范雨素》和《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等作品为世人所知。皮村的很多打工人受到他们影响,也开始阅读,写作,思考自己的命运。
当然,“打工人”的“说话”,也存在着种种困境,比如他们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诗歌和文章在写作技巧上还有差距。但我们能看到,如今的普通人已经在努力言说自己。千百年来,无数底层普通人来到世界,又匆匆离开,如同流星划过不留下半点痕迹。现在,他们正在努力自己说话,让世界知道他们的困境和情感经历。